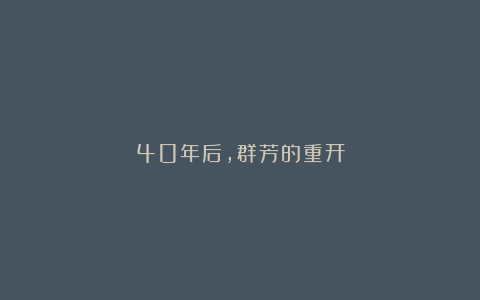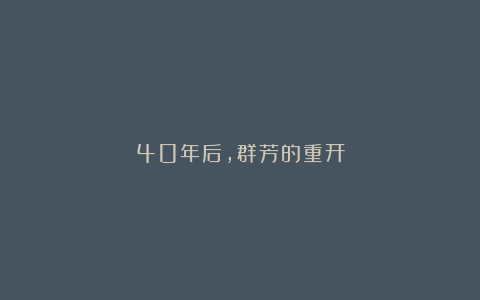《群芳谱诠释》是我国农史学家、园艺学家伊钦恒先生的代表作之一,在中国农史研究和园艺研究中,常常列为“重要参考”。在尚未成为编辑之前,这本戋戋小册一直是我内心所希望藏于箧中的“压箱宝”,但当时此书早已绝版多年,若非后来得知某著名的二手书网,恐怕此书真是无从购买。十年之前,在费过一番功夫后,我终于获得了这部装帧极为朴素的“秘册”。当时到手即展读的情形,至今想来,历历在目。不过,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虽然其内容整体不错,但书中仍存在不少的问题,从标点到文字,都有提升的空间。遗憾的是,限于环境,这部书连重版的机会都没有,修订更是无从谈起。
进入书局工作后不久,结合局内规划,我提出《群芳谱诠释》一书可以作为书局的出版项目立项。经过沟通,局内同意了这一提案。随后在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张金辉老师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群芳谱诠释》的作者方——伊钦恒先生的子女。在表明来意后,伊先生子女对于重版乃父著作一事十分支持,合同得以顺利签约。解决了合同签约问题之后,我即将精力投入到了《群芳谱诠释》的稿件编辑中。
《群芳谱诠释》,[明]王象晋 纂辑 伊钦恒 诠释
熟悉图书出版的人知道,旧书的重版工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新书一样,旧书也需要审读并撰写审读意见,通过复审、终审讨论确定发稿,在不伤害稿件骨架的基础上,对若干细节进行适当的修整,如此才能保证一部旧书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来。《群芳谱诠释》也是如此。这一次作为编辑审读此书,我发现《群芳谱诠释》从来源上确实依托于古籍《二如亭群芳谱》,但其结构与《二如亭群芳谱》并不完全一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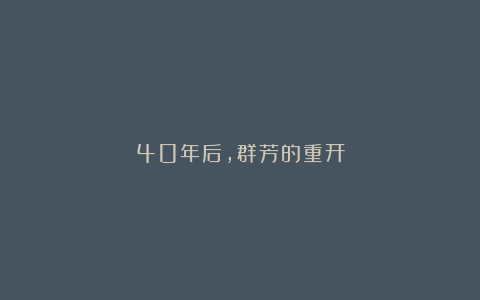 其情况具体是,《二如亭群芳谱》一共分天、岁、谷、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药、木、花、卉、鹤鱼十四谱,《群芳谱诠释》不载天谱,于岁谱中也只择采了十二月的农事,所以实际上《群芳谱诠释》只有十三谱。就谷、蔬等十二谱而言,《二如亭群芳谱》每一谱开始都有小序与首简,其中首简是若干古人文章的选辑;正文则按条撰写,下面有五或六个组成部分。以卉谱中的芸香为例,其正文分芸香一条的条目正文(即该植物的介绍),芸香的种植须知(谱中一般称呼此类内容为“种植”)、与芸香有关的其他植物(谱中一般称呼为“附录”),芸香的用途(谱中一般称呼为“疗治”),与芸香有关的典故(谱中径直称为“典故”),与芸香有关的诗文(谱中称呼“丽藻散语”)。《群芳谱诠释》保留小序与首简的内文结构,其中若干小序和首简还由整理者重撰;在正文部分,只选入条目正文,典故、丽藻散语等一概不选,种植、附录、疗治这三部分择要而选。如此操作的目的,正如伊先生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此书的工作是“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展开的。
其情况具体是,《二如亭群芳谱》一共分天、岁、谷、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药、木、花、卉、鹤鱼十四谱,《群芳谱诠释》不载天谱,于岁谱中也只择采了十二月的农事,所以实际上《群芳谱诠释》只有十三谱。就谷、蔬等十二谱而言,《二如亭群芳谱》每一谱开始都有小序与首简,其中首简是若干古人文章的选辑;正文则按条撰写,下面有五或六个组成部分。以卉谱中的芸香为例,其正文分芸香一条的条目正文(即该植物的介绍),芸香的种植须知(谱中一般称呼此类内容为“种植”)、与芸香有关的其他植物(谱中一般称呼为“附录”),芸香的用途(谱中一般称呼为“疗治”),与芸香有关的典故(谱中径直称为“典故”),与芸香有关的诗文(谱中称呼“丽藻散语”)。《群芳谱诠释》保留小序与首简的内文结构,其中若干小序和首简还由整理者重撰;在正文部分,只选入条目正文,典故、丽藻散语等一概不选,种植、附录、疗治这三部分择要而选。如此操作的目的,正如伊先生在引言中所说的那样,此书的工作是“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展开的。
旧刻本《二如亭群芳谱》版式
不仅如此,在这条方针的指导下,作者在《群芳谱诠释》中还多做了两项工作,一是调整了若干条目的位置,如将原在果谱的百合、莲藕等改入蔬谱;二是增补《二如亭群芳谱》原书没有条目,如凤梨(菠萝)、猕猴桃、番木瓜、西红柿等条目的补入。从现在严格的古籍整理标准而言,以上两项工作看起来都过于大胆,但站在从作者作为要向大众提供园艺知识的园艺学家的角度出发,这些工作却在情理之中。
在厘清《群芳谱诠释》的结构之后,我对整个书的内容进行了梳理,结果发现旧版中需要调整改动的地方很多。举例而言,在旧版中蔬谱下没有南瓜一条,初读之下,或者以为这是作者不选本条的缘故,但在其瓠子条的诠释中,作者开篇即说“黄瓜、稍瓜、菜瓜、丝瓜、冬瓜、南瓜、葫芦、瓠子都是葫芦科草本植物”,从这一条可以推出在原稿中是有“南瓜”一条的,如果没有南瓜,作者的诠释就成了“无本之木”了,因此,本次编辑时就根据其诠释将“南瓜”条补回。
再如,花谱中的兰条,这一条内旧版在涉及条目内介绍兰花各栽培品种的小字注文时,都存在节略的情况,但在本书引言中,作者交代其节略的原则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兰花各栽培品种下的小字注文是对该栽培品种的形态学描述,从今天眼光看确实有不准确的地方,但并不属于“糟粕”之列,节略这部分描述显得“莫名其妙”。后来我专门就此同作者方家属沟通,提出针对节略文字采用补回的操作,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因此书内涉及到节略地方,本次都依据《二如亭群芳谱》做了补回;即使不能补回的,也在相应位置以编者注的形式做了说明。
《群芳谱诠释》旧版出版于1985年,而出版当年作者伊钦恒先生逝世。结合旧版中出现若干文字使用情况推断,作者当年原稿应是一份繁体手写稿。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些情况无疑增加了该书的编辑难度。书稿存在节略与缺失,显然是一种“中间态”的形式。以此形式出版,应有其不得已的原因。所幸,在系统分析了稿件的结构(骨架)之后,确定了正确的编辑方案,最终为本书在新旧古今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使本书能够以更符合其理想面貌的形式出版。
从上文的叙述中,或许会有人以为本书只是一部套着古书皮的园艺新书,实则本书对于未来进行《二如亭群芳谱》的严格整理也有极大的参考意义。例如在谷谱首简中,作者选录了《二如亭群芳谱》原书就有的氾胜之《论耕》篇,本篇第一句“凡耕之本,在于趋时,和土,务粪泽,早锄早获”中的“早锄早获”,《二如亭群芳谱》原作“早锄获”,但《群芳谱诠释》改为“早锄早获”,更符合其农事进行的逻辑,而金泽文库本《齐民要术》在此处正是写作“早锄早获”。从此可见《群芳谱诠释》对于《二如亭群芳谱》的文字是有所校订的。
在内容编辑上,除了上述对《群芳谱诠释》与《二如亭群芳谱》关系的调查与平衡,诠释部分的重审与订正也是编辑《群芳谱诠释》的重要工作。就内容而言,作者的诠释是多个方面的,有些时候是对这一条目的现代植物学知识的介绍,有些时候是对这一条目涉及的植物学史的介绍,有些时候对该种植物的若干栽培要点的介绍等等,这无疑给编辑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特别是现代植物学知识部分,因为现代植物学也在不断地发展,书中涉及这部分的知识或多或少会显得“滞后”,甚至表现出“错误”。为了平衡这部分的关系,我采用了编者注的形式,将若干与当下植物学知识不符的内容尽量做了页下标注。值得一提的是,书内现代植物学知识审核工作,曾由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张全星先生承担,在这里向其致以深深的谢意!
此外还有一点要说明,在编辑带有拉丁学名的图书时,为了方便读者检索,一般都要编制书内涉及的拉丁学名索引,由于生物的拉丁学名在不断的修订,按照出版这类图书的一般原则,都要编制新旧学名对照表。这两种图书辅文是科技类,特别是与生物学相关的图书的“标配”。旧版限于时地环境,未能制作这两种辅文,这一次新版,就将拉丁学名索引以及新旧学名对照表这两种辅文附上,既合乎这种隐形的“规范”,也方便读者使用本书。
在图书编辑临近尾声时,我设想本书的封面应该是要和“群芳”二字相合,当时脑中立马闪过了科学画大师曾孝濂先生的画作——《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此画中一共绘制了三十七种原产于中国的植物,正和《群芳谱诠释》中提到的若干植物合若符契,而且曾先生的画作是将这三十七种植物绘制于一图之上,色彩绚丽,层次分明,百卉同开,群芳争艳,非常具有震撼力。能够用《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来作为本书的封面,恐怕再也合适不过了!为此我辗转联系上了曾先生,并告知曾先生想用其画作作为图书封面底图的设计方案。曾先生得知后,欣然允可,并且还提供其若干画作作为本书的插画。曾先生的无私与热忱,值得我永远铭记!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国内曾系统出版过一大批农书,这些农书基本有一个特色——旧书新做,专家整理。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农书都逐渐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少农书甚至未能得到最合适其内容的展现形式。《群芳谱诠释》就是这样一部农书。现在,通过努力,这本书在新时代以合适的面貌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诚挚地希望,这一次群芳的盛开,能够留给世人更多更美的风采!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