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晚明时期,波诡云谲、变幻莫测。樊树志教授笔下的晚明图景,字字是辉煌,又句句有苍凉,令人难以释卷、无法平静。
樊树志以数百万字巨作展现一代王朝由盛转衰直至覆亡的全过程。隐于书后的他,曾为历史上的哪个人、哪件事心潮澎湃?记者向87岁高龄的老教授寻求答案。他语气淡然地谈论“晚明大变局”,平实的表达中不乏振聋发聩之论。
今年,他三次校对《重写晚明史》书稿,三次因用脑过度而送医急诊,目前虽处于停笔状态,胸中依然涌动无限遐思。一代历史学人以学识与修养之光,为今人照亮了历史上那些被忽略的岁月。
【樊树志】
生于1937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明史半个世纪,专注于晚明史亦有20余年。
代表著作有《重写晚明史》五卷(2024年)、《人世事,几完缺——啊,晚明》(2024年)、《江南市镇的早期城市化》(2023年)、《明史十二讲》(2021年)、《图文中国史》(2020年)、《国史十六讲》(2016年)等。其中,《晚明史(1573—164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
第一个提出“晚明大变局”观点
上观新闻:“晚明大变局”是您的创见?
樊树志:是的。“晚明大变局”是我研究明史的感悟,也可以说是心得,是由我第一个提出。
晚明这个概念历史学界早已有之。李文治先生写过《晚明民变》,仅涉及明末农民起义;谢国桢先生写过《晚明史籍考》,泛指明嘉靖、万历以及明末的时间段;而我选择将1573年(万历元年)至1644年(崇祯十七年明朝灭亡)定义为晚明,是为了叙述方便。
晚明虽然政治体制依然故我,但在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等方面出现了大变局。这表明中国内部正在发生巨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新因素和新突破。一言以蔽之,我认为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上观新闻:对于“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的说法,学术界有何反响?
樊树志:这虽然是我的“一家之言”,但近年得到许多学者的呼应,我觉得自己不是孤军奋战,“晚明大变局”已然成为一个共识。
上观新闻:您第一次提出“晚明大变局”,是在2004年6月28日刊登在本报的署名文章《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中。
樊树志:是的,我和《解放日报》很有缘。我步入史坛的早期专攻明清社会经济史,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在复旦大学为本科生开设中国土地关系史课程。我认真备课,写了详细的讲稿,一面上课一面修改充实,形成50万字的《中国封建土地关系发展史》。
此后,我把研究重点转移到江南市镇,又有出版社编辑邀我撰写《万历传》和《崇祯传》,那套帝王传记丛书很畅销。持续五六年对万历和崇祯两朝历史的深入探索,改变了我的研究方向,从此开启了持续20多年的晚明史研究。
2003年,我的《晚明史(1573—1644年)》上下册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印行,受到出版界与读书界的肯定,同行专家周振鹤、葛剑雄、唐力行、熊月之、范金民等写下评语,激励我继续努力。努力的成果就是《晚明大变局》和《重写晚明史》。后来,我全力投入《晚明大变局》的撰写。2004年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这篇文章,论述了重新评估晚明史的不同寻常的意义。
2004年6月28日,樊教授刊登在解放日报上的署名文章《文明的彷徨——晚明历史大变局》
上观新闻:“晚明大变局”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
樊树志:绝对不是故意耸人听闻。人们常说晚清大变局,殊不知晚明也有大变局。我希望人们放宽历史的视野,看看16世纪至17世纪的中国发生的巨变。重新评估晚明史,这对认识晚清史也有好处。
我主要从六个方面论证晚明的大变局,一是“海禁—朝贡”体制的突破,二是卷入全球化贸易的浪潮,三是市场经济与早期工业化,四是思想解放的潮流,五是西学东渐与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六是文人结社与言论的新气象。这种剧变是前所未见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或许可以说,没有晚明大变局就不可能有晚清大变局。
历史的道路并非笔直向前
上观新闻:您站在全球史的角度解读晚明王朝,得出了“中国的近代化起步与欧洲几乎同步”这个结论,颠覆了不少人的认知。
樊树志: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局,历史学家称之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或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绕过非洲好望角发现了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些发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人类历史进入史无前例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也因此卷入了全球化贸易浪潮。
由于制造业的优势,中国与任何国家的贸易都处于顺差之中。无与伦比的优质生丝、绸缎、棉布、瓷器等中国商品从澳门通过马六甲、果阿、好望角运往欧洲的里斯本,这是印度洋大西洋丝绸之路;从漳州的月港出发经过马尼拉,搭乘马尼拉大帆船,运往美洲的阿卡普尔科,这是太平洋丝绸之路。
随着商船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传播欧洲的科学文化。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放眼看世界。而先进的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结果,使得一般中国人的世界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中华书局出版的《重写晚明史》五卷本
上观新闻:既然晚明时期中国的近代化已初露端倪,后来为什么又落后了呢?
樊树志:所谓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绝对始于哪个年代。历史的道路并非笔直向前,有时也会停滞甚至倒退,近代化之路也不例外。放宽历史的视野,用全球史眼光看来,没有晚明何来晚清,16世纪开始的晚明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目前已经得到一些学者专家的呼应。
明清史研究大家孟森说:“熹宗,亡国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泽犹未尽也;思宗,自以为非亡国之君也,及其将亡,乃曰有君无臣。夫臣果安往?昔日风气未坏,正人君子,屠之而不能遽尽,故无君而犹有臣;至崇祯时,则经万历之败坏,天启之椓丧,不得挽回风气之君,士大夫无由露头角矣。思宗而在万历以前,非亡国之君也;在天启之后,则必亡而已矣。”确实是振聋发聩之论。
孟森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写了洋洋数万言。我则用将近两百万字来展现明朝由盛转衰直至覆亡的全过程——仅仅有经济文化的繁荣,而没有震慑朝廷内外党同伐异的雷霆手段,没有把内忧与外患消弭于无形的非凡能力,王朝终将走向末路,改朝换代不可避免。
上观新闻:晚明大变局对后来的中国产生了什么影响?
樊树志:没有晚明大变局就没有晚清大变局。清朝建立后,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的抗清运动而实行空前严厉的海禁政策,“片板不许下海”。晚明时期东南沿海繁荣的对外贸易景象消失得无影无踪;清初以降,朝廷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屡兴文字狱,康、雍、乾三朝,一朝比一朝厉害。文人们个个噤若寒蝉,躲进象牙塔,埋首于古代经典的文字训诂。晚明文化思想界的宽松氛围,早已烟消云散。嘉庆以后,统治者对思想的钳制有所放松,情况才有所变化,类似晚明大变局的浪潮再次出现。魏源接受林则徐的委托,编写《海国图志》,向国人介绍世界,打开国人的眼界,就是突出的表征。
我们还可以在新文化运动中看到当年王阳明开创的思想解放潮流的影响。王门后学“掀翻天地”“非名教所能羁络”的精神,引起了共鸣。
“人”的身上映照出王朝命运
上观新闻:晚明的众多人物中,您着墨最多的是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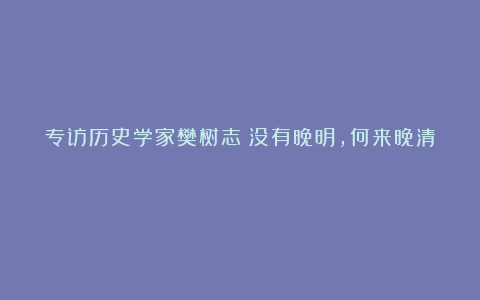
樊树志:自然是万历皇帝和崇祯皇帝。万历皇帝10岁登基,少年天子励精图治,与张居正联手打造万历盛世。张居正死后却对其抄家清算,掀起数十年党争。其后20多年不上朝,被大臣痛批“酒色财气”。
万历皇帝在位48年,一生基本可以分为两段,他的人性弱点也给他的王朝带来了厄运。许多人问,万历前期还比较勤政,后来为什么很少上朝?我根据考古报告判断,发现他确实是身体有病,他很胖,晚年不方便行走。说他不理朝政,是指他不是每天上朝,但他还是控制朝廷的。要说皇帝完全不理朝政,我想几乎找不到这么一个人。
万历皇帝肖像画
上观新闻: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又是怎样一个人呢?
樊树志:后来的史家认为,明之亡实亡于内。其中原因很多,最显而易见的便是在攘外与安内的两难选择中举棋不定。或者说,崇祯与廷臣对“必安内方可攘外”的方针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而崇祯皇帝一生最值得称道的政绩,是下令清查阉党逆案。他没有处死魏忠贤,魏忠贤是在被流放的路上上吊而死的。
研究历史最忌因人废言、因事废言、预设禁区,否则必将使揭示历史本来面目成为一句空话。
上观新闻:我特别喜欢您今年在中华书局与《重写晚明史》系列一起出版的《人世事,几完缺——啊,晚明》一书。这本书故事性很强,书名用的是明末清初吴梅村的诗,他是否也是触动您的人物之一?
樊树志:没错。我读完《梅村家藏稿》,感慨不已,仿佛超越时空听见远方传来一声沉重的叹息:“人世事,几完缺!”这是吴梅村的感叹,也是我对晚明命运的感叹。
吴梅村少年时便有才名,很受崇祯皇帝赏识,连他的老师都发出“人间好事皆归子”的感叹。
但是吴梅村生不逢时,在明朝灭亡、清朝建立后没有投身抗清运动,也没有摇身一变归顺新朝,他一直在冷眼旁观。后来他在清朝被迫为官,晚年病重时写下“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的句子。他给世人的最后留言,竟是认为自己“草间偷活”“一钱不值”,内中的辛酸与悔恨,欲说还休。从他的身上,可以映照出一个王朝颠覆的悲凉与无奈。
中华书局出版的《人世事,几完缺——啊,晚明》
以冷静公正之心、新颖流畅之笔书写历史
上观新闻:您从皇帝写到大臣,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立体而饱满,您写历史是为了“以古喻今”吗?
樊树志:中国一向有“以古喻今”的传统。历史与现实固然不能割断,但历史是历史,现实是现实,两者不可混为一谈。我没有想过“以古喻今”,只想以尽可能客观、冷静、公正的心态书写晚明史,其间可能有些见解有悖于以往流行的传统观点,那是对历史理解的视角有所不同,乃百家争鸣的题中应有之义。
上观新闻:从事写作的人都知道,既要坚持历史学的“宏大叙事”,又要有文学性的表述,这很难。您是如何达成这种统一的?
樊树志:我一向主张历史著作应该是学术性和可读性并重,雅俗共赏,文章既有学术底蕴,又能引人入胜。
2006年,我的讲稿《国史十六讲》出版,当时影响力比较大,有人说是“引起轰动”,《中华读书报》以将近一个版的篇幅发表书评,分析此书出版后连续几个月位居学术类图书排行榜前列的原因。评论者分析出两个“奥秘”:一是“好看”——写法吸引人,二是“值得看”——论述内容有价值、有意义。
我的《重写晚明史》也注重这两点。我力争做到写法新颖、文字流畅,尽力避免历史著作枯燥乏味的弊端。为了锻炼文笔,我有时也写写历史类随笔,甚至还写过影评。
上观新闻:您写历史人物传记与写其他历史著作又有明显不同,具体而形象的文字使一般读者也能轻松自如地读下去。其中有何秘诀?
樊树志:写历史人物传记,与写一般历史著作明显不同之处,是必须树立传主的形象、刻画人物的性格,不能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地写成一笔流水账。
古希腊传记体史著奠基人普鲁塔克在他的名著《亚历山大大帝传》序言中,曾经这样透露心得:“我所写的,不是历史的书,而是一部传记。一些小小的行动及语言,常常比大事件更能显示一个人的性格。正如画家画一幅肖像时,他只抓住脸庞和眼神,几乎不考虑身体的其他部分。我也把大事迹或战争部分让给他人去写,我只写人物心理方面的特征,用这种方法来叙述或描写每一个英雄或伟人的传记。”我以为这是值得借鉴的传记笔法。
当然,帝王和重臣,并非个个都是英雄或伟人,但关于他们的传记的写法,大体是有共通之处的。不过,话虽这么说,做起来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有相当的功力和识见。我尽量写得洒脱一些,但有时也不尽如人意。多年来形成的固定程式、习惯也会困扰着我的思绪,要追求一种新颖的章法和笔法,时常心有余而力不足,流露出为旧传统所束缚的痕迹。所以,我在写作过程中,非常有意识地去克服这些问题,写完后还会反复读、反复改。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字,都是生动而轻松的。
上观新闻:您喜欢哪些历史读物?
樊树志:比如说,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史学经典就很好,其中许多篇章可以与脍炙人口的文学大师的散文佳作相媲美,读来朗朗上口。此外,当代美国的历史学家史景迁所写的一系列叙事史作品,好评如潮,道理也在于此。
成功的历史学家给予我们的启示是多侧面的。著作等身的一代宗师朗克说,历史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就其寻求史料、确定史实等方面来看,史学是科学,但史学并不到此为止,它要求叙述和再造。作为科学,它与哲学相关;而作为艺术,它又与诗歌相近。
在朗克之后的英国史学家马考莱的作品以叙述生动细致著称,他曾经说过,历史著作应该让我们的祖先以他们自己的语言、方式和装束出现在我们面前。另一位英国史学家屈维廉一生写下大量文笔生动、受人欢迎的作品,继承了“文学史学”的传统,追求一种美、一种趣味、一种联想。这些都是我们历史学人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把学术研究时间延伸20年
上观新闻:看得出,您退休后的研究与写作进入了更加自由的状态。
樊树志:我们这一代人,20世纪50年代进入大学,但多年来可以静下心来读书研究的时间很有限。1977年恢复大学招生以后,我们奋起直追,竭力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年轻时为了评职称写论文、出专著,是出于工作的需要,而真正谈得上做学问,是在50岁以后,而且随着年龄增长、学问积累,大体呈现后来居上之势。
我现在算算,50—60岁期间,出版了4本著作;60—70岁期间,出版了5本著作;70—80岁期间,出版了7本著作;80岁以后,出版了11本著作——当然,其中有些内容是修订本重印。现在你们看到的装帧精美的五卷本《重写晚明史》,就是我80岁以后的成果。我把学术研究的时间延长了二十年。
上观新闻:您这几十年的研究道路,有什么特别值得回忆的事吗?
樊树志:其实我的历史研究生涯可以说是一帆风顺的,尤其是研究晚明以来更是顺利,因为这个时代,各种资料都实现了数字化,查阅十分方便。
我年轻时经常到图书馆抄书,我对此印象很深刻。我抄过很多卡片,装满好多大袋子。那时我家住在黄河路附近,距离上海图书馆不远,我经常到那里去看书,开一张书目,一本一本找书,一去就是一整天,中午就在图书馆食堂买肉包子吃。
我以前还经常去合众图书馆,那个图书馆位于长乐路、富民路口,是一幢“凸”字形的街角建筑,图书馆是抗战时期建立的,当时为了避免侵略者的注意,图书馆面向路口的正门不挂任何牌子,也从不打开大门。走到门口按了电铃,才能到阅览室去看书。当时我正在研究江南市镇,我在那里阅读了许多难得一见的地方志。很多年来,我抄的小卡片全堆在家里的床底下,全是手写稿,现在还有一部分保留在老房子里,那是我很珍惜的早年积累。
樊教授多年积累下数万张资料卡片和许多笔记本
上观新闻:您至今还保留着手写的习惯吗?
樊树志:六十岁以前,我的书稿和抄的资料都是手写的;六十岁我开始学习电脑打字,其后的书稿都是电子稿。近几年为了锻炼脑力,我经常手写日记,但目前已经完全停笔了,我不想再延长自己的学术寿命了,我的眩晕症就是用脑过度造成的。
今年我完成《重写晚明史》的校稿后,虽然不写东西了,但还是会关心国际形势,看看纪录片、听听广播。我最感兴趣的是每天下午的“音乐下午茶”,听听西洋轻音乐,还有就是每晚七八点的苏州评弹,评弹的词汇很丰富,对写作的人会有很大的帮助。
你看,我已经把我的学术研究的时间延伸了20年,来弥补此前流失的20年。钻研学术的前提是身体健康、思路敏捷。这两年,我经过五次住院,如今终于回归到“退休”的本义。
题图来源: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