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古物大量流散欧美,价格高、易携带的古玉尤为大宗。笔者于1979-1980年曾旅行探访二十余所博物馆,在各馆库房仔细研究玉器。到1990年代,再多次前往重要的馆藏从事专题研究。“良渚玉器上的刻画符号”就是当时密切关注的专题之一。
去年(2019)良渚文化申遗成功,浙江的考古工作团队与故宫博物院联合推出“良渚与古代中国——玉器显示的五千年文明”特展。中国文物学会玉器专业委员会配合展览,八月底在故宫举办一天“良渚玉文化论坛”。笔者应主办方的要求,介绍良渚古玉流散欧美情况,因成此篇。
本文除回顾百余年流散欧美的良渚古玉收藏及出版情况,介绍四件圆周有刻符的良渚玉璧并讨论良渚文化礼制外,也略论约16至20世纪仿赝良渚古玉的特征。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Chinese antiquities were scattered in Europe and America. Highly priced and easily carried ancient jade has become the majority sold to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e author traveled and visited more than 20 museums between 1979 and 1980, and carefully studied jade objects in the repository of each museum. By the 1990s, the author repeatedly visited the important collections to conduct special research. ‘ Characterized engraving symbols on Liangzhu jade’ was one of the topics I paid most attention to at the time.
Recently (2019), Liangzhu Culture was successfully enlisted as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s. The archaeological team in Zhejiang and the Palace Museum jointly launched a special exhibition of ‘Liangzhu and Ancient China-Five Thousand Years of Civilization Displayed by Jade’.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exhibition, the Jade Profess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lics Society held a ‘Liangzhu Jade Cultural Forum’ at the end of August in the Palace Museum. At the request of the organizer, the author presente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ituation of Liangzhu jade collections in Europe and America.
In addition to reviewing th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llections and publications of Liangzhu jade in the last 100 and more years, and introducing four Liangzhu jade bi-disc engraved with inscriptions on the circumference, the author also briefly discusses the etiquette of the Liangzhu culture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16th to the 20th century’s counterfeit of ancient Liangzhu jade.
关键词:良渚文化玉器;良渚文化禮制;欧美收藏;明清仿赝
Keywords:Liangzhu Culture Jade Liangzhu Cultural Etiquette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llection
Counterfeits made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早年良渚玉器流散欧美
目前从出版品及各博物馆官网公布资料初步统计,在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瑞士、瑞典,约三十间博物馆或研究机构,以及一处皇室收藏,所公布的良渚玉器,保守估计约二、三百件。博物馆名大致如下:
(一)美国:共22间,依字母为序如下:
笔者于1991年出版《百年来古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1]文中收录了当时能网罗的大多数欧美地区典藏中国古玉的博物馆及其出版品的资料。近年《玉器时代》一书的出版,[2]增加了美国境内多间博物馆的资料。由于资料繁琐,笔者仔细浏览检索各处收藏良渚玉器的资料,[3]编为附录,列于文后,以备检索。
海外收藏良渚玉器数量最丰富的,首推华盛顿的弗利尔博物馆,藏品主要来自二十世纪初大收藏家弗利尔先生(Charles Lang Freer, 1854-1919)的捐赠,目前该馆官网上登录168件良渚玉器,多系二十世纪初年上海的古董商游筱溪所出售。[4]其中有四件玉璧、一件玉镯,器表刻有特殊的符号,则是1917年及其后数年间所购。[5]本文第四节会讨论其中的一件璧。
但良渚玉器进入欧洲的时间可能更早。
祖籍浙江湖州,先后旅居法国、美国的古董商卢芹斋(C. T. Loo, 1880-1957),他于1950年在美国诺顿博物馆出版英文图录《中国古玉—诺顿博物馆特展图录》,[6]在序言中,卢氏记录1912年,巴黎的赛奴奇亚洲博物馆(Cernuschi museum)馆长找他举办以中国古玉为核心的中国艺术展。受此影响,法国北方铁路公司的吉斯拉博士(Dr. G. Gieseler)对卢氏表示自己打算集成一批中国古玉收藏。1912-1913年,卢芹斋在中国全力为吉斯拉收购中国古玉。
或因此故,吉斯拉获得一件良渚玉琮(图一~1),1915年吉氏撰法文论文讨论之,当时公布全器线绘图及射口上最明显的符号(图一~2),文中叙及在上、下射口还各刻有五个符号。[7]1929年喜仁龙(Osvald Siren )法文版《中国古代艺术史》专书中公布该器的黑白照片。[8]
从吉美博物馆的出版品记录可知,该件玉琮于1932年捐赠给巴黎的吉美博物馆。[9]吉美博物馆曹慧中研究员曾受笔者请托,据实物绘出了1915吉斯拉提及,但未公布的10个符号,笔者乃于1993年撰文《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10]完整公布了该玉琮上下射口共11个符号的相对关系。罗马数字I-IV,代表不同的四个面。“右”“中”“左”代表符号在上射口或下射口的部位。“中”代表正对中央直槽的射口上。(图一~2-12)
1923年乌娜·蒲柏-亨内西(Una Pope-Hennessy)执笔的英文版《早期中国玉器》一书在纽约出版。[11]书中发表六件所谓“琮”,均属英国藏家乔治・尤莫弗普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1863-1939)所有,书中多订于周代、汉代。但从今日考古资料可知,其中二件属良渚文化、一件属齐家文化。[12]前二者后归大英博物馆。其中之一是一件十九节良渚文化晚期玉琮,高49.5厘米。它是目前存世最高的良渚玉琮,当时被订为汉代,以大头向下的方式发表。[13](图二中)
根据卢芹斋1950年书中记录, 1927年,他在伦敦展售藏玉时才认识尤莫弗普勒斯先生,因此可确知图二中那件高玉琮并非卢氏出售,推测当时良渚玉器流散欧洲应不止一个管道。[14]
卢芹斋共出版二本关于中国古玉的专书。由于1924年河南彰德府(即今日安阳)与洛阳各被盗掘一座大墓,卢氏获得全部的玉器,并与伯希和合作,于次年出版法文大书《卢芹斋藏中国古玉》。[15]该书主要收录殷墟、西周的玉器,以及石峁文化的墨玉牙璋、长刀等。[16]书中并无任何一件良渚文化玉器。
但卢芹斋后来开拓他在美国的市场,1948-1949年,因中国政治因素,他被迫结束古董事业,所以1950年在诺顿博物馆的玉器展售图录,可视为他结束营业前,出清玉器存货的买卖。书中就有四件看来可能属良渚文化的玉器,(图三至六)但书中都定为“西周晚期”。
总之,二十世纪初,良渚玉器最初流散至欧洲,很可能与卢芹斋有关。但卢氏之外,也应有其它管道。良渚玉器也大量经由上海的游筱溪卖往美国,弗利尔则是主要的收藏者。不过,当时这些都被视为周、汉时期玉器。
黄浚(1878-1951)也是活跃于二十世纪前半的古董商。他定居于北京琉璃厂,主要经营尊古斋,分别于1935年、1939年出版《衡斋藏见古玉图》、《古玉图录初集》,书中只刊载他所经手出售玉器的拓片或照片,未定时代、品名。从出版品可知,当年他所经手的许多玉器,而今分散藏于欧美重要博物馆,笔者曾作追踪研究,[17]可知他的顾客群也颇多欧美人士。
在黄浚的两本书中,[18]均刊有一件刻有良渚风格面纹的奇特玉璜(图七),在《古玉图录初集》中,除该件玉璜外,还刊有一件可能为良渚文化的八节玉琮。(图八)
图七玉璜虽刻有乾隆35年(1770)的御制诗,证明原属清宫旧藏,但不知何故,后归属金石学家王懿荣所有,又传给其子王崇烈收藏。[19]由于两度出版于黄浚的集子里,推测1935年以前已归他所有。
图七玉璜后收入“中国文物商店总店”。由于20世纪70-80年代期间,考古发掘了良渚文化玉器后,有学者把这件玉璜当作良渚文化玉器撰文讨论。[20]笔者于2003年初春,在由“中国文物商店总店”。改制的“中国文物信息咨询中心”仓库见到实物。[21]仔细观察可知,纹饰结构与线条都不像真的良渚文化玉器,笔者于2005年、2006年两度撰文论述之。[22]目前它可能归入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却未见展览出版。因本文第六节将讨论明晚期至清代仿良渚纹饰的问题,所以在此节先行介绍。
有关良渚古玉的外文出版物
除了古董商的记录可提供我们追索古物的流散轨迹外,早年西方学者的专书也透露许多讯息。限于篇幅,本节仅略做介绍。
1906年,纽约的藏家毕绍普(Heber R. Bishop)私人出版其藏品英文专书《毕绍普收藏-玉的调查与研究》。该书分上下册,系敦请矿物学家坤斯(George Frederick Kunz)和医生兼东方学家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联合规划,只印制一百册,相当巨大精美,内附有李澄渊的《玉作图》。[23]毕氏的收藏后归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多为清代作品及印度蒙兀儿帝国玉器,并无良渚玉器,[24]这显示西方藏家最初收藏东方玉器的方向,重视美感与制作工艺。
洛弗氏(Berthold Laufer , 1874-1934),是一位德裔的美国人类学家。他深受吴大澂《古玉图考》影响,1912年出版英文专书《玉-中国考古和宗教的研究》,[25]引述颇多吴氏书中线绘的各式所谓“琮”。[26]洛弗氏的研究对二十世纪初年西方学者影响甚深。
二十世纪中叶,研究中国古玉的学者,主要有萨尔摩尼(Alfred Salmony, 1890-1958)与韩斯福(S. Howard Hansford)。前者是德籍艺术史家,后移居美国,执教于纽约大学。他研究流散美国的中国古玉,于1938、1952、1963年出版三本专书。[27]后者为英国学者,伦敦大学教授,研究流散世界各地(美、英、法、瑞典、伊朗等)的中国古玉,于1948、1950、1968年三度出版专书。[28] 1969年,则为旅居南非的逢欧兹男爵的玉器撰写图录。[29]
综览萨氏与韩氏著作可知,他们主要受吴大澂、洛弗氏的影响,将当时流散美国、英国的良渚玉琮,推测为周代玉礼器,是“地”的象征。韩氏更受到法国人密舍尔·亨利(Michel Henry)的影响,认为长管状的玉琮可能是与“璇玑”组配,观测星象的“玉衡”。[30]所以在韩氏1968年专书中,把大英博物馆藏良渚文化晚期八节玉琮释为“可能是观测管 perhaps a sighting tube”。
萨氏1963年专书首度发表藏于弗利尔博物馆的三件良渚玉璧上所刻画的符号。(图九、一0、一一)。他将之都订为商代,并解释图九符号的意义是:“小鸟是死者的灵魂,栖息在祖庙屋顶。双圈代表灵魂之门。玉璧象征太阳,所以刻纹联系了灵魂与日、夜的星辰。”
二十世纪后半叶,研究中国古玉杰出的西方学者有罗樾(Max Loehr, 1903-1988)与罗森教授(Jessica Rawson, 1943-)。罗樾于1960-1974年间任哈佛大学东方艺术史教授,1975年出版典藏于该校福格博物馆(Fogg Art Museum)的温索普收藏中国古玉的英文专书《福格博物馆的温索普收藏中国古玉》。 [31]由于笔者曾认真检视此收藏,可以较肯定地确认:书中只一件真的良渚文化玉镯,但当时被归为时代不明(图一二)。反而把四件二十世纪前半的仿良渚赝品高琮,断代为“东周玉琮”(图一三)。[32]
如图一三的赝品,在二十世纪前半制作了多件,估计是以图五、六、八这些良渚玉琮(当时认为是周、汉玉礼器)为母型的仿赝。多销往海外,除哈佛大学的温索普收藏四件,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芝加哥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也有。[33]日本大阪江口治郎氏藏有一件,以彩色图发表于1955年出版的《支那古玉图录》卷首。[34]
罗森教授于1976-1994年间担任大英博物馆东方部副主任与主任,1994年后任教于牛津大学,担任墨顿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副校长。1975年,她参与英国艺术理事会(Arts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在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举办的中国古玉特展,并出版英文图录《中国历代古玉》,书中发表一件私人收藏良渚晚期六节玉琮,订为东周。[35]总之,直到二十世纪的70年代,虽然流散在欧美的良渚玉器虽陆续发表,但多被断代为周代或汉代。
由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在江苏、浙江先后发掘多处重要的良渚文化遗址,[36]令世人为之震惊,才知道那些玉器的年代如此久远,意义非常重大。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林巳奈夫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员莫瑞(Julia K. Murray),均适时地将弗利尔博物馆藏良渚玉璧上的刻画符号,或以图片,或以线绘图公布。[37]
笔者于1992年、1995年、1996年,分别在华盛顿、台北、伦敦、旧金山查访了四件圆周上刻画重要符号的良渚文化晚期玉璧,对研究良渚文化意义重大。将于第四节集中讨论。
1995年,罗森教授为香港何东所收藏的古玉举办展览,出版英文图录《新石器时代至清代的中国玉器》,[38]书中将何氏所藏及大英博物馆所藏良渚文化玉器,作了正确的断代。同时举办中国古玉学术会议,笔者参与会议,并发表中、英文论文《中国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论》。[39]
进入本世纪后,与早年流散欧美良渚玉器相关的西文著作至少已有三本。
前文已提及2009年江伊莉等出版的中英文双语专书《玉器时代 : 美国博物馆馆藏中国早期玉器》,[40]作者甚为用心地广搜考古资料,希望对流散美国的中国史前玉器给予定位。但作者不知用以制作良渚玉璧的玉料多为斑晶结构粗松的闪玉,[41]所以良渚玉璧的厚度与直径有一定的关系,若制作过薄,就易于断裂。所以很难想像直径几达29厘米、厚度只有0.32厘米,色泽也很不类的玉璧,被推定为良渚文化。[42]
2016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中英文双语专书:《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玉器》,[43]2019年,哈佛大学博物馆群出版英文专书:《哈佛艺术博物馆群藏早期中国玉器》。[44]前述所述及的温索普古玉收藏亦并入此博物馆群。后两本书中讨论良渚玉器的部分,尚有待议之处。将于本文第五节讨论之。
“符号”证明良渚极晚期才形成“非典型璧琮礼制”
良渚文化发展千余年,近日正式公布的考古学年代为公元前3300-2300年。[45]但据称下限可后延至公元前2100年或2000年。是一支历时长久,分布于长江下游强势的考古学文化,留下大量的玉器。良渚文化大致可分早中晚三期。[46]大约良渚文化中期晚段至晚期时,在玉器的类别、尺寸、造型、纹饰主题上,发生明显变化。[47]
譬如:崧泽晚期至良渚早期流行的所谓“龙首纹”,到良渚中期时就逐渐少见,终至消失。图一四就是清末金石学者端方收藏的所谓“龙首纹镯”,流散海外,成了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藏品。[48]由于明晚期至清代,流行将古玉染呈褐色,甚至将原本较浅的纹饰,用砣具再加深刻,所以图一四通体呈现褐红色。这类玉器曾被古董界称为“蚩尤环”。[49]
良渚早期的瑶山遗址虽出土形似小璧,被定名为“圆牌”的成串佩饰,但不出土真正的玉璧。也属于良渚早期,但比瑶山略晚的反山遗址,大量尺寸介于13.4至19.9厘米的中型玉璧,也只集中于第14, 20, 23号墓,[50]而这些墓中不出现雕有“龙首纹”的玉器。
良渚早期墓葬中,被今日考古学家称为“琮”的玉器,实际是雕琢神徽式花纹的手镯或臂钏,器外壁多修琢成弧形,它们的创形理念与“方”无关,从埋藏现象推测,它们显然不是专用以祭祀地祇的礼器。笔者怀疑,在上个世纪80年代晚期,张陵山、瑶山、反山发掘时,如果当时的考古学家脑海中没有被晚清金石学家吴大澂、端方的著作误导的话,只看玉器出土位置,应该不会称图一五至一七这类玉镯或玉方鐲为“琮”。[51]稍晚发掘的普安桥、新地里遗址,人骨保存较好,更见这类玉镯直接套戴墓主手腕。[52]
值得强调的是,良渚先民制作这类玉镯、玉方镯时,设计重点是在外壁浮雕四片琢有特殊面纹的长方形饰片,今日称之为“射口”的部位,只是雕琢饰片时在其上、下留下的光素窄边。
累积四、五十年考古资料可知,良渚早晚二期在玉器上最大的差异是:良渚晚期才出现高大厚实、外壁平直,剖面呈方形的“琮”,它们不能被套戴于手腕上。与之相匹配的,良渚晚期的玉璧也增大体量,出现直径二、三十厘米大型璧。璧与琮除了尺寸加大、中孔缩小,无法套戴于腕部外,玉料也多选择一种深浅交杂的深绿色闪玉(Nephrite)。[53]在部分良渚晚期的大璧与高琮上,刻画了可能用以通神的密码式符号。笔者自1992年起,即致力于良渚符号的研究。[54]
回忆1990年我初访杭州认识牟永抗先生以后,彼此间开始多年的辩论,焦点在于良渚文化到底有无“璧琮组配”的礼制?最初牟先生坚持,从墓葬布局中看不出璧与琮有组配关系。这样的观点后来也清楚记录在反山正式报告中。[55]但当时我提醒牟先生需正视一个现象:那些轻浅的,与天象有关的符号(鸟立高柱、祭坛、飞鸟等)只刻在大璧与高琮上,换言之,“璧与琮是通神符号的唯二载体”。牟先生当时无言以对。
后来牟先生赴美检视弗利尔博物馆所藏几件刻有符号的玉器,又在旧金山亚洲美术馆发现一件良渚玉璧的器缘刻了一周“交互双L形符号”后,1999年牟先生发表《关于璧琮功能的考古学观察》一文,宣称“良渚文化中,璧与琮是既有分别、又有内在联系的两种玉器。”[56]
2002年笔者的专文与2015年良渚博物院出版的专书,[57]是有关良渚玉器刻画符号资料比较丰富的二份出版品,但可能还没有收集完整。迄今保守估计大约有19件璧、12件琮,它们都是良渚晚期晚段风格,其中属正式考古发掘的有:玉架山(璧1)、朱皇庙(璧1)、少卿山(璧2)、蒋庄(璧1),但还是无法在出土墓葬里看出璧与琮有组配摆放的现象。换言之,能确认良渚文化璧与琮之间应具组配关系的唯一证明,仍只是:“它们是通神符号的唯二载体”。
事實上,从玉器所透露良渚早晚两期宗教信仰最大的变化是:良渚早期的宗教型态是单纯的“动物精灵崇拜”(可简称为“物精崇拜”),大部分的玉器都可纳入“宝玉衣”的范畴,[58]也就是巫觋们穿戴披挂于头、颈、胸前、手腕,或缝缀在法衣上的,以神灵动物(鸟、兽面、龙、鱼、蝉等)为主题的各式玉饰,它们形制各异,但纹饰主题一致。图一五至一七這种雕纹玉方鐲,也是“宝玉衣”行头之一,且男女均可配戴。
反山遗址裡较晚的墓葬中出现大量不能穿戴、只能堆叠的中型璧,就意味着另一种宗教思维的兴起。[59]事实上,除了大量堆叠中大型玉璧外,还出现一件圆片方筒迭压造型的玉器,也就是所谓“玉琮王”,笔者怀疑,这或是通过上层交流网,接收黄河上中游 “天体崇拜”信仰后发生的变化。
百余年来,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均,导致大陆考古工作资源分配极度不平衡。黄河上中游疆域广袤,[60]有关史前玉器的研究迄今仍在起步阶段。但若以不多的考古出土器为基点,串联数量庞大的传世器与可靠的流散品,[61]已可建构基础轮廓,证明“天体崇拜”信仰,与“制器尚象”“同类感通”的思维,极可能源自黄河上中游史前文明。
陕西高陵杨官寨庙底沟文化遗址(约公元前3637至前2918年)出土一件径达16.9厘米,颇端正的石璧,以及二块石琮的残片,三者分别埋藏。图一八为一件石琮残块,孔缘无射口。[62]图二一玉琮与一件径达18.6厘米,制作甚精致的玉璧,同出于师赵村第七期8号墓,属齐家文化早期,年代约公元前2300年前后。[63]换言之,从庙底沟文化到齐家文化(约公元前3600至前1600年),是黄河上中游先民制作带大圆孔的圆形、方形玉石器传统,从萌芽、发展至高峰的全历程。从整个中国玉器史可知,这样的圆、方带孔器,应就是文献记载的“璧”与“琮”。它们在现实生活中毫无功能,极可能是祭祀天神、地祇的礼器。
夹在庙底沟文化至齐家文化早期之间的六、七百年(约公元前3000至前2300年),围绕着陇山的广袤大地(今日甘肃、宁夏、陕西),发展了马家窑、半山、常山下层、菜园、客省庄等文化,可泛称为“先齐家诸文化”。从考古资料可知,這時段也是璧与琮(在祭祀后?)被分开掩埋,逐渐发展到成组,甚至上下叠压掩埋。这时段也是“琮”由 “无射口”发展到 “有射口”的时期。图一九、二0两件正是这过程中的产物。
图一九为考古出土器,但报告尚未出版。[64]甘肃广河是半山文化发展至齐家文化的地区,玉器珍贵且坚韧,较早的半山文化玉器也可能出现在较晚的齐家文化地层;大半个世纪前,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即在该处采集与图一九相似,更为短矮的无射口方琮。[65]图二0是宁夏隆德页河子早年采集的石琮,该地区分布常山下层文化(年代上限为公元前2930±180年)、菜园文化(公元前2500-2200年),此二文化彼此相似,都与齐家文化的形成有密切关系。[66]图二0石琮内壁钻凿工艺十分粗陋,固原博物馆展出时定为“约5000年前”。即约当常山下层文化阶段。事实上,在传世器、流散品中,颇多与图一九、二0相似的,简陋粗工的玉琮。
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北京大学秦岭副教授在陕西宝鸡市岐山县京当乡双庵村发掘了一个客省庄文化灰坑(笔者怀疑是祭祀坑),无他物,仅在一平置的残存约半的玉石璧上,压放着一件有极浅射口的玉石方琮,璧与琮的石材甚为相似。[67]双庵白石琮与图二0页河子灰青石琮相似,但整体比例更扁矮,圈形的射口虽极浅,但明确。虽然双庵遗址尚无碳14测年数据,但从形制特征可确知,双庵石琮应早于图二一师赵村出土玉琮,后者闪玉质,器身微歪,但射口较高,制作工艺较难。
双庵遗址“方琮叠压圆璧”的场景非常重要,证明在黄河上中游不具生活实用功能的,带中孔的圆形、方形玉石器,确实等数量组配,并埋藏于无人骨、陶器的坑内。虽因长期受土层挤压,出土时二者中孔并未完全扣合,但仍保持琮上璧下的相对位置。但此一遗存,无言,但强烈地暗示真正的“天体崇拜”“感应哲理”“璧琮礼制”“圆方叠压”应源自黄河上中游。事实上,在先秦文献中“制器尚象”及“感通”的观念,主要记录于周文化圈的文献《周易‧系辞》中,也间接证明感应观的源起地区在黄河上中游。[68]
双庵资料给我们一个提示:史前先民不辞辛苦地在方琮中孔上下孔缘琢出一圈“射口”,其目的或为了卡稳璧、琮间的斗合。这充分说明黄河上中游史前玉琮的“射口”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制作。与前文所述良渚玉镯、玉方镯的“射口”,只是制作长方形饰片的“留边”,二者是完全不同的制作理念。
迄今,连同双庵、师赵村二份资料,在甘肃、宁夏、陕西,共查知有九处(一处墓葬、八处祭祀坑)出土等数量的璧与琮,少则一组璧琮、多则四组璧琮,常有玉质一致、大小相匹配的特征,但可惜这些征集资料已不详当初摆放关系。若以师赵村玉琮(前文图二一)作为齐家文化早期的标竿,可将射口更短矮,多呈浅圈口的玉石琮共三处归为先齐家诸文化阶段,射口较高的六处归为齐家文化。近日笔者已发表论文详述之。[69]
图二二是出土于陕西宝鸡扶风县城关镇案板坪村的一璧、一琮,[70]笔者见过实物,确知二者玉质相同,[71]且二者的中孔相当精准可以上下套合。从全器造型端正、射口已较高的形式观察,图二二玉琮年代应晚于图二一师赵村玉琮。
图二二玉璧、玉琮的绝对年代虽较晚,但从杨官寨、半山、双庵、页河子、师赵村一系列资料,引导我们思考,将带中孔的圆片、方筒叠压的行为,不但根植于史前黄河上中游的“天体崇拜”信仰,且这种信仰与“制器尚象”“同类感通”的思维,可能曾经由“上层交流网”的运作,影响到不接壤的长江下游。催生了良渚文化内部的变化,良渚人因而创作了图二三这件精妙的玉器,考古编号:反山M12:98。[72]这种形制在良渚文化找不到渊源,却与遥远的黄河上中游祭祀坑中的场景相似。
有学者分析图二三玉器的造型:“上下的圆视为天地,把贯穿上下的射孔视为通道和主柱,那么这一复杂几何形式的立体是当时天地宇宙观的象征”。[73]笔者认同此说,但需强调:这样精彩的剖析,只适合解读反山M12:98及极少数与之造型相似且体积硕大的玉器,而不宜将之全面解读如图一五至一七那样体积适合套戴手腕的玉镯。
更需强调的是:只有黄河上中游史前先民赋予“射口”以“贯穿上天下地的通道”的功能。对良渚早期先民,他们没有刻意制作“射口”,那只是制作“雕纹饰片”的“留边”罢了。
广面思考下,笔者建议或可将图二三这件奇器暂定名为“璧琮”。
反山遗存的年代可能不晚于公元前2600年,但那些出土古朴玉石璧、琮的遗址,如:宁夏海原、固原,甘肃甘谷、广河等,年代数据也是落在庙底沟文化之后,齐家文化之前的所谓“先齐家诸文化”的年代范围内(公元前3000至前2300年)。
考古学家应该认真探索“天体崇拜”“璧琮组配”礼制的源起时间、地区、发展脉络,以及是否?如何?通过不接壤的上层交流网,在公元前第三千纪的前半,影响了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令此一高度发展“物精崇拜”的文化发生质变,在良渚文化晚期发展了“非典型璧琮礼制”:也就是墓葬中看不出二类玉器的伴随关系,但在良渚晚期晚段的部分玉璧与玉琮上,雕刻了“与天象有关的符号”。
四件器缘刻有符号的良渚玉璧
良渚文化晚期玉璧、玉琮上用极轻浅的断续线条刻画的,除了少数简单符号外,多半是“飞鸟”“立鸟”“阳鸟(背着太阳的飞鸟)”“立柱”“卵”“祭坛”,以及“交互双L形”符号。前述几种还常组成“鸟立祭坛”的构图(图九、一0、一一)。探索符号的深层内涵,多与“天象”以及“鸟生神话”有关。
迄今为止,只有四件玉璧,在其磨出微凹的器缘,琢有神秘的“交互双L形”符号。其中三件流散欧美,一件曾典藏在台湾。这四件玉璧器表所刻符号公诸于世的过程,笔者均亲自参与或独力完成:笔者或新发现过去未知的符号,或据实物绘图、测量、记录各符号彼此关系,更绘制可供直观即能了解的线绘图。主要的中英文论文共8篇,较重要的4篇见附注。[74]
如第二节所述,自1963年以来,已陆续有学者撰文报导弗利尔博物馆藏良渚玉器上的刻画符号,林巳奈夫教授据实物所绘符号的线图,就是重要的先驱工作。
1992年,笔者专程赴弗利尔博物馆库房仔细检视实物,找出前人未曾找到的“山丘符号”,(刻于图二四~4面上)并测量各符号的实际尺寸、记录各符号相对位置,制作较直观易懂的线绘图。[75](图二四~4,5)
1995年笔者出版《蓝田山房藏玉百选》一书,发表蓝田山房所藏良渚文化玉璧(图二五)。[76]该玉璧亦参加1995-96年,台北故宫举办的“群玉别藏特展”。[77]
伦敦的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藏一件良渚晚期大玉璧,径达32.5厘米、厚约1.55厘米。是四件玉璧中最厚大的一件。器边缘所刻符号最初被屈志仁先生发现,并于1988-1989年报导,文中公布玉璧全器及窄缘上的一只飞鸟的黑白图。[78]笔者于1995年夏,赴该馆检视并测量、图绘各符号,复原为图二六。该馆刘明倩研究员于1995/96与2006年,先后发表全器彩图及窄缘上的符号图像。[79]
旧金山亚洲博物馆所藏的良渚玉璧也很厚大,是1995年牟永抗先生在观察实物时发现全器边缘刻有一周,共22个结构相同的「交互双L形」符号。但牟永抗先生仅告知笔者及其它学者,并未绘图,亦未详加记录。笔者1996年前往该馆,测量记录并图绘。1999年该馆的贺利研究员正式发表该玉璧的彩图(图二七~1)。[80]目前该馆网络公布全器及窄缘上的刻符。
这四件极为珍贵的玉璧,周缘都磨作内洼状,在蓝田山房玉璧的一面器表刻绘了“立鸟‧高柱‧祭坛”符号(图二五)。在弗立尔美术馆玉璧的两面各刻绘一个“鸟立祭坛”,一个似“山丘”的符号。(图二四)二符号在璧的器表的部位并不完全一致。
在蓝田山房玉璧、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璧、弗立尔美术馆玉璧的窄边,各有:三、二、二只飞鸟,头像一致地展翅飞翔(图二五、二六、二四)。在弗立尔美术馆玉璧的窄边还有看似鱼骨头(?)的符号。(图二四)
飞鸟或游鱼(?)呈三分或四分的布局分布于玉璧的窄边上,在这些符号之间又各刻绘三个或四个“交互双L形”符号。只有亚洲美术馆玉璧上,没有鸟、鱼(?)的符号,只在窄边上刻画连续的二十二个“交互双L形”符号。(图二七)
窄边上的“交互双L形”符号不是以一根细线做连续回绕的“云纹”,它可能脱胎自良渚中期反山十二号墓玉瑁上的“交互螺旋线”。(图二八a,b)[81]是作两个“L”形密闭回绕线分别自左右两端,依顺时钟或逆时钟方向旋绕,形成有如两手相互扣合的样子。
“交互双L形”符号可分为:简式、变化式与复杂式三种。为清楚显示细微处差异,着以红、蓝、黑色,列于表一:
A、简式:最接近“交互螺旋线”的结构。不过有时会在上下外缘加刻细直线,如表一:2。
B、变化式:就是在“L”形非密闭的一端,其中一条线继续延伸回绕。
C、复杂式:就是在交互相扣的两个“L”形之间,又多出一道“S”形线条,也就是在红色与蓝色的“L”形之间,那根黑色的线条。
「交互双L形」符号究竟隐含什么象征意义呢?它这种「一来一往」「交互运作」的线条结构应基于「二元」观,是否当时已有了「一阴一阳」的观念?是否代表宇宙中阴阳二气交互运作?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若然,它可能是迟到宋代才形成「定像」的太极图的史前滥觞。
总结第三、四两节,良渚文化晚期晚段的大璧与高琮,确实不是巫觋穿戴佩挂的行头。虽然从墓葬布局无法证明它们是成组礼器,但只有大璧与高琮上可以刻画这种与“天象”及“鸟生神话”有关的符号,笔者将之释为“先民与神祇对话的密码”,所以,笔者认为良渚文化晚期才出现与“天体崇拜”信仰有关的“璧琮组配”的礼制。[82]
近年学者对海外良渚玉器的误判
前文第二节笔者已透露,近年有关流散美加地区良渚古玉的西文论述,尚有待议之处,既有以真为赝,也有以赝为真的情况,必须深入探索。
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M)藏品编号为918.7.136的玉镯,1971年首度发表于该馆玉器图录,订为“汉代或更晚”。[83]笔者于1980年亲赴该馆检视实物,发现在这件浅黄绿莹润玉镯的外围,浅浮雕8个椭圆片上,以断续的阴线刻绘大眼面纹,在每个椭圆片之间的器表,另刻画“斧头形纹”,笔者当时据实物所绘线图发表于1986年拙文,当时笔者虽将之归入良渚文化系统,但因为与出土玉器上的大眼面纹不完全一样,拙文仍将之暂订为东周。[84]
林巳奈夫先生也前往观察实物,再度仔细绘制了更精准的线图,(图二九~3)发表于1999年的专书,书中将玉镯订为良渚文化。[85]2006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沈辰副馆长撰文发表,亦订之为良渚文化,公布全器及局部彩图,(图二九~1,2)可清晰看出浅黄绿莹润玉质,局部有裂璺及浅褐色斑。[86]经过林教授、沈馆长的观察、绘图与发表,可确认虽然迄今尚未从良渚考古遗址出土与安大略玉镯完全相似的玉器,但该器无论在玉质特征,玉镯外围浮雕多个动物面纹的造型,以及轻浅断续阴线的刻纹技法,均属良渚文化风格,基本排除它是新石器时代之后作品的可能。
但是苏芳淑教授在其2019年新著中,推测安大略玉镯,与哈佛大学所藏温索普玉镯,二者所用色泽清亮的玉料来自新疆。[87]
温索普玉镯属哈佛大学的温索普收藏(Winthrop Collection)编号1943.50.490,即本文图一二。前文已提及罗樾教授1975年书上把该件玉镯订为“时代不明”。但1980年代以来,不但发掘了大量良渚玉器,且浙江余杭汇观山出土一件玉镯,(图三0)形制、纹饰与温索普玉镯相同,即是围绕外圈横向排列同样的大眼面纹(考古报告常称为“神兽纹”)。[88]温索普玉镯较大,琢有八个面纹,汇观山玉镯稍小,琢有五个面纹。
根据苏芳淑教授2019年新书公布的彩照,[89]及书中的描述,温索普玉镯外表大部分是褐色,苏教授认为是盘玩所致,[90]但该器内壁有一块保持原有的浅青绿色;所以她断言:温索普玉镯和安大略玉镯的玉料都是典型新疆玉料,清乾隆皇帝在1759年克服新疆后,很易获得这种玉料。所以她直言温索普玉镯可能是清代时宫内制作的仿古玉,意味安大略玉镯或亦相同。[91]
事实上,良渚文化的时间跨度大,在玉料上也有早、晚之分,大致而言良渚晚期较常见深褐绿的大璧、高琮,但良渚早期多选用浅青绿、黄绿,透明度甚高的闪玉,制作的器物体积多不硕大,有学者分析良渚玉料特征时,称这种为“黄白玉”。[92]在太湖以南的浙江反山、瑶山、汇观山等地出土者,多深沁为乳白色(如图三0),但在江苏张陵山(图三一)、[93]上海福泉山良渚遗址中,都有保持原本浅黄绿至青绿莹润色泽的出土器,色泽与安大略玉镯非常相似。这似乎是研究良渚文化学者們的通识。
总之,笔者认为温索普玉镯(图一二)与安大略玉镯(图二九)都是良渚文化玉器。前者形制纹饰已有汇观山出土玉镯为证,后者器上轻浅断续的刻线,也是典型良渚风格。明晚期以后的仿赝良渚玉器,刻纹多直而深,下节将举例讨论。
海外良渚玉器的新研究,除了这般“以真为赝”外,也出现“以赝为真”的情况。
在1927-1928年间,加拿大多伦多市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经由怀履光主教的努力,入藏27件吴大澂旧藏玉器,本即为海外收藏吴大澂藏玉的重镇。[94]2012年,该馆接受社会人士捐赠一件,曾为清末收藏家吴大澂所藏的玉璧。(图三二)由于该玉璧所附木座上刻了23个字,记录该璧是吴大澂用一件青铜尊向南浔顾氏换得,沈辰副馆长乃深入追踪调查,并撰文说明探访经过。[95]该玉璧也参加了2017年,苏州博物馆举办的“梅景传家-清代苏州吴氏的收藏”展。[96]
笔者认为该玉璧既曾经名人收藏,流散海外故事曲折,能归入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但对于被推定为“良渚文化玉璧”,则不以为然。因为从图片显示器表密布一条条不自然的牛毛式黑色细沁班,以及不合良渚玉璧的尺寸规范(太薄),笔者怀疑它就是吴大澂生活时代,也就是19世纪晚期的仿赝作品。[97]
博物馆员不可对没有见过实物的物品,仅凭图片发表意见。不过我曾将我的怀疑告知沈辰副馆长,当时沈副馆长认为,可以将之先行发表,再接纳社会各方意见。
2017年这件玉璧参加了“梅景传家”特展,良渚文化古玉专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王明达研究员,亲自赴苏州鉴赏该玉璧,告知笔者该璧非属良渚文化。
除了这件璧外,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还藏一件径达48.9、厚达3.2厘米的大璧,该馆亦定为良渚文化。[98]笔者未见过实物,但观察图片,确知是一件难得的大璧,但认为该璧应不属良渚文化遗物。除了玉料色泽不像外,更因为该璧器表有明显的,看似砣具切割造成的“同向等径”弧形切割痕。真正的良渚文化玉器上,或为直条片切割痕,或为弧形线切割痕,若为后者,应该“同向不等径”,且弧痕之间会有明显高低起伏的波磔痕。
明晚期至民国初年仿赝良渚玉器的梗概
分析了近日出版西文著作,出现对早年海外流散品中所谓“良渚玉器”断代的问题后,笔者深感需要将明晚期至20世纪前半,市场上仿赝良渚古玉的发展,略做说明,提供读者日后检视各类藏品时的参考。但须强调,此节提供资讯,不包括对20世纪末以来,新起一波狂热赝品潮的鉴定观点。
如前所述,20世纪80年代之前,传世器、流散品中的良渚玉器,都被视为周代、汉代的古玉。明晚期文人笔记小说中,只见“古玉”一词,到了清代,普遍称古玉为“汉玉”。笔者怀疑是否因为当时统治者为满人,普遍以“汉人”“汉字”区别“满人”“满文”,所以也开始用“汉玉”一词指称“汉人的古玉”,有别于当朝时作的玉器。
明代中晚期时,江南地区经济繁荣,收藏古物的风气很盛,也就带动了制作赝品的风气。高濂(公元1573年-1620年)《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中清楚地记录制作赝品多为:“模拟汉宋螭玦勾环”,也就是雕琢“螭虎纹”的韘形佩、[99]带勾、小环等,文人能把玩的小东西。
清宫旧藏中,有的良渚玉器器表纹饰显然经过后世玉工用尖锐工具,按照原本已模糊的花纹,再度深刻过。图三三、三四两件都是很好的实证。由于清初康熙、雍正二帝对中国古玉无特殊兴趣,故这类改制品、染色品,可能是明代时改制染色后进入皇室收藏。
图三三可能是良渚文化玉梳背(考古报告多称作“冠状器”),下方可插有机质制作的梳齿。明代玉工改制了下缘,将器表原来纹饰加刻深,还在器的窄边加琢明代仿古几何纹饰。全器均染成褐色。
图三四可能是良渚文化,或与之相关的其它考古学文化的玉璜,[100]在其上下缘,分别琢五个、四个浮雕椭圆片,其上再以浮雕及阴刻表现大眼面纹(考古报告多称为“神兽纹”)。据笔者仔细观察,这件玉璜的两端龙鼻、口、牙,阴线宽深,可能是明晚期改制。上缘五个大眼面纹保留新石器时代纹饰,但已磨蚀不清,下缘四个大眼面纹,也曾被明晚期玉工用工具顺著原有纹饰加以深刻。林巳奈夫先生据实物绘制图三四~2。
明晚期玉工有机会将传世古玉上磨蚀不清的细密纹饰,用砣具或雕刀加以深刻,自然就熟悉了这种良渚文化面纹的构图。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光素的古玉,会被加刻这类面纹。前文图七介绍,出版于黄浚1935年、1939年两本书中的,刻有乾隆御制诗,又被王懿荣、王崇烈父子收藏的玉璜,骤视之,会以为就是良渚文化玉器,事实上,笔者2003年仔细观察,认为玉璜本身或为新石器时代遗物,但纹饰比例失当,线条宽深,整体僵直无神,应是明清时的仿作。笔者在2005年、2006年,两篇论文均有详细分析。[101]
台北故宫藏有一件十二桥文化中期(约公元前1000至前700年)玉琮,原本器表可能光素,或有简单几何纹,但可能在明晚期时也加刻了良渚式小眼面纹、大眼面纹。(图三五~2)纹饰线条十分生硬刚直,显然是玉工在摸挲过真正良渚文化玉器后,所模仿的作品。且这位雕纹玉工似乎也明白古人雕纹时,器物的大端向上。但是传到了十八世纪,乾隆皇帝为之赋诗,诗加刻在器壁四个直槽时,就以器身较大的一端向下,并为之配制木座和铜胆,用以盛水插花,所以图三五~1彩图显示,器身方凸块的纹饰是倒置的。
明晚期玉工既有将真正良渚玉器上模糊纹饰加以深刻的经验,(图三三、三四),又有在现成古玉上,加刻仿良渚面纹的经验,(图七、三五),所以当他们直接用玉料制作时,也会制作如图三六那样纹饰线条宽深,似古非古的作品。[102]流风所及,到了十八世纪盛清时期,这类小玉环的造型、纹饰,也成为皇帝选为仿制、吟咏、把玩的对象。而有了图三七那般的,刻有乾隆御制诗的仿古珍玩。[103]
不过,无论是明晚期玉工,或盛清时的皇帝,可能都不知道,他们所深刻、仿刻纹饰的玉器,是五千年前良渚文化的玉器,他们只知道那是“古玉”罢了。
笔者在本节举例说明,明清时玉工制作仿古器,会仿其基本形制及纹饰的大致结构,但因为明清时已用效率甚高的金属砣具雕琢纹饰,大致而言,明代金属圆砣的刃部较厚,制作的阴线较宽深;盛清时圆砣的刃部较薄,制作的阴线较细致;但无论明代或清代,玉雕的线条都算稳健平顺。不会雕琢出如图二五~2,玉璧窄缘上的符号,或图二九~2玉镯上的面纹,那般以轻浅、粗细不匀的细线,构成的符号或花纹。
到了二十世纪前半,因为頗多欧美人士热衷于购藏中国古物,因而沿海大都会中兴起所谓“洋庄”,即以欧美人士为对象的商家,所出售古董真赝杂陈。如本文图一三的赝品笔者也见过多件,基本上就是用砣具将深浅交杂的灰色石料,模仿良渚多节高琮粗制滥造而成,所刻纹饰更是宽深硬直。
总之,自16至20世纪初制作的仿赝品,与真正良渚文化玉器上刻纹差异甚大。因为良渚文化时期还没有金属,良渚先民只能用石英、隧石,或其它硬度更高的矿物,在硬度高达6-6.5度的闪玉上,一道、一道慢慢刻画出古拙、断续,但蕴含强大的信仰力量的纹饰。那与明清时使用高效率金属砣具制作的纹饰,是很容易分辨的。
附录:美国、欧洲散存良渚古玉及出版情况
① 表中《玉器时代》系《玉器时代-美国博物馆馆藏中国早期玉器》一书的省称,该书出版资料见本文附注2
② 官网一栏注记“☆”符号,表示该馆官网有良渚玉器图像资料
|
序号 |
博物馆名 |
出版品 |
官网 |
备注 |
|
1 |
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美国自然史博物馆) |
⑴,Childs-Johnson, Elizabeth,(江伊莉)Dragons, Masks, Axes and Blands from four Newly-documented Jade-working Cultures of Ancient China, Orientations, April 1988, Vol.19. no.4, pp.30-41. 文中报道该馆藏一件良渚玉钺。 ⑵,《玉器时代》图4-03璧,图3-22锥形器,后者亦可能属大汶口文化。 |
||
|
2 |
Art Institute of Chicago(芝加哥艺术研究院) |
⑴, Salmony, Alfred, Archaic Chinese Jades from the Edward and Louis. B. Sonnenschein Collection. Chicago, 1952. 此收藏佳,多件高大多节玉琮。 ⑵, 《玉器时代》 |
☆ |
|
|
3 |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 |
此原属私人收藏,1987年成立博物馆后,并未出版玉器专书。 《玉器时代》图5-21, 5-22为九节、十节良渚高琮。 |
☆ |
此馆和第9号弗利尔博物馆共用一个官网 |
|
4 |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旧金山亚洲博物馆) |
⑴, d’Argence, Ren’e-Yvon Lefebvre, Chinese Jades in the Avery Brundage Collection, The De Young Museum, San Francisco,1972. ⑵, He, Li,“Asian Art Museum Reopens Chinese Jade Gallery, ”Arts of Asia, Vol.29,No.1, Plate 1, 1999. Pps.54-67. ⑶, 《玉器时代》图3-14冠状器、图5-03单节琮式镯、图4-09璧都是良渚玉器,后者B60J957图周所刻符号的彩图,只发表于该馆官网,线图则见本文图二二。 |
☆ |
此馆藏二件可能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仿赝良渚风格玉器,编号分别为B81J1、B60J623,前者出版于江伊莉1988年论文fig28,误报导为良渚玉器。 |
|
5 |
Buffalo Museum of Science(布法罗科学博物馆) |
《玉器时代》图3-05玉镯订为良渚,应再审查。 |
该馆1975出版中国玉器书中无良渚玉器 |
|
|
6 |
Cleveland Museum of Art(克利弗兰艺术博物馆) |
《玉器时代》图4-10玉璧定为良渚,径达32厘米,厚仅1厘米,文化别应再审查。 |
☆ |
|
|
7 |
Detroit Institute of Arts(底特律艺术研究院) |
《玉器时代》图5-20為良渚九节高琮,甚典型。该馆编号68.261 |
☆ |
2019年笔者查访官网,仍注记公元前八世纪。 |
|
8 |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菲尔德自然史博物馆) |
⑴, Laufer, Berthold,(洛弗氏)Archaic Chinese Jades, Collected in China by A. W. Bahr now in 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Privately Printed for A. W. Bahr, 1927 ⑵,《玉器时代》书中图3-24为一组四件锥形器,有的器表纹饰似被改制 |
⑴与 ⑵均报道馆藏一件高27.2厘米的十一节高琮,器表腐蚀甚。但⑵ 图5-25误报道为十二节。 |
|
|
9 |
Freer Gallery of Art(弗利尔博物馆) |
⑴, Murray, Julia, Neolithic Chinese Jades in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Orientations. Nov. 1983 ⑵,《玉器时代》图3-10龙首镯(本文图一四)原属端方旧藏。该馆最有名的刻有符号的四件璧、一件筒形镯均于书中出版彩图。 |
☆ |
官网宣称有168件良渚玉器,且多名品。 |
|
10 |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 |
⑴,Loehr, Max, Assisted by Louisa G. Fitzgerald Huber, Ancien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Grenville L. Winthrop Collection in the Fogg Art Museum, 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ss. 1975. ⑵, 《玉器时代》图3-11即本文图一二的彩图。 ⑶,So, Jenny F.(苏芳淑), Early Chinese jades in the Harvard Art Museums, Cambridge, Mass. : Harvard Art Museums, 2019. |
早年温索普收藏属福格博物馆时出版⑴, 后拨交该校赛克勒博物馆。后与哈佛大学其他博物馆联合称为“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 |
|
|
11 |
Hermitage Foundation Museum & Gardens(爱尔米塔什基金会博物馆) |
《玉器时代》图5-18一件七节高琮属良渚文化。 |
||
|
12 |
Honolulu Academy of Art(檀香山艺术研究院) |
《玉器时代》图9-01玉钺订为崧泽至良渚,文化别应再审查。 |
||
|
13 |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印地安纳波利斯博物馆) |
《玉器时代》图3-23二件锥形器,应再审查。图5-02所谓单节玉琮,局部改制。 |
||
|
14 |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洛杉矶郡立美术馆) |
⑴,Kuwayama, George, Chinese Jade from Southern California Collections.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77.有良渚高琮。 ⑵,《玉器时代》图3-08玉镯、图5-07琮式镯、图5-23十节高琮均为典型良渚文化玉器。 |
☆ |
少量,但精致典型。 |
|
15 |
Lowe Art Museum, University of Miami(迈阿密大学洛尔艺术博物馆) |
《玉器时代》图4-01璧定为良渚,应再审查。 |
||
|
16 |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大都会博物馆,纽约) |
《玉器时代》图3-20半圆形饰、图4-04玉璧二件订为良渚文化。但官网上还发表九节高琮。 |
☆ |
|
|
17 |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明尼安波里斯博物馆) |
⑴,Na Chia-liang and Peterson, Harold, Chinese Jades, Archaic and Modern, from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The 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 1977. ⑵,《玉器时代》该馆藏二节、五节、七节玉琮各一。尚佳。但图4-07璧,径达28.89,厚仅0.32厘米,且玉质色泽均不典型。被订为良渚,值得商榷。 |
☆ |
|
|
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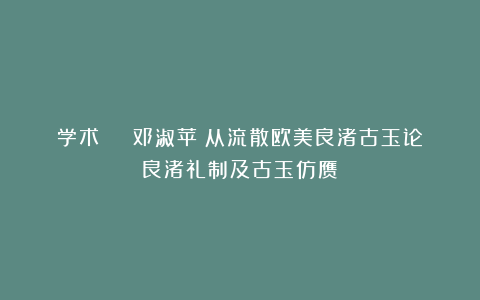 |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波士顿美术馆) |
该馆官网公布一件编号MFA-1990.313 (E5145CR-d1)的雕有神组面纹的半圆形玉饰。疑为瑶山盗掘品。 |
☆ |
|
|
19 |
Norton Museum of Art, West Palm Beach(诺顿博物馆) |
《玉器时代》图5-08为一件良渚早期琮式镯的残件,纹饰精美。 |
||
|
20 |
Saint Louis Art Museum(圣路易艺术博物馆) |
《玉器时代》图5-06为单节小眼面纹的琮式镯。但该馆官网公布一件良渚晚期十节高琮。 |
☆ |
|
|
21 |
Seattle Art Museum(西雅图艺术博物馆) |
⑴,Watt, James(屈志仁) , Chinese Jades from the Collection of the Seattle Art Museum, Seattle Art Museum, 1989. ⑵,《玉器时代》图5-11两节小眼面纹琮式镯(此造型常称为矮琮) |
||
|
22 |
University of Michigan Museum of Art(密歇根大学博物馆) |
《玉器时代》图9-05被订为良渚玉钺,应再审查。 |
☆ |
|
|
23 |
Royal Ontario Museum(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
⑴,Dohernwend, Doris, Chinese Jades in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Toronto. 1971. ⑵,沈辰, 古方主编,《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中国古代玉器》Ancient Chinese jades from 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文物出版社,2016。 馆藏一件典型良渚两节小眼面纹琮式镯(矮琮) |
☆ |
馆藏编号918.7.136即本文图二九,编号DSC_0090即本文图三二 |
|
24 |
British Museum(大英博物馆) |
⑴, Jenyns, R.Soame, Chinese Archaic Jades in the British Museum, London, 1951. ⑵, Rawson , Jessica ; with the assistance of Michaelson, Carol ; 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 London : British Museum Press, 1995 |
☆ |
此馆原有藏品已很丰富,本文图二中为高达49.5厘米高琮。 ⑵,为何东收藏寄存而出版。 |
|
25 |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维多利亚与亚伯特博物馆) |
⑴, Ayers, John and Rawson, Jessica, Chinese Jade throughout the Ages. Catalogue of an exhibition organized by the Art Council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London. 1975. ⑵,Wilson, Ming, Chinese Jades, Victoria & Albert Museum, Far Eastern Series, V&A Publications, 2004.(中译本书名见附注79) |
☆ |
本文图二一即为此馆所藏圆周刻有符号的玉璧。 |
|
26 |
Fitzwilliam Museum, Cambridge (剑桥大学菲茨威廉博物馆) |
James C.S. Lin., The immortal stone : Chinese jades from the Neolithic period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 London : Scala Publishers Ltd., c2009. 书中cat.3良渚四节琮,cat.3良渚玉璧。 |
||
|
27 |
The Guimet National Museum of Asian Arts(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 |
Tsao, Huei-Chung.(曹慧中), Jade from emperors to art deco, Paris : Somogy Editions d’art ; Paris : Musée natonal des arts asiatiques – Guimet, 2016 |
本文图一即该馆藏有名的吉斯拉玉琮 |
|
|
28 |
Museum Rietberg Zurich, Zurich. (苏黎世,里特贝格博物館) |
Marie-Fleur Burkart-Bauer ; fotos:Isabelle Wettstein, Brigitte Kauf. Chinesische jaden aus drei jahrtausenden, Museum Rietberg, , c1986 书中第17号是一件三节小眼面纹良渚玉琮,第2号可能是良渚玉璧。 |
||
|
29 |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Stockholm. (斯德哥尔摩,远东博物馆) |
☆ |
官网上有一件看似良渚琮式镯,不确定 |
|
|
30 |
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HM Gustaf VI Adolf)收藏 |
Gyllensvard, Bo and Pope, John Alexander, Chinese Art from the Collection of H. M. King Gustaf VI Adolf of Sweden. The Asia Society, New York. 1966. 书中第64号应是八节良渚高琮。 |
后记:
如提要所记,本文是2019年8月在故宫博物院配合“良渚玉文化论坛”要求所作口头报告后的论文,初稿曾发表于《中原文物》2020年第2期。再经修改增补而成。近日笔者论文《史前至夏时期 “华西系玉器”研究》分上、中、下,发表于《中原文物》2021年第6期至2022年第2期。对于黄河上中游等数量璧琮组配的九笔出土资料(一处墓葬、八处祭祀坑)已在该文详细说明,故在此文中略做删减。
注释 (滑动阅读)
原文来自:徐琳、顾万发主编《玉器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22年9月
点击链接 查阅书目
授权:邓淑苹
编辑:孙蒙蒙
审核:方 婷
关注我们,获得更多信息
投稿、讲座信息、资料、投诉可找博闻君(silkl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