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结
故乡对我来说,在许久以前是剪不断的情结,在现在是想割舍又难割舍的纠结,也像是我生命中很难拆开的死结,熟悉又陌生,向往又失落,牵念又疏离。也许只有当我生命终结时才能放下它,因为我的后辈们已经与它没有多少情感上的联接。
那山那水
故乡的山水,即使离乡已近五十年,我依然是十分熟悉的,开车不用导航,摸黑也知道怎么走,包括每一条小的岔道。只要记性尚可,这种印痕就会永远被留住,因为这是我出生和童年生活的地方,是我祖辈们的根脉所在。我想,这也应该是人的通性,不管走的有多远,离开时间有多长,故乡是无论如何都难以从记忆里消逝的,况且近几年,我偶尔还会因家事回去看一看。看一看故乡的山,故乡的水,故乡那些熟悉和不熟悉的小路,以及小时候留下无数笑声的水渠和池塘。
记得四十年前回汉中老家,交通工具只有两种,一种是火车,一种是汽车。坐火车要到武功县普集车站乘车,还要提前好几天购票,大约下午四、五点坐上车,第二天上午九点左右才能到城固柳林铺治江车站。火车走宝成线绕阳平关进汉中,于是凤县和阳平关两个地名从小就进入了我的脑海,过了阳平关,我就知道离家近了。因为坐的是慢车,火车行走在秦岭里,还要几次给快车让道,不得不在原地等待,那时没有手表,也无从计时,总觉得等待的时间非常慢长,加上过道拥挤,空气中五味杂陈,硬座时间长,所以对坐火车回老家从心理上总是很排斥、很畏惧的。坐汽车回家,一定要在宝鸡换乘,经凤县到汉中,那时盘山公路狭窄,汽车在转弯处与对面车辆会车,向下一看,如临万丈深渊,让人内心充满恐惧,双石铺和柴关岭两个地名至今仍记忆犹新。回老家就像当时的过年,那时过年远不如现在这样有如此多的、丰盛的美食和文化活动,但也正因为一年里节日的气氛稀缺,孩子们便格外期盼,回老家亦如此,在外漂泊的人无论归途有多艰辛,对故乡的牵念却总是很迫切的。
故乡在汉中一直是刻在我人生深处最骄傲、最深刻的印记。我从小就很自豪地在简历“籍贯”一栏写上“汉中城固”,然后等同学、朋友,甚至是后来的同事说一声“你们汉中好,人称小江南呀〞,心里总是有点美滋滋的感觉。我其实是不大喜欢炫耀的,但汉中除外,因为它给我童年生活留下的都是满满的幸福感。后来学了历史,看了些古籍,才对汉中有了更多的了解。汉中,古称南郑、兴元,梁州、天汉,因汉水而得名,秦代已设汉中郡,它也是汉家发祥地,刘邦从这里走向长安,刘备也因占据汉中才有了攻伐魏国、兴复汉室的胆气。偶尔通过网络看到一个视频,说刘邦当初被封为汉王,建立的王朝叫大汉,穿的衣服叫汉服,故而中原华夏民族才被称为汉族。作为一个根基在汉中的外乡游子,我怎能不心潮澎湃。至于近年被热捧的兴汉胜境、龙头山,因机缘不巧,我没有去过,也一直认为那都是经济利益推动下的产物,并不能成为汉中的名片,我的脑海里留下的始终是武侯祠、拜将台、周家坪的南湖,上元观的古会,还有静静流淌了几千年的汉江水,以及难以释怀的属于童年的风物和年节。人,即使时代再如何变化,怀旧的心理总是无法改变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汉中才是我熟悉的故园。
老家城固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城固在秦代时已设县,取名“成固”,南北朝时更名为“城固”,唐初一度改名为“唐固”,贞观年间复名“城固”,由名可见,这里在历史上就是军事要塞,城防稳固是由来的源头,距今近2400年的历史也为它增色不少。但最让城固人对外炫耀的可能就是从这里走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外交官张骞,有许多物种都是因张骞出使西域而得以引种中原,造福了千秋万代的后世子孙。城固米皮则是汉中米皮的代表,汉中蜜桔以城固桔园的最有名。
我的生活与“柳林”二字一直结缘。家乡柳林镇是城固县的西大门,家乡人俗称为“柳林铺”,东汉太尉李固的墓地就在这里,汉中机场处在街中心,当地人都叫它“柳林机场”。机缘巧合,一九七六年我们举家北迁后,父母所在单位叫柳林滩种马场,从小就耳熟能诵的诗歌贺敬之的《回延安》里也有个柳林铺,宝鸡的凤翔区还有个柳林镇,后来才知道,全国其实还有上百个叫柳林的地方,认同感如此强的地名全国可能也不太多吧,我的柳林情结由此产生。过去,汉中很多地方都是区辖公社,柳林镇的前身柳林公社隶属于文川区,这种历史特点鲜明的行政区划却是我们的下一代人所无法想像的。时代的发展在平凡人心中湮没了许多历史痕迹,就像现在的合村现象,若干年后,又有多少人记得曾经的地名、村名以及它们背后的历史印记。前几年眉县在争取设市时,其中地名征集候选中有个叫“眉阳”的,我用文学常识推演了很多遍,都找不到其中原由,后来偶尔看到一些史学记载才知道,“郿”是眉县的专属字,已有两千年的历史,后简化为“眉”,“阳”是因为先秦曾在眉县建平阳宫,“眉阳”相合是有很久的历史渊源的,想一想现在不爱文史的年轻人又如何了解这些呢。当然,舍区设镇是时代的需要,只是年代记忆同样属于历史需求,它承载着几辈人甚至几十辈人的生活传承。
从柳林铺街道西侧路口向北三公里就是我的祖辈们耕耘栖息的地方代家山了。之所以用“代家”起名,大概是因为当初姓“代”人家多的缘故吧。据村史记载,清朝顺治元年代姓由湖北麻城就迁居到此,从此繁衍生息,仅现在在这里生活和从这里走出的代姓人就有近千人。称之为山其实并没有山,顶多只相当于陕西关中人嘴里说的“坡”,远没有关中人眼里的土塬高。汉中很多地方起名都很有地域特点,有坡的地方常以山、岭、坪、坝、坡命名,有河道的地方常用湾、坎、塘、滩、川命名,处在交通要道的常称为关、营、铺、店、堡,有庙宇古建筑的地方则常称观和庙。像我们村周围就有段家山、崔家山、袁家坝,刘家湾、王家湾、新铺、上元观、余家塘、道姑庙、草坝岭等村镇,汉中市汉江南岸就是有名的大河坎,这与汉江川道冲积盆地的地理特点息息相关。
顺坡而上一公里,就到了老家屋前。记得过去生产队场院西边有条南北大渠,绕着小学和生产队院子流淌,旁边一条大道从村口直通向崔家山,与这条大渠相邻的还有一条斜淌的小渠,两渠交汇处的地方叫刘家湾。我家老屋的后面约一百米处东西还有一条渠,渠在房后旁边分岔向北流淌了一支,它们又与村西大渠相连,是我们几个生产队灌溉农田的主要水源。老屋南边约一百余米是一个池塘,过去村里养鱼种藕都在这里,既是鱼塘,也是藕塘,还是小朋友们戏水的水塘。池塘旁边有口水井,周围二十几户人家的饮用水就来自这口井,打水并不像过去关中人家使用辘轳,或打的是压水井,我们村里人都是把绳子在木桶把上系成扣,或者用扁担的勾搭挂住木桶把,将桶探下去左右摇摆提水上来。井口平时也不遮盖,沿口用石头砌成,略高于地面,显得原始、古朴,卫生不卫生,村里人并不在意,因为这口井养育了我们祖辈好几代人,不知道向上能追溯到什么时候,也从来没有人思考过这件事。
老屋的村落周围全都是水田,出村的路都沿着稻田走,所以村落的布局远不如关中村庄横成排竖成行来的方正,随方就圆的座落更符合它的特征,现在还是如此。但熟悉的老家却还是让我产生了很多陌生感,也许是在关中待的时间久了,时代变迁带来的南北发展上的差异让我对故乡的山水产生了既熟悉又陌生的距离感。进村的岔路口不再如记忆中那样宽阔显亮了,通向老屋的大路因为农家宅院的扩建被挤压的狭窄弯曲,生产队的场院也因为包产到户后废弃而盖满了房屋,灌溉的大渠有的变成了小渠,有的已经被填平,老屋两侧过去尚算宽阔的村巷如今也已变成了狭窄的巷道,遇到雨天,行走都要十分小心,私家小汽车要开回家是很考验驾驶员驾驶技术的。村里人吃水的井已成废井,池塘里的鱼、藕已经成为奢望,过去的菱角也已成为一种记忆。如果说过去的故乡在我心中就象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充满田园牧歌式的美好,现在的故乡虽也楼房渐多,但环境杂乱,在我眼里却如鸡窝洼人家,充满了荒朴感和沧桑感。
不知道是现在村里的模样还如过去一样,只是因时间太久,才让我与老家产生了距离感和陌生感,还是确实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加上叔伯邻里们因为利益的驱动和潜在的小农意识作梗,才让村里的现状与时代发展的步伐显得如此的不协调。
站在老屋前,我向前看巷口,知道不会再有大家一起蹲在那里吃饭谈笑的情景了;再抬头,看见的只是四角天空,天空上没有了那轮金黄的圆月,圆月下也没有站着那个快乐的十一二岁的少年。也许正如鲁迅所说:“故乡本也如此,一一虽然没有进步,也未必有如我所感的悲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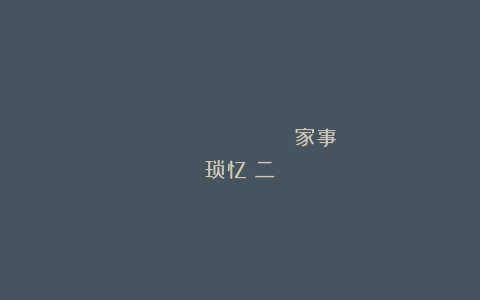
只要脑海里仍然留有故乡原来的痕迹,至少能在我后半生寂寞的时候看到一些抚慰。
那年那月
人到成年,尤其是中年以后,在经历了工作日日繁复的压力、抚育子女成长的不易、孩子工作和婚姻袭来的重逼、以及上老下小交织照管的忙碌之后,静下心来想一想,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才是中年的我们忆起时向往、寻求时无影却还时时在心里期许、嘴里念叨的完全自由的状态。
童年是自由的、快乐的。童年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说都是最无拘无束的年龄,对我这个八岁就离开老家、跟随父母北迁关中的游子来说,留在老家的童年生活在以后的岁月里再也找寻不到了。现在的孩子们,可供玩耍的方式和工具远比我们小时候要丰富,但空间却狭小了许多,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孩子们的天地在旷野和池塘,白云月亮太阳星星是他们最好的伙伴,他们不需要去知道山那边的世界是怎样的。那时关中的孩子主要的娱乐方式是堵烟囱爬树,撒欢儿摸瓜,滚铁环打弹球,玩烟盒丢方加上斗机。老家的童年娱乐方式却充满了地域特点。夏秋两季,是玩耍的最好时节,水稻快抽穗的时候,就是在稻田里捉泥鳅掏黄鳝的好时候,粗铁丝一端弯成钩,上面套上一截蚯蚓、洞口准备一个竹篓就是最好的捕捉工具,在稻田田坎边往往就会有丰厚的收获。这时候,池塘、稻田和水渠也是吊青蛙的好地方,一根小木棍或小竹杆一端系上绳子,绳子尽头系上用大头针弯好的小钩,上面挂上个小野花,就能够顺手吊蛙了。水稻快成熟的时候,是蜻蜓最多的时候,老家俗称蜻蜓为麻螂,只需找一根两三米的木棍或竹竿,顶端用柳条和铁丝扎成圆圈,上面缠满织蛛网,一个称手的捕捉工具就有了。汉中夏天潮热,蚊子又多又大,在蚊帐里放上五六个蜻蜓,就可以避免蚊子的肆意侵扰。透土蜂也是一项乐此不疲的活动,那时盖的基本都是土坯房,房后的墙皮在时间的侵蚀下往往开裂,这给土蜂栖息提供了良好的住所,墙上的小洞也成了小伙伴们的最爱,准备一个带盖的瓶子、一根小树枝,就不怕捉不到土蜂、吃不上蜂蜜,当然,被蜇的鼻红手肿也是常有的事,偶尔也会因为掰墙坯而掉进邻家的粪坑里,但记性在这时好像也不太起作用,土坯墙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采菱角、摸鱼也是水乡孩子们喜欢的活动,滚铁环打弹球最好的去处则是生产队的场院,平整、开阔,同龄的孩子们聚集最多的地方就在这里。最安静舒心的夜晚是坐在院子数亮亮飞机,因为老家离陕飞机场近,几乎每天晚上都能看见飞机升起、降落,童男童女们追逐着喊着亮亮飞机,快乐的笑声在夜空中回荡。童年的孩子们有时还回拿成年人打趣,记得有一次一群小孩追着一个骑着老式自行车的中年喊叫着:“陈广发,䅗墩墩,骑着毛驴串亲亲”,随后就是一阵爽朗的笑声。那时的童年至今让人向往,因为即使上了小学的孩子最多也只有六门功课,语文数学是文化课,自然、美术、音乐、体育都是身心放松的课程,那时的孩子们有大把的时间去玩耍,下午三点多放学,除了放牛、打猪草,其它时间完全由自己支配,放牛回家时,骑着水牛行走在田间小路上也是十分惬意的事。而现在的孩子却被囿于一隅,玩耍的空间和时间也被不断挤压,率真奔放的童年对他们来说是那样的陌生,这也是现代文明下的一种畸形、悲哀的现象。
童年尽管生活朴素却让我在记忆中不断回甘。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大部分地方生产资料极度缺乏,许多地方解决不了温饱问题,更谈不上有足量的肉食和佳肴。那时候,阶级成分很重要,农村孩子连上学都要填贫农、中农、上中农、下中农、富农(地主已经被打倒),阶级成分与升学、工作的机会都有很大关系,工农兵大学生也是需要根据成长表现和成分审核、经过组织推荐才能上的,政审在那时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关口。到了八十年代,与成分并行的商品粮和农业粮成了主流,政策的变化有时就决定了孩子们的未来。童年时在老家,庆幸的是我基本没有遇到过重灾荒。家里的成分是中农,有二亩多自留地,虽然那时水稻产量不如现在,但加上生产队的工分和口粮分配,主粮是不缺的,每年多少还有点富余。蔬菜、肉食在那时还是紧缺的,水果更是稀缺的好东西,家里养的猪,到过年时才能杀,大部分要卖掉换钱,用来购买生活用品,过年时母亲会去买点布,给几个孩子每人做一件新衣裳,记得那个时候,最羡慕穿藏蓝色中山装的人,认为他们都是当干部的、有文化的人,盼着长大了也自己也能穿上四个兜的中山装。杀猪后的肉往往只取一块用来过年,其余的肉腌制后挂成腊肉,过节或来客时才能吃到。最欢喜的美食是母亲做的粗豆腐,那是家里难得的牙祭,菜蒸饭和米皮也是大家喜欢的食物,菜蒸饭下面闷的多半是苕芽或野菜,即使很少见到菜油入锅,但已经能让童年的我们食欲大增。有两个情景至今回忆起来很有情趣,有点闰士在夜月下去扎獾的感觉。一个是小学一年级课间休息时,我们几个小男孩经常会从生产队场院西边的学校迅速跑到场院东边队里的牛棚,在牛槽里抓上几把饲养员刚煮好不久用来喂牛的胡豆(蚕豆),生怕被看见,转头一溜烟就又跑回了教室,在同学们面前炫耀美食,多少年后回忆起来与牛争食的情景,心里依旧有美滋滋的感觉;一个是每逢大年三十,守岁是老辈人的习惯,而童年的我们主要任务是抢牛,凌晨四点左右我就跑到队里的牛棚去争着牵牛,然后拉着牛到离老屋二百米左右有大碾盘的地方去碾磨早晨包元宵用的米粉,姐姐则早就在石碾旁先占位了,大家早起都是为搏个新年的好彩头,大年初一早晨,一碗醪糟元宵是城固人饭桌上的必备。吃完元宵天才蒙蒙亮,孩子们就带着老人们给的几毛一块的压岁钱,相约到东目山去扛一捆白甘蔗回来,然后到街上叫卖,顺便去看看舞狮和跑汉船,初一的街上是一年最热闹的时候,至今延续。六七十年代的生活,虽然餐桌上远没有现在丰富,但那种快乐和满足感却是现在的生活里怎么也找不到的。这也许就应了那句话:我们走了很远,却忘记了为什么出发。
多少年以后,我仍然对童年在老家时的生活情景充满向往,这也许就是我喜欢看知青和旧农村题材电视剧的原因吧,纯朴率性、自由亲切。等我再回到老家时,依然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寻找记忆中的影子,但似乎再也找不到过去的些许痕迹,内心的失落和怅惘便油然而生。
生活总是随时间流转,我们又哪里知道祖辈们年轻时候的情景,又怎能预设后辈们的未来。其实,童年的快乐只要能在晚年勾起一些美好的回忆,觉得生活有滋有味了,足矣,又何必去杞人忧天呢。
那屋那人
说到老屋,其实它早已经不在了,三十多年前老宅就已经卖掉了,新户人家还建宅于原址,每次回乡,我都会驻足呆看很久,老屋的原貌在脑海里也始终清晰可现。
老屋在我心里一直极有分量,那是母亲一生辛劳的缩影。记得在很多年前教学生学习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时,就不由自主的会想到南方房屋的结构,五十年前的老屋与归有光笔下的房屋结构大致相仿,这也是当时老家房屋普遍的结构。老屋是并排五间的大房,座北朝南,中间主屋外有两米多宽的长廊,屋架延伸出长廊,遮风挡雨,屋架下有数根立柱支撑。两侧房屋外沿和长廊外沿等齐,最东边是厨房,最西边是储藏间,中间是堂屋,东西两侧房间主门朝向长廊,正堂两扇门朝南,也是整个房子的主门,门柱下有石礅,中间其余两间睡房只有内门,经厨房内门穿过东边睡房内门进入堂屋,经堂屋再穿内门可直达西边睡房,西边睡房和储藏间的墙上并不设内门。这是老家房屋的普遍样式,只是根据庄基大小,盖的间数不同而已。那时候宅基地审批没有现在这么严格,庄基六七分地的非常普遍,大的可按亩论。那时的老家房屋还有两个特点,一是院子普遍大,没有围墙;二是虽然也因水田多的缘故相对分散,但只要有三五户甚至七八户人家住在一起,都成行成排,错落但有致。我们屋后是二爷和四爷两家,前面是同族一个太爷家,我们家东侧是一个族叔家,太爷家东侧是大伯家,大伯家东侧座东朝西的两家分别是四爷和一个族叔家,二爷家东侧也是一个族叔家。并排的两家之间有三米多宽的通道,南北通畅,因为都没有院墙,通道显得格外宽阔,通道就成了族里几家人午饭拉家常的好地方,回忆起来真有点“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感觉。老屋西边隔着我家的自留地,南面住的也是一个代姓本家人,北面住的则是父亲五爷家的后人,和我爷爷是堂兄弟,也是本家人了。整个村子绿树掩映,水田围绕,小渠流淌,池塘花开,“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这是何等美丽令人不能不长久怀想的田园稻乡呀。
老一辈人是牵动我乡情的导线。 村里人都按辈份称呼,我家前面住的比我年龄小的我要叫人家达达,西边五太爷家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后人,我也要叫声达达的,这种辈份的传承其实也是一种文化,同辈人姓名相连也是一种文化,我们的后辈是已经无法理解这种这种感受了,起名已经不再考虑族里同辈相连了。村里人对亲族的称呼也一直让我充满亲切感,离乡多年后再返乡,这种亲切感便愈加浓烈,双音节词是其最大特点。大伯我们要叫一声“大老”,族叔堂叔我们都称为“达达”,婶子们我们都叫声“新妈”或“妈妈”,族祖我们都叫“爷爷”、〝婆婆”,父亲我们要亲切地唤一声“爸爸〞,兄弟姐妹也必须以“哥哥”“姐姐”等双音节词称呼,表兄弟我们都喊一声〝老表〞或〝哥哥”、“兄弟〞,表姐妹我们还是要亲切地称一声“姐姐〞“妹妹〞。这种特有的乡音至今让我回味无穷,声音里面透着温暖,透着窖藏的醇香,让在外的游子时时牵念,难以忘怀。
我的长辈们是我眷念着故乡的最大理由。小时候有一年多,母亲和妹妹与父亲在关中生活,我和姐姐、爷爷一起在老家,二爷、四爷家成了我最大的依靠。爷爷喜欢喝茶,柳林街上有两家茶铺,爷爷和二爷是那里的常客,门一上锁,晚上两人才回来,我和姐姐吃饭就遇到了问题。老家那时一直是两顿饭,早上九点多,小学生放学回家吃早饭,十点多又去上学,大人们则在十点以后陆续出工干活,下午三点放学,大人们也陆续收工,吃午饭,四点多再次下地,孩子们则要放牛、打猪草,晚上七点左右陆续回家。晚饭一般不做正餐,饿了就用锅盔对付几口。遇到中午饭点,二婆四婆家的饭桌就是我和姐姐的吃饭据点,两位婆婆都唯恐我们吃不好,虽然资源有限,但也是尽量变着法子给我们做好吃的,有时妯娌两个还为争着叫两个孙子吃饭拌上几句嘴,几位姑姑则承担起为我们缝补洗衣、家庭管教的责任。有时候晚上我们也会在二婆或四婆家住下,因为爷爷有时回来的实在太晚,那时我和姐姐已经进入了梦乡。那段生活,最开心的是跟着几个爷爷、达达们到几里外的桃花店看电影,又在月光下笑着跳着回到家,最让别的孩子羡慕的是二爷家的小姑,她扮演的李铁梅十里八村都有名声,我也逢人就喊“我姑是李铁梅”,最让我泪眼婆娑的是一九七九年因爷爷去世我们全家回村,父亲场里派车把爷爷的遗体运回老家,办完丧事临走时,卡车已经起动,二婆在后面追着喊着,说要送给我们的东西没有带上,卡车却越走越远,二婆跪在地上哭喊的样貌我至今记忆犹新,也感怀至今。正是有着对这些长辈们从心底里溢出的、在血液里流动的情感,老家在我心中的份量才愈加厚重。
近几年,尽管时不时还会想起老家,但伤痛感和疏离感也在不断地刺痛着我。伤痛的是几位爷爷婆婆都已去世多年,我终究没有与他(她)们见上最后一面,还听说二爷当时安葬的不顺利,让我心里总有一个解不开的疙瘩。前些时候,住在老屋前面的、两年前回去老家还探望问候的长元爷爷也走了,三爷家的儿媳、我的一个新妈也离开了人世,志安达达被迫住进了敬老院,二爷家的达达和新妈也生活的很辛苦,一生性格开朗的姑父上半年也与世长辞,加上四年前父亲的去世、现在母亲的体弱多病,更让我体会到的是岁月的无情,故乡不再有朗月星空,树梢房屋甚至整个村子都仿佛笼罩在了雾气之中。疏离的是人事变迁带来的陌生感,回到老家,三五句关心问候之后,达达新妈、堂兄堂弟们说到的都是家长里短、如何挣钱,与我的共同话语已经不多,侄儿侄女们也只是在父辈们的引导下礼貌性问候,陌生才是关系的常态,我越来越感到故乡是看得见却看不清,回的了却摸不着,回乡的意义似乎正在淡却。
我的孩子没有在老家生活过,她也只是跟着我回去过两次,老家的亲人她大多都是陌生的,牵念对于她来说太过强求。有母亲在,有父辈们、同辈们生活在故土,与故乡的情感一息尚存,若干年后,也许真的就是天各一方了。高铁、高速拉近了空间上的距离,但心理的距离却随时间的流淌慢慢拉大。
对故乡情感上的纠结可能在未来还是难以打开的症结,回去的最大意义也许只剩下祭拜先人,慰藉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