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洛克的时代,人们开始认为他们可以运用理性来改良社会境况,因为理性毕竟已经通过科学改善了他们的物质存在。人们思忖道,如果存在着指引所有其他生物的自然力量,则或许也存在着指引人类的自然力量。于是,自由主义从自然法理论的襁褓中孕育而生。
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则属于较晚的世代,事实上他是处于第二波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最前线。就像早期的自由主义者,边沁也是启蒙时代以来的科学和技术进步成就的产物。他相信人可以运用理性改良自身,但是他认为自然法理论会走向哲学末路。他认为,只要社会中的人们相信,存在着一种“正确的行为”是可以通过积极追求“正确的理性”来发现的,则社会将会不断地产生变革。然而,一旦那些在位者认为他们已经找到了答案,则所有的公民将不得不遵从其领袖的理念,此时社会将失去活力而停滞不前。
功利主义与实证法
边沁并不主张自然中存在着一个绝对、永恒、普世的法则(即自然法),而人们必须根据该法则来治理他们的行为。相反的,边沁的自由主义是基于他对人类自恃的价值的信念。边沁拒绝自然法,而提出他自己用来评量人类行为的标准,他称之为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一书中写道,“自然已将人类置于两个主权者的治理之下,此即痛苦与快乐。”当痛苦极小、快乐极大时,便可以达成人类的幸福。因此,任何政策的价值或效益都可以用它带给个体或社会整体的快乐或痛苦的数量来衡量。边沁拒斥精英主义,而主张每一个人的幸福与任何其他人的幸福是相等的。此外,边沁相信,任何政策如果能够使“最大多数的人拥有最大的快乐”,则社会的福祉将达到最大值。边沁的主要兴趣在于功利原则或功利主义,他所从事的每一件事或撰写的每一篇稿子,几乎都是关于该主题的变种,他同时也阐述了一套实行功利主义的法律理论。
实证法(positivist law)是边沁对自然法的拒斥、他的功利主义,以及他的“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作为使社会的快乐极大化”的信念相结合的产物。“政府的工作,”他写道,“便是促进社会的幸福。”边沁认为,特定法律的权威与任何自然法理论家所相信的永恒的善或正义的概念无关,法律并不植根于绝对的、不变的真理,它不是人们应该予以崇拜且永恒不变的半神圣事物。在边沁的观点中,法律不过是一种工具,社会可以用它来修正其境况以增进它的福祉。因此,边沁的实证法理论将法律从早期自由主义者赋予它的崇高地位拉下来,使它回归到社会可要求其改变和改良的范围内。
虽然边沁视任何由正当权威所制定的法律都是有效的法律,但他并不认为每一个有效的法律都是好的法律。相反的,他将法律区分为程序上正确的法律与合乎正义的法律。边沁应用了他的功利主义试剂来检验法律的智慧,他想知道有多少人受到法令的负面与正面影响。
然而,如果一个社会想要采纳一个能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快乐的政策,它势必要有一个测量效益的方法。为了满足这个要求,边沁发展出了他的“快乐计算法”(hedonistic calculus)。这个精心设计的公式包含了人类的14种快乐、12种痛苦以及7个测量标准。边沁主张一个科学的立法机关应该采用这个公式来判定一项政策的智慧程度。这个快乐计算法并不实用,甚至有点可笑,但是它却源自一个可敬的关切:政府与立法程序的改良与民主化。此外,我们应该谨记在心的是,这个公式被提出的时代是一个人人着迷于科学的时代,因此它是出自善意的一个尝试:希望能够合乎科学地测量任何政策或法律的正义程度,而不是由立法机关一时兴起的慈悲或社会阶级的偏见来衡量。
边沁的贡献相当重要,他具有引领西方思维从自然法的绝对主义牢笼中脱困的远见。他的功利主义提供了一个测量特定政策的价值的实际准则。借由这些理念,边沁使自由主义有了新的方向——一个可以显著地改良社会境况的方向。在呼吁政府采取积极作为来改良社会方面,边沁为1830—1850年间英国所采取的许多改革措施提供了动因,其中包括文官制、秘密投票、议会代表权平等、扩大教育机会、动物的人道对待等。称边沁及其追随者给了英国一个新的社会良知,这种说法也许并不为过。简而言之,边沁堪称当代自由主义的创始人(参见第二章)。
民主社会主义
将功利主义与实证法引入民主理论,产生了一个全新的民众政府的概念。自洛克的时代以来,甚至是自麦迪逊的时代以来,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已经产生了彻底的改变。在17、18世纪,最可能压迫人民的事实上是政府,很少有其他机构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压迫民众。那些势力强大者,例如教会或地主阶级,几乎都是利用政府来支配民众。民主政治本身在当时相对未受到检验,所谓的民主政治经常堕落成暴民统治,并且最终演变成一人的独裁统治。
然而,在19世纪,民主政治取得了较大的成功,而且它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成长。这个新政治体系被称颂为由人民来治理,但另一方面,经济体系却似乎将所有权压缩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而且这个过程没有停歇,直到某个单一公司成为特定场域的主要雇主,甚至直接拥有一个城镇。薪资被压低,工时变长,安全设施被忽略,男人、女人甚至儿童都受到剥削。
显然地,人们可能遭到经济力的控制,就像过去他们受政府的控制一般。资本主义长久以来一直受到自由主义者的拥护,因为它倾向于提升个人的自由和平等,但现在却因其剥削人们的本事而受到质疑。渐渐地,那些位于政治光谱左侧的人开始感到纳闷:如果政府是民主的,而且如果社会上经济势力正剥削着人们,为什么人们不运用他们对政府的控制权来防止经济力的暴虐统治?这个新的关注彻底改变了自由民主主义,使它更趋向于社会导向,而减少个人主义的成分。虽然边沁是第一位现代自由主义者,但是他的思想只为看待民主的新态度铺平了道路,新理念的成熟还有赖于后续的数位思想家的成就。
🔳密尔
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边沁的学生,但他学识渊博、逻辑严谨、条理清晰的写作风格,使他超越了他的老师。他的知识力是如此的强劲有力,以至他普遍被视为19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密尔像边沁一样是一名政治活跃分子,他甚至在英国下议院待了三年。从早年开始,密尔便极为支持当时的社会运动,例如免费教育、工团主义、议会席位平等分配,以及取消农产品关税等。此外,他也是首倡女性平等的思想家之一。
密尔对于许多思想领域都感兴趣,包括哲学、逻辑学、道德学和经济学等。他最重要的著作《论自由》(On Liberty, 1859),可能是英语中关于个人自由最雄辩滔滔的论述。他在书中声称,虽然民主是比较好的政府形式,但即使民主政治也有限制个人自由的倾向。因此,应该给予言论和思想自由以法律之下的绝对保护,因为个人自由是达到幸福的最确定方式。
显然受到边沁理念的影响,密尔也是一名功利主义者。他推论道,幸福是社会的首要目标,而当人们彼此为相互的利益着想时,最能够达到幸福。密尔认为,仁慈对待他人的最原始动机便是开明利己主义(enlightened self-interest)。换言之,个体表现出良善的行为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最终将受益于这样的行为。然而,密尔又做了更进一步的分析,致使他推导出一个与支持开明利己主义动机理论的人们非常不同的结论。密尔声称,人们最后会变得习惯于做好事,即使他们不期待能够得到任何特别的奖赏,也将持续地这么做。换言之,密尔几近于主张人不必然是自私的,即便人是自私的,人们也能改变或控制他们的一部分天性。这种对于人性的乐观主义,即是典型的左派意识形态。
密尔的结论逐渐引领他走向对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的抨击,并且使他成为第一位抨击“资本主义的奴役能力”的自由民主主义哲学家。密尔的论证是如此的铿锵有力,以至于在他的时代以后,很少有自由主义者支持自由放任政策。在密尔之前,只有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与激进主义者这些极左派反对自由放任政策,然而在密尔的影响下,自由民主主义开启了一个向左转的运动,它视社会主义为比资本主义更优的民主政治的经济伴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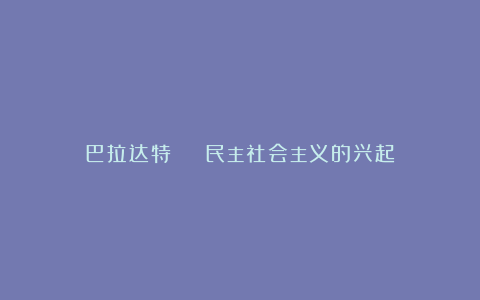
🔳格林
格林(Thomas Hill Green, 1836—1882)是一位英国道德哲学教授,后来成为主要的左派思想家。他像密尔一样极为关心个人自由。“我们或许将一致同意,”他写道,“被正确理解的自由是最好的祝福,达到自由是我们作为公民所努力的不二目标。”然而,格林小心翼翼地指出,自由并不意味着不顾及他人地做个人想做的事的权利。正如洛克所主张的,自由并不等于不受节制。为因应工业化加诸大多数人的经济与政治阻碍,格林将自由定义为:“所有人能够平等地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而释放自己的力量。
”格林以一种积极的、社会性的意义来主张自由,代表着自由主义思想另一次重要的向左转。
格林认为,个人的自由并不来自于人们能够追求他们自己的福祉,而是来自于人们能够奉献于社会整体。他反对洛克所构思的政府角色,即只作为个体纷争的被动仲裁者。相反的,格林认为政府应该采取明确的措施来增进人们的自由。他发现,社会中导致个人自由受到限制的因素之一便是私有财产。工业革命使大量的财富集中于一小群富有者手中,而被迫离开土地进入工厂的普通民众则必须依赖他人,依赖一个他们没有控制权的生产与分配体系,人们变得比过去更加受制于有产阶级的权势。格林认为这些趋势是不民主的,因此他鼓励人们利用政府机构(除此之外他们别无控制手段)来保护自己免受有权势者的经济力的压迫。这一立场无疑是福利国家(welfare state)概念的早期哲学依据。因此格林强力支持政府通过种种政策,例如免费教育、保护妇女与儿童的劳工法、卫生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其他积极措施,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格林认为,贫穷就像监狱一样使人不自由。如果这一见解是正确的,而且国家如洛克所主张的,负有增进个人最大可能的自由的责任,那么很显然,政府必须为公民的物质福祉负起责任。简言之,边沁、密尔与格林引领自由主义超越了政府对国民仅负有政治义务的信念。政府不可以将自身角色局限在打扫街道、追捕窃贼等事务上。相反的,正如洛克自己曾不经意地暗示的,除了完整的政治功能外,政府对国民尚负有社会和经济责任。
格林的理念对于当代自由主义运动至为重要,它不仅为政府积极行动保护公民免受权力的侵害(在边沁和密尔的传统中,人民对此是相当无助的)提供了哲学基础,还有更多的贡献。格林的主张将自由主义带离了孤立的个人主义,而走向社会良知与集体主义。这一趋势发展到最后,致使自由主义者支持了一个类似于卢梭(但不像卢梭那么极端)的有机社会的理论。不过,格林的自由主义是奠基于边沁的功利主义和密尔的开明利己主义,而不是任何的人权道德观。赋予自由主义在当代所具有的道德深度,尚有待另一名哲学家来完成。
🔳杜威
杜威(Library of Congress)当代自由主义(或者说社会民主主义)的主要的美国哲学家是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陈述了自由主义的目标,使得自由主义者试图改变政治机构以追求社会利益的哲学原则,完成了最后的建构。杜威强烈地信任人的智力与尊严,以及个体奉献于集体利益的力量与智慧。
杜威将自由主义带回其中心论题。他声称,所有人在人性上是平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在身体或心智能力上没有差异——这种论点是相当愚蠢的。然而,无论人们之间的差异如何,没有人比其他人更是人。每一个人对社会都有所贡献,因此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要求国家给予同等的政治与法律对待;而拒绝给予这样的对待,便是侵害每一名个体均有同等请求权的人权。重要的是,杜威声称,正因为人们之间存在着身体或智力上的差异,因此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对待更有必要;否则,那些力气或智力较贫弱者可能遭到强者的暴虐对待。
借由重新建构这个基本假定,杜威扩展了边沁、密尔与格林的逻辑。杜威同意个人的幸福是社会的主要目标,然而,他认为没有一项事物的定义是可以维持不变的;我们对所有事物的理解取决于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经验。这种经验主义的态度建立在杜威所支持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基础上。它倾向于认为,所有的知识都是试验性的、有条件的,因此幸福、社会、人权,甚至个体本身的意义,也是随着我们对环境的知觉的改变而不断地改变:“个体既然是现成的,便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杜威这样强调他的道德相对论,“一件事绝不会在孤立的情况下被完成,而是有赖于包含在’文化’经济、法律与政治等机构以及科学和艺术之中的文化与实体环境的辅助与支持。”
然而,杜威并不主张仅仅因为环境创造了我们的定义,我们就任由环境摆布。他与长久以来的自由主义信念相一致,认为人们可以应用他们的智力来解决面临的问题,从而使生活更好。
杜威关于真理本质在变动的信念,以及他对于人类理性能力的信心,使他提倡一种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他不像保守主义者那样认为现行机构本身即具有价值,因此不应予以干预;相反的,他是社会实验的狂热支持者,鼓励人们修正并调整现行机构以增加社会的福祉。柏克声称,现行机构是累世集体智慧的产物,因此任何单一世代都没有通过变革的方式来改良它的能力。杜威对此不表赞同,他写道,自由主义“对于积极地创造优良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等机构极感兴趣,就如它对于消除侵害与公然的压迫的兴趣一样。”因此,人们不仅能够修正压迫他们的机构,他们还应该更进一步地创造能够增进他们的幸福的机构。
杜威表示,人们应该对他们的社会从事研究,并且毫不迟疑地对现行机构进行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的变革。不过人们不应该仅止于此。他鼓励人们尝试塑造自身以改良人类,并且使他们在社会上更能,和睦相处。杜威的这一理念,的确与麦迪逊认为人性是恶劣的、不可改变的这种相当黯淡的观点大相径庭。“基于自由主义对实验程序的信奉,”杜威说明道,“它主张个体与自由的概念应与社会关系的变迁紧密联结,而持续不断地重新建构。”
这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哲学家对社会工程概念的崇奉,产生了巨大的效应。杜威的理念激发了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创造出“新政”、“公平施政”和20世纪60年代的“伟大社会”等政策。
本章与第四章所讨论的是民主的理论或原则,然而正如我们在第四章中指出的,民主政治包含了特定的程序与原则,因此下一章中我们将探讨当代民主政体中最重要的程序与机构。
#artContent img{max-width:656px;}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