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本文作者,原基建工程兵政治部组织部干事张佩芳,参与了兵种撤销前基建工程兵纪念画册的编辑工作。本文通过对画册光荣榜的深入解读,展现了基建工程兵部队在激情岁月里所获得的众多荣誉与贡献。这部纪念画册,是对基建工程兵18年辉煌业绩的倾情讴歌,是对部队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深情咏叹。
基建工程兵部队撤销前夕,兵种政治部经请示领导,拟出版一部全面反映基建工程兵部队业绩的大型画册。
兵种政治部领导牵头筹备,召集政治部有关人员反复研究,对画册的指导思想、基本内容、框架结构等形成共识后,做了分工:画册的主体部分,即摄影作品、美术作品和文字撰写,由宣传部、文化部和报社合作完成。画册的光荣榜部分,刊登全兵种部队所有获得二等功以上表彰奖励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等有关资料,由组织部负责汇集提供。
经过半年多的紧张工作,画册于1983年初出版,成为部队撤销后留下的珍贵纪念。
画册光荣榜收录了先进集体149个,先进个人226名。
如果说其中有什么特点的话,数量可观倒在其次,最主要、最突出的一点,是实施表彰奖励的部门五花八门,奖励名目繁多,蔚为大观。
例如,实施表彰奖励的单位除了军队以外,还有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冶金部、煤炭部、地质部、化工部、交通部、电力部、二机部、三机部、七机部,以及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北京市、广东省,共十六个部门(省市)。
再如,表彰奖励的名目,先进个人除了部队授予的荣誉称号和军功(一等功、二等功),还有地方性质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新长征突击手、三八红旗手等等,可谓琳琅满目。
这种现象只有在基建工程兵才可能发生,而在全军所有部队,各个军区、军兵种里,是绝无仅有的。原因很简单,基建工程兵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全兵种十多个指挥部(兵办),各有各的行业领导,十多个行业系统各有各的奖励名目,这是基建工程兵独有的特色。
这个特色的优长是显而易见的,部队担负的任务,涵盖国家众多的经济建设领域,涉及重要的国计民生,社会影响力广泛。
英模人物对部队和社会公众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在那个年代,建设“四个现代化”口号响彻全国,各项工作大干快上,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事业云蒸霞蔚,英模人物们凤翥龙骧,是他们,在为这支50万大军壮焰增辉。
在基建工程兵历史的天空,那些名字是闪亮的星。
兵种组织部是负责奖励工作的职能部门。但先进典型的发现、宣传和褒扬,组织部与宣传部、报社的工作各有分工,当然也就互有交叉与合作。
基建工程兵历史上,12支队111团姚虎成,是唯一被中央军委授予荣誉称号的英模人物,兵种机关专门召开命名大会,兵种领导全部出席,国务院副总理、基建工程兵第一政委谷牧颁发奖状,可谓影响巨大。
我到兵种组织部工作时,姚虎成荣誉称号的命名大会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从兵种机关到部队基层,学习、宣传姚虎成的热潮依然在持续。
发掘和报道姚虎成事迹的同志,主要是由宣传部的同事们,在姚虎成所在部队的协助下共同完成的。一场接一场姚虎成事迹报告会,由宣传部领导或同事出面去讲,许多报刊没有发表的细节,都可以在报告会上畅所欲言,加之报告的语言都是口语话化的,比报刊上的文章更生动,更富有生活气息,所以受到领导和基层官兵的广泛欢迎。
组织部有一个内部刊物《组工通讯》,下发全兵种组织部门,用以交流工作业务。王玉凌部长让我去找宣传部的同志,索要有关材料,在《组工通讯》上刊登姚虎成事迹报告,以及那些鲜活的部队学习姚虎成活动动态。
我去新闻科长兰书臣办公室,他绘声绘色地向我介绍了采写姚虎成事迹的体会。他谈到了一个独到的细节:姚虎成雪崩遇难,遗体从七八米深的雪堆中挖出来后,已经没有心跳了。战友们从他手腕上摘下手表,放在耳边听听,它还在滴滴嗒嗒分秒不差跳动着。
兰书臣说,他在姚虎成事迹报道中使用了这个细节,编辑称赞,读者感动,作事迹报告的领导讲到这个细节,会场上都是一片肃静,人人为之动容。
中央军委授予的荣誉称号,事实上是国家最高荣誉,因为,授予荣誉称号的命令由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签发,而我们国家的体制,军委主席同时也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所以说,基建工程兵部队奖励规格最高、奖励等级最高、影响最大的英模人物,非姚虎成莫属。
基建工程兵全部历史上,共有4个人曾获得过军队荣誉称号。除了前面说过的姚虎成,还有55团谢成华和301团马如飞,他俩的“模范共青团员”荣誉称号,是基建工程兵党委授予的;211团战士杨太平的荣誉称号“抗洪抢险英雄”,是南京军区授予的(杨太平牺牲于画册出版半年之后,故未能收录)。
授予荣誉称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纪律条令》规定的最高奖励,是国家和全社会对军人的崇高褒扬,除了打仗时涌现的“战斗英雄”,在和平环境,几乎没有任何人能在活着的时候得到过军队的荣誉称号。
以上4人,或牺牲或病故,他们获得的荣誉称号,都付出了年轻生命的代价。
采写报道马如飞事迹时,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曾有一个细节,让我心里难受了好一阵子。
马如飞的主治医生告诉我说:马如飞患上的是一种比较罕见的脑干肿瘤,有病理学研究价值。马如飞去世后,医院决定取出他的脑部,用福尔马林液保存在玻璃器皿中,供科研和教学使用。
医生一再叮嘱,这事千万不要在公开报道中出现。
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说出来,恐怕不必有什么顾忌了吧?
军队之外的荣誉,在那个年代,唯有全国劳动模范能与之相比。特别是遇到重大庆典,比如国庆活动每十年一次的“逢十大庆”,全国推选出来的劳动模范代表进京,参加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表彰大会,表彰令由国务院总理签发(那时国家尚未恢复国家主席制),逢这种机遇受到表彰的劳动模范代表,就属于地方性质的国家最高荣誉了。
画册光荣榜上,全国先进集体801团(原名为全国先进企业);全国劳动模范,24团解治国、401团杨正明,就属于上述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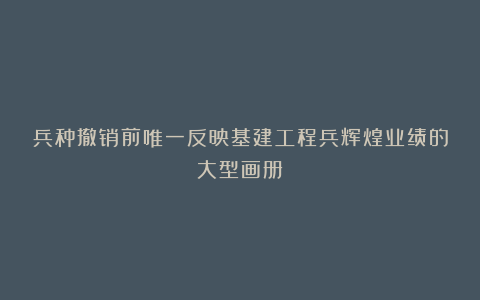
1979年国庆节,恰逢三十年大庆,国务院召开的表彰大会,他们被推选为全国先进集体和劳动模范来京参加大会,表彰嘉奖令由尚在担任国务院总理职务的华国锋签发,同时也是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大会上颁奖。
我认识杨正明时,他早已经是受过表彰的全国劳模了。
那次,组织部领导派我去河南平顶山煤矿,深入了解杨正明所在的401团8连团支部和青年团员,在施工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情况,打算通过总政报给团中央,为他们争取“新长征突击队”称号。
那时,杨正明还在8连当连长。到了平顶山,他首先领我去煤矿井下,让我对他们的工作有个直观印象。
401团承建的河南省平顶山煤炭,是国内少数大型煤矿之一,号称“高温矿”。由于地质情况特殊,水患、塌方和瓦斯事故等复杂情况偏多。
杨正明带我去下到地下近700米深的矿井,在掌子面上,实地体验官兵们掘进作业。
35度以上高温,蒸笼一样,井下基本上没有女性,许多战士光着上身,只穿一个裤头;震得耳膜几乎破裂的各种机器轰鸣,对面说话听不见;呛的胸闷的瓦斯气味,高强度的体力劳动,401团的官兵们在这常人难以忍受的环境中,劳动生产率创造了同行业全国第一名,井巷掘进连续3年超万米。尤其是8连,连续3年荣获井巷掘进国家等级队称号。
至于杨正明个人,得到的各种表彰和奖励,就太多了。深入的接触和了解,感到他确实挺了不起,全国劳动模范的盛名之下,是常人难以达到的业绩指标。
基层官兵得到这么高的荣誉,是评选活动中优中选优,在精英中选出更精英的结果,绝非偶然和侥幸。
这样优秀的连队,又有这样的先进人物作支撑,我撰写的8连团支部事迹材料内容就感觉太充实了。经组织部领导审核后报到团中央,最终如愿以偿,8连团支部被团中央评为“新长征突击队”。
共青团组织那几年开展“新长征突击手”命名表彰活动,全国县级以上共青团组织,先后命名了一百多万“新长征突击手”,可谓数量庞大。
基建工程兵画册光荣榜上,有7名团中央表彰的“新长征突击手”。他们7人中,只有904团技术员刘晓平,曾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1981年11月召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的表彰大会。
这次大会,是开展“新长征突击手”活动那些年,唯一的一次全国性表彰大会。
那时团中央颁发的奖状,“新长征突击手”前面,原本是没有“全国”二字的。(画册光荣榜上的“全国”二字,是编者添加的。)受到这次大会表彰的“新长征突击手”,才可以视为全国性荣誉。
那次,团中央分给全军部队10个“新长征突击手”代表名额,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及军委直属单位,共二十多个大单位竞争,最后,基建工程兵组织部推荐的刘晓平脱颖而出,完全凭的是过硬的事迹材料。
刘晓平事迹“牛”在哪里?撰写报给总政的刘晓平事迹材料前,我和刘晓平进行过比较细致的交谈,她的情况可以简单地归纳为四点:
一是她所从事的水文地质工作,搞孢粉分析,给人以神秘感,极易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二是她有知识分子背景,许多专业上的事,人们闻所未闻,使人有新鲜感。三是她刚刚二十几岁,一个年纪轻轻的姑娘就是中国古生物学会会员,中国孢粉学会会员,“招牌”比较亮眼。四是在实际工作上的确“有两把刷子”,凭苦干做出了贡献。如此而已。
刘晓平受表彰后,《解放军画报》曾对她有个专题报道,摄影师把她的彩色照片拍的很漂亮,她不仅在水文地质部队,在全兵种也有了名气,曾多次为部队做事迹报告。我们组织部的同事,参与了刘晓平事迹报告的整理,并把它用小册子印发到全兵种各个部队。
来之不易的荣誉,代价也是不小的。除了苦和累,没完没了的在实验室耗费青春时光,顾不上考虑个人婚恋问题。因为长时间接触化学药品,她得了接触性皮炎,起了一脸疙瘩,又痛又痒,一直发展到面部变形。
这对一个爱美的姑娘家来说,压在心头的重量是不言而喻的。我和她谈话时,她说经过治疗已经好多了,但脸上仍有隐隐约约的带血丝的红斑痕迹,虽然用药和化妆,依然瞒不过人。
以后是什么情况?兵种撤销后就完全不知道了。
光荣榜上先进个人中,除了国务院各部委表彰的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等地方性荣誉44人之外,还有一等功的12人,二等功的156人。批准立功的机关,有部队,也有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因为缺少原始资料,是否所有的人都是军功,待考。)
在和平年代,等级较高的军功,比如二等功,特别是一等功,其条件是很严格的。例如,多年后享誉世界的任正非,那时研制成我国第一台“浮球式标准压力发生器”,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支队党委给他记的是二等功。立一等功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那些数量不多一等功的荣立者,无非是两种情况——要么功绩卓著,有重大贡献;要么就是在非常时期,在随机事件中有特殊成绩,且社会影响较大。
例如,7支队61团战士张国安,63团工人万有,就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这一特殊时机,各记一等功的。
张国安和万有同在一个吊车组,吊车组与陆军38军官兵互相配合,在倒塌的楼房废墟中救人。那时我还在7支队宣传科当干事,奉命抽调到唐山救灾指挥部材料组,在救援一线,亲历了那个特殊事件。
地震已经过去13天了,倒塌的楼房废墟中已经没有任何生命迹象了,他俩操作的59号吊车,吊开楼板,救出了一个还活着的名叫卢桂兰的中年妇女。此事很快在救援一线引起轰动,军内外报纸电台争相报道,称之为“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他俩荣立一等功后,又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的表彰大会。
在北京指挥部所属的6、7支队广为流传的“蒋林川事件”,则属于一种更为特殊的情况。
蒋林川原是6支队51团一名战士(该团1978年划归9支队)。1976年,“四人帮”最猖獗时期,蒋林川用了四个多月时间,写出煌煌十二万言意见书,属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和所在部队番号,上书毛泽东主席、党中央,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痛斥“四人帮”祸国殃民。
随后,蒋林川遭到拘捕关押,开始接受没完没了的审讯。“四人帮”垮台后,蒋林川解放了,被破格提升为连队副指导员,荣立一等功,并当选为第十届团中央委员。人民日报曾于1978年刊登长篇通讯,报道蒋林川的事迹。
1978年,51团划归9支队建制后,有一次蒋林川到支队政治部来,准备由这里去参加团中央的一项活动,我和他有过简略的交谈。
蒋林川个子不高,略有些黑瘦,普通话里带着明显的江南口音,语速不紧不慢的,语气沉稳温和。如果不了解,真看不出他在面临大是大非时,那件皱巴巴的军衣所包裹着的身躯里,曾经一腔热血,壮怀激烈。
一个普普通通的士兵,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这份忧国忧民的情怀和胆略,得到一等功的荣誉,可以说是实至而名归的。
这部纪念画册,是对基建工程兵十八年辉煌业绩的倾情讴歌,是对部队先进集体和个人的深情咏叹。
抚今追昔,除了感慨,还有一个困惑不解之处。
光荣榜上一百多个先进集体暂且不论,先进人物除去当年已经牺牲和病故的,还有二百多人。这么多人,唯有二等功名单中的任正非,如今举世瞩目经常露面之外,其余所有人,可循音讯的渠道除了官媒,还有那么多自媒体和公众平台,以及各种各样的群团活动,却见不到一点今天的踪迹,是不是感觉有点奇怪?
才四十多年时间,一个非同寻常的群体,在公众视野里销声敛迹,该不会这么彻底吧?他们都在哪里?
作者简介
张佩芳 军人,曾任基建工程兵七支队和九支队宣传科干事,基建工程兵政治部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副院长,少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