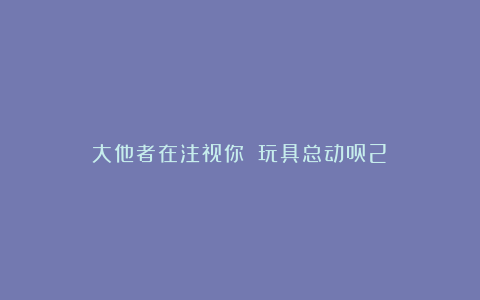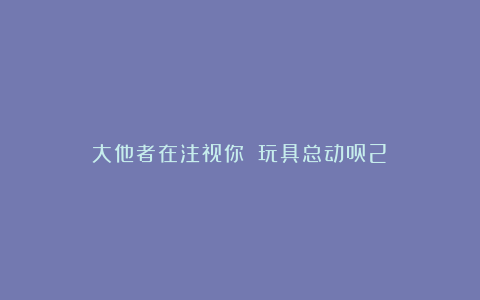|
大他者在注视你:《玩具总动员2》
作者:Lilian Munk Rösing(拉康派电影评论家)
在精神分析中,主体由缺失、分裂和裂隙构成。我们可能幻想自己是完整的,甚至在生命的早期、婴儿阶段,或者更早的胚胎期,我们或许体验到没有缺失、分裂或分离,感觉自己与周围的一切融为一体。然而,作为语言和欲求的生物(对拉康来说,语言和欲求正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所在),我们是分裂的存在:在事物与它的名称之间分裂,在我们想要的与得到的之间分裂,在自我感觉与自我形象之间分裂,在现在与过去之间分裂,在自以为说的或想要的与实际说的或想要的之间分裂,在意识与无意识之间分裂。分裂也来自时间性:不可能拥有一个纯粹的当下,不受过去或未来的影响;来自欲求:不可能得到完全和永久的满足;来自死亡:虚无的边界围绕着我们的存在。
在他第十一次研讨班中,拉康的演讲《眼睛与凝视的分裂》将主体的裂隙展示为眼睛的裂隙,既是观看的场所,也是一个物体,一个部分客体。比如,当你想到自己的眼睛时,一方面它是你脸上的一个洞,是你用来观看世界(但看不到自己脸)的地方;另一方面,它是一个有形的眼球。拉康将凝视归于客体,将其定义为视觉冲动的对象:“在可见领域中,对象a即是凝视”(拉康,1979:105)。这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它意味着我们的眼球渴望被凝视充满,成为观看的场所,而不仅仅是空洞的球体;另一方面,它意味着我们真正渴望看到的(例如在电影院中)是大他者的凝视。而大他者,即大O,是一个幻想性的存在(“被认为知晓的主体”),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都是在为这个存在上演自己生活的“喜剧”——不论是母亲、上帝、时尚杂志,或某种更抽象的存在。我们渴望这个凝视落在我们身上,渴望与之相遇。但当这似乎真的发生时,它却可能成为一种极为诡异的体验。正如齐泽克在《你一直想知道的希区柯克但又害怕问拉康》中所言,最终看到大他者的凝视,就像是看到《惊魂记》结尾中诺曼·贝茨的凝视(在那一场景中,声音和凝视似乎都像是“外来的”,在操控着一个人类的身体)(齐泽克,1992:245)。
拉康最著名的例子,用来说明大他者的理想化凝视转变为可怖的、毁灭性的“大零”凝视的转折点,便是汉斯·霍尔拜因1533年的画作《大使》(现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在这幅画中,可以看到两位穿着华丽的大使在摆姿势,倚靠在一张桌子上,展示着他们的书籍和仪器,这些象征着他们对世界的掌控。而在画面的前景中,一块奇怪的白灰色模糊斑块若隐若现。
可以说,这两位男子是在作为想象的角色,为大他者的凝视而摆拍——这也是我们在被绘画(在当今,更常见的情况是拍照)时一贯在做的。这里的凝视是公共的凝视,即他们向之展示自己的对象——当时是画家的凝视,今天则是镜头的凝视。但在这幅画中还存在着另一个诡异的凝视:如果从画面右侧的斜角观察前景的斑块,会发现它其实是一颗骷髅。这时,观者对凝视的欲求(反映了大使们对想象中的大他者凝视的欲求)会被戏谑地满足,而那失真变形的骷髅正是虚妄的象征。如果我们真正得以看见凝视,那么它将是实在的凝视,向我们回望,带来的信息只是主体的必死性。值得注意的是,画家在骷髅上刻上了自己的凡人之名,可以视作一种签名:“霍尔拜因”(Holbein)的含义是“空骨架”。
因此,这幅画使我们体验到“想象”中的凝视与“实在”中的凝视的区别,这两个概念是拉康三界中的两个,第三个为“象征界”。象征界在拉康的定义中是我们诞生于其中的社会和语言的世界;在象征界中,主体是语言、欲求和社会秩序的主体,被这种分裂、缺失或裂隙(即“象征性阉割”)所标记,这些是说话、欲求和作为社会生物所隐含的。在想象界中,主体是没有这种裂隙的:完整的(正如我们梦想自己是“完整”且“完美”的,或是新纪元式的梦想,或是青少年渴望成为明星的幻想)。在实在界中,主体则是无法被象征(语言、社会)定义或想象界理想所捕捉的:凡人的身体和无法掌控的幽灵般的存在。
在想象界中,主体是“某物”;在实在界中,他是“无”;而在象征界中,如果主体不将象征性身份(无论是“男人”、“教授”还是“太空骑士”)视为想象性认同,他则是“并非无”。这就像巴斯光年这个角色的例子:起初他相信自己是真正的“某物”(来自大他者,也即外太空的使命的巴斯光年),在经历失败后发现自己是“无”,最终意识到他其实是“并非无”(即作为一个巴斯光年存在)。托德·麦高文将大他者的凝视分为两种:“想象的凝视”(例如相机前的摆拍)和“实在的凝视”(突然回望的骷髅)。麦高文通过将电影理论的焦点从“想象的凝视”(作为由主导意识形态所支配的理想化形象的电影,包括父权制所规定的女性理想形象)转向“实在的凝视”(即电影作为你可能遇到诺曼·贝茨回望的场所),更新了拉康电影理论。
在《玩具总动员2》中有一幕,在美学和哲学层面上再现了与汉斯·霍尔拜因相似的凝视辩证法:那就是“清洁工”前来修理伍迪的场景。进入这一场景前,简要介绍一下影片的剧情是有必要的。
在《玩具总动员2》(1999年,由约翰·拉塞特、阿什·布兰农、李·昂克里奇导演)中,伍迪(汤姆·汉克斯配音)学到了虚荣的教训,既指痴迷于自己的形象,也指对死亡的觉悟。正如约翰内斯·温德所指出的,虚荣和死亡是贯穿《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的主题,尽管它们不再符合传统电影的特质;而是采用了动画电影的形式,不再捕捉稍纵即逝的瞬间,且其“生理躯体”随时可以被替换。影片开始时,安迪在玩耍时不小心扯松了伍迪的手臂,导致伍迪不能和安迪一起去“牛仔营”,而是被放在了架子上(玩具们称之为“被搁置”),在那里他遇到了“吱吱”——一只布满灰尘、挤压装置失灵的旧塑料企鹅。吱吱陷入了类似希区柯克电影《迷魂记》续集般的迷幻梦魇,梦见自己被安迪丢入垃圾桶,坠落在破碎的玩具零件中。第二天,安迪的母亲收拾吱吱准备参加旧物拍卖;伍迪在救他时,自己也成了拍卖的一部分。这时被肥胖贪婪的玩具收藏家艾尔(韦恩·奈特配音)看中,最终偷走了他,因为安迪的母亲不想卖掉他。在收藏家的家中,伍迪发现自己其实是早期一部儿童电视节目的明星,是一个玩具组合的一部分,其中包括牛仔女孩杰西(琼·库萨克配音)、淘金客臭皮特(凯尔希·格兰莫配音)和马儿飞箭。他遇到组合中的其他角色,逐渐沉迷于自己在电视屏幕上的形象。试图逃跑时,他的松脱的手臂彻底掉了下来,但影片最引人入胜的一幕随即展开:一个老玩具修理专家“清洁工”对他进行了修复,最终准备将他和其他组合成员一起送往东京的一家博物馆,那里以高价购入了整套牛仔玩具。然而,安迪的其他玩具已经出发营救他,找到了“艾尔的玩具仓库”,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令人捧腹的替换闹剧:巴斯光年(提姆·艾伦配音)与一个仍然处于迷惑状态的替身“巴斯”相遇,这个从架子上取出的巴斯短暂地替代了“真正的”巴斯,最后却被识破,留在玩具店里,享受着与他先前的敌人、类似达斯·维达般的“父亲”祖格的和解(祖格模仿《星球大战》的台词宣称“我是你的父亲”)。在机场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追逐后,伍迪和他的组合成员终于被带回了安迪的家中——安迪用笨拙的男孩针脚将伍迪的手臂重新缝好,形成了与“清洁工”完美修复的对比。
《玩具总动员》和《玩具总动员2》的剧情和主题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个玩具被某种邪恶力量带离了家,无论是邻居家的孩子还是玩具收藏家,经历了某种象征性的阉割甚至十字架刑罚。(巴斯光年和胡迪都失去了一只手臂,巴斯在试图飞行时,胡迪在试图逃跑时,而他们的断肢之后都以一种“效仿基督”的方式被展示:巴斯像十字架一样躺在地板上,胡迪则挂在收藏家的玻璃箱里的金属架上。)但不同的是,巴斯的象征性阉割使他从自己“来自外太空的任务”(作为某个“大他者”的工具)的精神错乱幻想中解脱出来,而胡迪的阉割(必须发生两次)最终让他摆脱了对自身外貌的自恋迷恋(在大他者面前的想象性展示)。
探讨虚荣和凝视的主题,让我们从“清洁工”(乔纳森·哈里斯饰)来修理胡迪手臂的场景开始——在我看来,这是皮克斯最好的场景之一。通过蒙太奇手法,该场景巧妙地表现了作为凝视之地和作为对象的眼睛之间的互动,正如拉康所称的“眼与凝视的分裂”(le schism de l’oeuil et du regard)。场景的配乐让人联想到柴可夫斯基的《胡桃夹子》或奥芬巴赫的《霍夫曼的故事》,因此暗示了玩具复活的主题,就像E.T.A.霍夫曼的故事中的玩具,尤其是《沙人》中的玩偶奥林匹亚,其中凝视和松动的眼球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年老的“清洁工”(这是为了致敬昆汀·塔伦蒂诺电影《低俗小说》中的哈威·凯特尔角色)带着大鼻子和白色的毛茸茸眉毛走向胡迪时,视角在清洁工和胡迪之间切换,而胡迪脸部的“客观”镜头中,他的眼睛仅是绘制的表面,并非凝视之地。坐在胡迪对面,将工具箱放在桌子上,把胡迪放在金属夹中,像是在理发或牙医的椅子上一样,老者拿出放大镜,仔细观察他的“标本”。这放大镜对观众来说既是清洁工观察的屏幕,也是我们观察清洁工眼睛的屏幕。因此,我们在凝视之地的眼睛和作为凝视对象的眼睛之间切换。此外,作为对象的眼睛在这个场景中由清洁工工具箱中的松动眼球来表现。
除了放大镜,另一种工具也在老人与胡迪之间、在作为主体的眼睛与作为对象的眼睛之间充当了轴心,那就是老人在清洁胡迪眼睛时用的棉棒。我们看到棉棒从胡迪的视角接近——然后我们实际上共享了他被棉棒碰到眼睛的体验:棉棒的纤维充满整个屏幕,屏幕随即完全变白,转场至玩具商店的场景,作为清洁工场景的插曲。这个“白屏”稍后在“黑屏”中重现——在一个真正疯狂的镜头中,我们似乎从胡迪身体的缺口体验这一情境,缺口在老者缝补他的手臂时合拢。
该场景在主观镜头和客观镜头之间的切换,可能让我们联想到齐泽克所称的“希区柯克式蒙太奇”(例如在《惊魂记》中莉拉凝视诺曼的哥特式房子,而房子里某个难以辨认的点似乎也在回望她的场景)(齐泽克,1991: 117)。这种蒙太奇隐含了物体反向凝视的体验,这可以说是《玩具总动员》系列影片的核心概念:玩具在回望,整个世界从玩具的视角被观看。
图1:从胡迪腋下的不可思议的镜头。取自《玩具总动员2》(约翰·拉塞特,1999)© 皮克斯。
《玩具总动员2》中的清洁工场景实际上比其他任何皮克斯场景的蒙太奇程度都更高——它被剪辑得更加细致(这是我们在影片评论音轨中得知的)。同时,我们可以注意到该场景中的镜头运动非常顺滑、流畅,几乎带有抚慰的意味,这样的处理方式与剪切、分裂以及眼与凝视之间的裂隙和谐统一,就像清洁工实际上在修复胡迪一样。
尽管镜头的顺滑和和谐感一如既往,但可以说在这个场景中,我们几乎接近了真实的“凝视”——它作为视觉领域中的污点出现。霍尔拜因画中的骷髅,或希区柯克《群鸟》中的鸟群,就代表了这种凝视的真实。在清洁工场景中,这种“污点”可以说是通过胡迪那盲目的、涂画的木质眼睛表现出来,或是在瞬间转场到一个极度疯狂而不可能的视角时,出现的黑屏——那一瞬,视角移动到了胡迪衬衫的纤维之间,随着老者缝补,布料逐渐合拢。
《玩具总动员2》的主要主题可以看作胡迪在“真实凝视”和“想象凝视”之间的游移。当暴露在真实凝视中时,他成为死亡的对象;当暴露在想象凝视中——观看自己作为电视明星时——他成为了镜像阶段中的“大他者”所观看的对象。当他观看自己在《胡迪大游侠》电视节目中主演的场景时,充满了自恋的神态,他的面部和整个身体都散发出迷恋的光彩——这是一个人彻底爱上自己形象的模样。
影片中真实凝视与想象凝视的对比,呈现了胡迪物化的历程,分别在现实中(胡迪成为一个死去或会死去的身体)、象征层面(胡迪成为商品、交换对象)以及想象层面(作为商品的幻想面:胡迪作为珍贵的收藏品)中表现出来。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中,艾伦·阿克曼将胡迪视为商品(既在电影中也作为皮克斯的周边商品),并提醒我们瓦尔特·本雅明对“灵韵”(aura)的定义,即“无生命的物体能够回应人类的凝视”的能力(阿克曼,2011: 101;本雅明,1968: 220-2)。胡迪拥有这种“灵韵”,而在阿克曼看来,修复场景象征着“艺术的奇迹,甚至如同复活一般的奇迹”(阿克曼,2011: 110)。阿克曼还解读了艾尔将玩具从历史时间转移至艺术领域(将它们出售给东京的博物馆)的计划,将其视为一种救赎性的项目。
《玩具总动员2》甚至似乎在影射希区柯克以“凝视”为核心主题的影片《迷魂记》。影片开头胡迪梦境中的迷幻风格让人联想到詹姆斯·斯图尔特在《迷魂记》中的噩梦,而胡迪在片中看似无尽的坠落情节,仿佛是坠入深渊的版本,与《迷魂记》关于坠入眼睛的深渊的主题相呼应(齐泽克,1991: 87)。伴随着胡迪的坠落,一副扑克牌也掉在地上,诡异地全部显示为黑桃A,看上去像是扑克牌白底上的黑色瞳孔。(根据影片评论音轨,黑桃A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在塔罗牌中它象征着死亡;这种电影外的寓意并未掩盖电影内部对瞳孔的视觉暗示,强化了凝视的主题。)因此,胡迪对死亡的焦虑体验与一些影像相结合,这些影像可能暗示了眼睛作为一种平面或深渊的体验,而非一个观看的场所或灵魂的镜子。
在《斜目而视》中,齐泽克提出了三种应对“凝视”或眼与凝视之间矛盾的电影方式:色情、怀旧和蒙太奇(齐泽克,1991: 107)。在色情中,观众因被简化为对象性凝视而瘫痪,而凝视则在画面中消失。(需要注意的是,这与劳拉·穆尔维的色情观有很大不同。穆尔维将观众视为主体控制者,而齐泽克则将其视为受害的对象。)在怀旧中,他者的凝视被包含为一种天真无邪的凝视,支持观众的凝视:我们设想一种凝视,将所呈现的世界视为完全自然且熟悉的。最后,蒙太奇是最忠实于眼与凝视之间的对立关系的表达方式。
在对斯皮尔伯格和迪士尼的有趣结合中,雷克斯·巴特勒关注怀旧与动画之间的联系。他提到《辛德勒的名单》中的一个瞬间,当一位手工着色成红色的小女孩出现在影片中,仿佛是动画般的存在,而影片其余部分则为黑白画面。这个场景位于克拉科夫隔都大屠杀之中,辛德勒从上方观看,突然看到这个小女孩回望着他。在影片的另一个场景中,这个红色的女孩再次出现,她在集中营的尸体堆上。巴特勒将这些场景描述为“原始、孩童般的动画时刻”,部分暗示红衣女孩是拉康“污点”的一种表现,同时也代表支持怀旧凝视的孩童凝视(巴特勒,2007: 321)。整体而言,巴特勒并不将女孩的凝视视为扰乱主体想象身份的真实的、不安的凝视,而更像是现实给主体想象身份的一个幻想性回应(辛德勒作为犹太人的救世主)。然而,他的解读似乎在女孩作为怀旧支撑的凝视与作为真实的骷髅般凝视之间徘徊。女孩卡通般的特质和她被着色成红色的处理,甚至可能使她成为拉康骷髅的某种掩盖。依据齐泽克的观点,巴特勒将斯皮尔伯格的影片定义为怀旧,因为它是为一种缺失的目光所拍摄的。他将这种目光与“在大屠杀中消失的犹太人”联系在一起(321),但我认为需要进一步说明:这个小女孩象征着天真犹太人渐渐消失的凝视,这种天真的目光在大屠杀前已经消失。在红衣女孩的凝视出现后,巴特勒甚至提出一种观点,即这部影片可以被视为辛德勒的幻想,一段由该凝视构建的犹太人得救的故事。
因此,巴特勒将斯皮尔伯格的怀旧模式与动画模式联系起来。《辛德勒的名单》中的动画时刻,以及《E.T.外星人》那种灵动的、诡异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灵魂是真实的,生与死、人类与外星人之间的区分已不再成立”(322-3)。对《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的分析尤其关注的是巴特勒进一步将怀旧和动画与缺乏父亲形象联系起来的见解。他认为《E.T.》是斯皮尔伯格试图回到“那个他还能相信动画的时刻”,并将斯皮尔伯格电影中反复出现的缺少父亲的主题归结为“没有监督的童年看电视”:“正是象征性父亲法则的缺失才允许那种虚构的暂停,进入想象界”(323)。按照巴特勒的说法,我们可以说《玩具总动员》系列电影中父亲的缺席,尤其是成年男性在电视机前睡着的重复情节,支持了电影的怀旧模式。不过,或许更准确地说,作为父亲法则的暂停,这种虚构的暂停既有怀旧的一面,为想象界提供空间,也有更为可怕的一面,为实在界敞开空间。
换句话说:如果父亲法则的暂停要导致怀旧而非精神病,则需要一个大他者来支持,以“假设相信的主体”的形象呈现出来,这包括大屠杀前犹太女孩的凝视、E.T.从柜子中投出的目光,或者普遍的“孩童凝视”的幻想,这种幻想激励了皮克斯动画师们的创作。
在《玩具总动员》以及皮克斯的其他动画电影中,怀旧似乎是最适合描述主导视觉模式的词。电影依赖齐泽克所称的“假设相信的主体”(齐泽克,2006: 29),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主体是孩子,这种幻想实际上驱动了动画师的创作。“假设相信的主体”是“假设知晓的主体”的一种变体。我们将天真、纯洁的信任凝视赋予孩子的眼中,从而支撑我们自己的享乐。然而,我尝试通过清洁工场景展示蒙太奇和暴露污点、真实凝视的元素。
转向电脑动画电影,作为一名拉康式文化分析家,不得不思考虚拟现实是否会排除某种程度上的“真实”。“虚拟现实[……]提供了被剥离了其实质性、抗拒性实在内核的现实”(齐泽克,2006: 38),这一点与齐泽克对当代资本主义文化特征的独到见解相契合:事物被剥夺了其危险的实质,比如无咖啡因的咖啡、无酒精的啤酒、无糖的甜食,以及无(人类)血的吸血鬼(如《真爱如血》和《暮光之城》)。那么,当电影不再展现人类的身体,它是否失去了“实在”的坚硬内核?
在这里,皮克斯动画电影中的唯一人类存在——演员的配音,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即使在其他维度上,计算机动画所构建的现实(与“实在”相对)实际上并非完全可控:媒介会以不可预见的方式作出反应,故事、动画、音乐、台词、角色的交织,再加上大量制作人员共同完成的结果,都是难以预测的。
齐泽克将虚拟现实与他所谓的“被动互涉”(而非互动)联系起来,并认为好莱坞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代理人:好莱坞为我们处理情感,让我们可以坐下来放松。齐泽克认为这是一种现代化、感伤版的希腊悲剧合唱团(齐泽克,2006: 22)。如果想在《玩具总动员》中找到希腊式的合唱团,只需打开评论音轨。在《玩具总动员2》的一个场景中,牛仔女孩杰西唱着一首非常悲伤的歌,讲述她被曾经爱她的孩子抛弃的故事,而评论则说道:“这太感人了,这一幕充满了情感——她在这首歌中倾注了无数的情感。”
根据评论音轨所述,牛仔女孩杰西的角色是为了回应“强势女性角色”的需求而创造的。这看起来有些滑稽,或许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因为杰西的“强势”,如果可以称之为强势的话,是一种类似男孩般的狂野。当杰西首次登场时,她几乎显得完全像个狂人:带着不加掩饰的热情攻击伍迪,尖叫着“是你,是你,是你”。后来我们了解到,除了这种狂躁的情绪外,杰西还会感到极度低落;她被赋予了一段“创伤性”的心理传记,通过悲伤的歌曲《当有人爱你》表现出来,讲述自己曾是一个女孩最深爱的玩具,直到那个女孩长大,变成一个只顾涂指甲、不再玩玩具的咯咯笑的少女。在“闪回”场景中,杰西一度相信长大的艾米丽终于带她回家了,但事实却是艾米丽正将她丢进垃圾堆,这一幕充满了感伤。
事实上,随着杰西在狂躁与忧郁之间的切换,她开启了皮克斯动画中一种似乎不断重复的角色类型:狂躁抑郁型的女性角色,后来在《机器人总动员》和《飞屋环游记》中也有出现。在《机器人总动员》中,有白色、流线型的“Mac风”机器人伊芙,她要么在瓦力的车库里完全失控,威胁要在狂野的舞蹈中摧毁一切,要么在“受孕”后进入类似死亡般的沉睡,将自己关闭起来。在《飞屋环游记》中,有弗雷德里克森的妻子,她既是那个完全无拘无束、闯入年幼弗雷德里克森生活的小女孩,也是成年后因无法生育而陷入悲痛的女人。显然,这体现了皮克斯动画中对“女性气质”的一种设想:女性要么是无拘无束的狂人,要么是抑郁的僵尸。这对应了我们文化中的两种典型“女性”角色定位:作为无法控制自己、总是溢出界限的女人,以及作为一种神秘、封闭在某种隐秘共鸣中的女人(弗洛伊德的“黑暗大陆”,拉康的女性位置)。
当伍迪选择留在他的“组合”里并被送往东京的博物馆时,他选择了停留在想象之眼的投射中,成为其珍贵的对象。在清洁工场景中那种平滑、抚慰的“镜头”移动压倒了它原本显露真实凝视的维度。伍迪被修复到他的象征性铭刻消失的地步,他的“父之名”——鞋底上的字母“ANDY”被涂抹掉,标志着他退出象征秩序,完全进入想象界。或许可以说,他选择博物馆生活是出于对其他玩具的同情(例如被困在仓库中的杰西的创伤经历),但电影的画面中展示的是他对自己形象的过度享受:一个被想象之眼驱动、被大他者的聚光灯捕捉的主体。
如果说《玩具总动员》讲述了伍迪象征性地“阉割”巴斯的故事,那么《玩具总动员2》则可以被视为巴斯“阉割”伍迪的故事。然而,正如之前所提到的,他们是从两个不同的状态中被“阉割”的:巴斯从一种成为大他者(太空控制)工具的精神病状态中被“阉割”,而伍迪则从一种成为大他者(公众)偶像的自恋状态中被“阉割”。
在《玩具总动员》中,当伍迪对巴斯喊出“你是一个玩具”时,意思是“你不是一个太空游侠”。而当在《玩具总动员2》中巴斯对伍迪说出同样的台词时,意思却是“你不是一个收藏品”。巴斯的阉割将他抛向了女性特质(正如他被希德的妹妹打扮成“奈斯比特夫人”),而伍迪的阉割则将他抛向了必死性。伍迪在展示用的玻璃棺材和朋友们来救他的通道之间的选择,似乎是他在不朽与有限性之间的选择。
在伍迪和巴斯的故事中,“阉割”都通过失去一只手臂来象征,但他们重新获得手臂的方式有所不同。巴斯的手臂恢复,是由希德的超现实玩具群体通过一种带有魔力的操作完成的,这些玩具以一种遮挡观众视线的方式围绕着他,这象征着一种类似梅兰妮·克莱因理论的修复性艺术创作阶段。伍迪的手臂则被缝合了两次:第一次是清洁工用完美无缺的缝线将手臂缝上,使之恢复得像新的一样甚至更好。第二次是安迪用笨拙的缝法缝回,填充不均匀,使上臂变得过于粗壮。关键在于,伍迪最终更喜欢安迪笨拙的修复,而不是清洁工的那种完美修复,而这一“错误”或上臂的畸形实际上赋予了他新的象征意义:伍迪摆出健美的姿势,炫耀自己“肿胀的二头肌”。因此,他的“阉割”符号——畸形的手臂——竟然成了力量的象征。这也许正是象征性“阉割”的意义所在:从失去中获得收益,进入语言和符号化的世界,在其中每一个现象,即使是畸形的手臂,也随时可以被赋予新的、从不固定的意义。
如果说《玩具总动员》告诉我们一个精神病主体通过坠落而成为分裂主体(一个正常的神经症玩具……)的故事,那么《玩具总动员2》讲述了一个主体被诱惑去凝固于想象的完美中,最终却接受了自己的不完美、自己的裂痕,这一裂痕被呈现为想象之眼和实在凝视之间的裂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