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运河苏州段是大运河的核心区段,也是大运河水系与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形态共同发展的典型区域,通过梳理其水系与环境的相关性及形成、分布特征,分析其与沿途城镇的相互影响,对当前传承与发展大运河文化具有积极意义。
运河是为了水运而建造的人工水道,是人类社会改造并利用自然环境的重要实践。苏州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有着优越的自然条件,孕育了灿烂的古代历史文化,其中,这里最早出现的一批人工河道成为隋朝大运河和之后京杭大运河的基础。
得益于运河的作用,苏州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在 2014 年中国大运河(以下简称“大运河”)成功申遗的过程中,苏州因与运河的密切关联而成为唯一以古城概念列入其中的城市。
大运河的形成、发展,是与所在区域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文化形态乃至国家统治同步共生的。自然环境是大运河发展的基础,不同环境中的大运河形态有着很大的差异;水运是大运河被开挖的驱动核心,离开水运的需求,也就没有了大运河存在的价值;经济需求是运河存续的驱动力,虽然历史上最早的运河因军事目的而出现,但后来大运河的作用更充分地体现在发展区域经济等方面;文化是大运河发展的精髓,与大运河相关的技术、管理和社会生活构成丰富的历史传承,也是当代大运河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关键。
与一般自然河流支流汇聚形成干流的树枝状水系形态不同,运河一般只由其干流组成水系中的航运主干,有着目的性较为明显的起止端点,常辅以相应的管理、供水等系统,并由人工维持其高效运转,同时,运河主干与所经地区的自然河道及其他人工河道相交汇,从而构成一个在河水流向、流量乃至物流组织等方面相互关联的特殊水文系统,即运河水系。
这一“水系”形态,在地处江南水乡环境中的大运河苏州段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大运河苏州段与自太湖通向长江的自然水系和人工引排水系之间,在走向等方面存在差异,在水流上存在交错,造就了大运河与本地水乡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在运输、防洪、治污等方面互为影响的关系,形成了大运河苏州段文化传承的基础条件。
一、大运河苏州段水系的特征和环境相关性
(一)大运河苏州段所处水乡地区水系的特征
大运河苏州段穿过了最为典型的水乡地区。长江三角洲原是长江及其支流所携带泥沙在滨海地带和湖沼地区堆积而形成的,苏州又处于长江三角洲腹地的太湖平原,这里地势低平、排水不畅,加上气候多雨、环境潮湿,水乡泽国是这里的原生环境。
经过数千年人类活动的改造,水乡地区特有的自然环境的优势特征愈加稳定。虽然近几十年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对这些特征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水乡依旧是这里没有改变的基础背景。
水乡地区水系的基本特征是区域内河网密度高、大小湖泊众多。在区域发展过程中,这些河湖往往积累了大量人工维护的投入,形成各种溇、塘、浦的形态和体系,其功能与运河之间的差异不是太大,都具有航运、灌溉、排水等作用,只是运河在运输方面的优势与特征更为突出,大运河的运输作用区域更为广阔。
在过去的航运中,水乡地区的湖泊往往是危途,尤其受特殊天气的影响极大,湖泊形态和水位的变化对航道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二)大运河苏州段水系的指向性
从全国范围看,苏州所在的长江三角洲是大运河水系的两大端点之一。有观点认为,北方京畿地区是大运河文化的核心区域。但如果从功能上看,这只是其中一端,从隋唐大运河时期的洛阳、开封,到京杭大运河时期的北京,都体现为政治体系的核心,是漕运物资主要目的地的端点。
而以苏州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区域,则是大运河文化的另一个核心,这里从以稻米为代表的物产中心、漕运物资供应地成长为国内最富庶的经济中心,始终是大运河文化的重要参与者,也是大运河航运的另一端点。在南宋时期,这两个端点可以说合并在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也因此,苏州段的大运河水系走向,根本上体现了北通京畿、南联杭嘉湖的指向。
从长江三角洲范围来看,苏州是江南运河干流最为重要的拐点,这在客观上更加突出了苏州在大运河水系中的重要性。太湖的存在,更进一步框定了大运河贯穿长江三角洲时航道的走向。
苏州往北,大运河在太湖东北侧,呈西北—东南走向,总体为沿着太湖边缘的较为稳定的航道;苏州之南,大运河在太湖东侧,为南北向,穿越东太湖原有的浅水湖滩区,甚至参与了这一地区的环境演变[1]。而在明清时期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后,苏州更是大运河水系中不能绕过的节点。
(三)大运河苏州段水系的发散性
在大运河沿线区域,或因气候偏干而使运河航线受到供水水源的制约,或因经过山丘地带使大运河航线深受技术和经济的制约,大运河水系往往呈现工程难度大、布局更改不易的情况。但在沉积物深厚、水源充足、河道成网的长江三角洲水乡地区,航道的更改却相对容易。
或因自然河道发生变化,或因某些河段由于运量增加导致拥挤,过境船只往往可以选择其他航运通道,大运河节点之间的连接线就表现出可变性、多变性,具有发散性的特征。总体上看,受重要城市目的地等节制,大运河水系的发散性通常表现在局部,从属于指向性之下。
如清代江南运河沿线地名图[2] 显示,当时的大运河经过望亭、浒墅关向东南方向进入苏州城时,共有三条通道:上塘河为主干,山塘河为辅线,两者均连接至阊门;另有过横塘,经胥江,入胥门的航道,宽度介于前两者之间。
而民国时期苏州城域地图 [3]描绘的苏州城西大运河相关水系中,认定的运河干线自浒墅关向南后,在十里亭转入山塘河,于阊门入苏州外城河;枫桥横塘之间的河道标注为“枫桥塘”,与胥江相通。
由于长江三角洲河网密度大,河道间联通性非常好,因此,大运河巨大的运能往往通过这些沟通在一起的水网脉络,发散到水乡各地。如苏州地区,在历史上以水运为主的慢经济、慢生活时代,大运河周边的市镇村庄都享受着这种舟楫的便利,甚至使内河水运通江达海,扩展到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乱年代,沿大运河干线布局的一些市镇,常因兵燹遭到破坏,而在大运河水系发散的区域腹地,却能得以幸免,甚至得到发展的机会。
二、大运河苏州段水系的衍变和干流分段
(一)相关因素影响下大运河苏州段水系属性的衍变
经济政治因素影响大运河格局与地位的变化。从大运河全局角度看,从隋唐大运河到京杭大运河的改变,体现了政治格局对大运河航线布局的影响;历史上大运河苏州段水系基本不变的指向性,说明了苏州乃至长江三角洲地区在全国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稳定性。
近代以后,大运河苏州段水系的地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究其原因,最主要的是经济区位的改变及运输方式的变化,如上海的兴起,公路、铁路等陆上运输方式的出现。
虽然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大运河航道的布局,但却改变了苏州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原有的交通中心、经济中心地位,整个大运河水系在运输量中占有的份额逐渐变小,大运河沿途的繁荣程度大打折扣。加之近代社会的动荡,大运河沿线部分地方如山塘街、黄家溪等地,受到了更为严重的打击。
技术因素影响大运河等级及航道选址的变化。在漫长的农业社会中,大运河航运的动力以人力为主,辅以风力等传统形式,大量的运能通过人拉手摇来实现。
因此,在重要的航道上,往往通过建造高桥来提升运输船只的通过能力,通过修筑纤道使船只得到稳定的牵引力,这样的投入也使大运河航道的建设水准得以提高,航道的位置得以进一步固定。在现代,水运具有的稳定和廉价的优势使其在运输体系中仍占据重要地位,其中,大运河水系尤其担任着重要的角色。
随着机械化水平的提升,大运河中航行的船舶日趋大型化,航道要求也日趋高等级化,原有大运河河道无法满足现代化水运的需要,必须拓宽改造。但航道拓宽时,在城镇区,尤其是通过苏州古城区时,会面临建成区拆迁、文物保护等方面的难题,加上大型运输船舶给沿途环境带来的废水、废气和噪声污染比较明显,因此采用规划建设新航道的做法以规避风险,这样,大运河水系的结构就随之发生了改变。
行政因素影响大运河航线设置与管理状态的变化。政府对航道的维护管理强化了运河航道的稳定性,如明清时期于无锡苏州之间运河航道狭窄地带设浒墅关钞关。
再如在驿站系统已经非常完备的明代,大运河苏州段干线上设姑苏驿、松陵驿、平望驿,三者间的距离比当时“六十里制一驿”规定明显缩短 [4],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政府在大运河苏州段管理上的更多投入。
就当今而言,比如“苏南运河”的名称,也体现了行政因素在大运河航道管理中的影响。大运河苏州段南至油车墩,全线长 96 公里,但有时候“大运河苏州段南至鸭子坝、全长 82 公里”的描述经常被引用,造成这一现象的主因,当与大运河航线的规划、设置及建设项目推进和协同等行政因素有关,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大运河文化传承过程中各方面因素的协调状态。
(二)大运河苏州段水系干流的分段
根据干流的自然条件、历史传承和当代建设特点,大运河苏州段纵向可分为四段。
1. 苏锡段:自丰乐桥(五七桥)过望亭、浒墅关至枫桥上塘河口附近。大运河自沙墩港北侧的丰乐桥连接无锡段,往苏州方向的干流基本为单一直线。所经古镇有望亭、浒墅关和枫桥,重要古迹有浒墅关文昌阁、十里亭等。十里亭对岸的白洋湾为山塘河西北端与大运河相连接之处,但其河口及水系已不甚清晰。山塘河东南端,与大运河阊门段直接相连,民国时期的地图也有将山塘河标记为大运河干线的情形。为确保水环境质量和大运河水量稳定,苏锡交界处的大运河通过望虞河枢纽工程与望虞河之间实现立体交叉,互不干扰。
2. 古城段:自枫桥至宝带桥北新老运河交汇处。此段大运河原先主要依外城河过苏州城。新中国成立后,因运河水运需求提升、运量增加,运输船只吨位变大,航道等级不断提升,先后形成古城段的三条主线:
3. 苏浙北段:自宝带桥至平望镇南莺脰湖。此段大运河干流水系相对简单,基本无大的分支和变化。干流沿线重要古迹除宝带桥外,还有松陵的三里桥、九里石塘,以及平望古镇的安民桥、安德桥等,在大运河拓宽的过程中得到保护和修复。而垂虹桥作为大运河水系中环境变化的见证具有极高的文物价值,目前其遗址得到了很好的保护。在大运河拓宽工程中,此段也有古迹被拆除的现象,如尹山桥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被拆除。需要说明的是,大运河在平望镇北与太浦河相汇,运河新航道建设时,从此交汇点向西借 1.5 公里太浦河为大运河航道,并向南新开航道 3 公里,进入并列于莺脰湖西侧的草荡,由此保留了平望镇区 2.2 公里的大运河故道和 1.7 公里的頔塘故道。尽管如此,由于莺脰湖在大运河历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在此仍将其作为分段节点。
4. 苏浙南段:自平望莺脰湖至浙江界。平望向南、向西,吴头越尾之地,历史上形成大运河的三大支线,通向京杭大运河的南端——杭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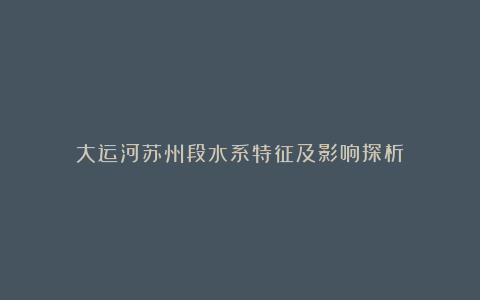
苏州古城以西的滨太湖区域,在太湖和大运河之间,北部区域狭窄,大运河与太湖相逼近;向南则逐步展宽,为苏州西部山丘的主要分布地。
(一)以水系为核心强化大运河的综合体意识是传承大运河文化的基础
(二)发挥大运河不同河段的优势特色是解决传承与发展矛盾的关键
大运河文化传承中,最突出的矛盾在于:一方面运河故道、大运河沿线古城古镇要传承保护;另一方面大运河水运、城市要发展,市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要提升。
原先的大运河河段,无论河道的宽度、通行船只的等级,还是沿途交通的设施,以及城镇建设的层次,都适应着过去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活状况,与现代社会的生产生活有着一定的距离,但这些历史遗存承载着大运河的历史、大运河文化。
这些遗存如果保护、处置不当,将永远消失,无法恢复。因此,要处理好“老”与“新”的矛盾,就要充分发挥“老”大运河河段文化遗存丰富等优势, 充分发挥“新”大运河河段现代河运发达等优势,让不同类型的河段担当不同的角色,体现不同的特色,兼顾保护与发展。
作为历史上与大运河共生共荣的苏州古城和周边村镇,在以若干点段及古城概念加入大运河申遗的过程中,已在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和传承、保护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如何更好地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从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角度去关注这些历史遗存,真正认识这些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应该看到,大运河苏州段虽没有高难度的运河航道建设技术,也没有横跨大江的特殊地理位置,但有着与大运河相互影响并不断成熟和谐的水乡自然环境,有着与大运河同步发展并长期占据全国领先地位的区域经济和文化——这也是苏州古城及周边地区所具有的特质。
因此,虽然现在大运河的航运干线不再经过苏州古城区,或大运河沿途古镇和乡村地区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苏州古城和沿途村镇的大运河文化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其传承意识,不应淡化,需要进一步加强。
对于新建设的大运河河段,应通过提升航线等级、增加运输能力等,使其发挥出比传统大运河更强的水运能力,不断加大对经济建设的支撑力度。
同时,也应看到繁忙的大运河航运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文化景观,同样能在旅游和教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要看到“新”运河与“老”运河的不同属性,在关注“运河遗产”热点的同时不要忽略新运河的优势,这对大运河文化的传承、保护更为有利,对大运河文化的创新和发展更为重要。
(三)保护和发展并重是延续大运河文化脉络的核心
其一,这里是大运河进入苏州的门户,也是大运河交通的重要节点,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自枫桥经上塘河到阊门是大运河进入苏州古城的主要通道,沿途形成苏州阊门外十分繁荣的一个带状区域;
其二,这里古迹集中,有枫桥铁铃关水陆城防体系,有寒山寺千年古刹,有“江枫渔火”“夜半钟声”的唐诗意境;
其三,这里还是水乡环境下大运河水系组织的极好案例,包括上塘河作为阊西运河承担的大运河进出苏州城的主线功能,枫桥与横塘之间的枫桥塘与大运河的关系等;
其四,这里的水系关系在不同时期发生的变化,如枫桥向南开挖新的大运河干线过程中对文物的影响,原枫桥塘西侧与新运河之间形成的江枫洲区域(枫桥景区)的文旅开发,江枫洲西侧大量大型船只过往的新运河航运咽喉地带的新运河文化带建设,等等。
[2] 张振雄 . 苏州山水志 [M]. 扬州:广陵书社,2010:地图插页 2.
[3] 高元宰 . 最新苏州游览地图 [Z]. 苏州:文怡书局,1943.
[4] 彭成,汤晓敏 . 明代江南运河沿岸驿站选址特征 [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农业科学版),2016,34(2):58-63.
作者简介:朱剑刚(1963—),男,江苏常熟人,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文化地理和地理媒体。
引文格式:朱剑刚 . 大运河苏州段水系特征及影响探析 [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9,36(5):43-51.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公众号
2019.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