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策兰的生平似乎也无需多介绍,被公认为是里尔克之后最重要的德语诗人。策兰的诗歌被称作是奥斯维辛之后的诗歌,与贝克特等人一起成为二战后欧洲的代表作家之一。
策兰的中文译者也有不少人,有王家新、芮虎合译,黄灿然,孟明,杨子,等等。北岛是批判了王家新和芮虎的译文(北岛:策兰,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我的看法是,如果自己不懂德语(即使懂,也达不到母语的水准),可能也不需要过于计较译文的准确;通过译文感受下就好~
关于策兰的文章很多,本文的用意是做一个简单快捷的综述,方便阅览~关于策兰的评述文章大多比较冗长,其实也无需去过分细读,直接读策兰的诗作译文就可以了。哲学家和学者们大多是从语言本体论、策兰写作与二战大屠杀之间的关系、奥斯维辛之后是否还能有诗歌(可以说是一种历史哲学论)等角度去研究的,比如阿多诺等人。
策兰本人拒绝“密封诗”这一标签
在德国语境中(且不说一般的读者,德国的评论家,从阿多诺到迦达默尔),普遍是用“密封诗”这个概念来评价策兰后期的诗作。但是策兰本人是坚决拒绝这一标签。因为在他看来这类认知完全建立在对他本人的创作无知的基础上。他曾对作家朋友阿尔诺·赖因弗兰克说道:“人们都说我最近出版的一本诗集是用密码写成的。请您相信,那里面的每一个字都和现实直接有关。不过,他们没有读懂。”“一点也不密封”,他这样对人说,“去读!不停地读,意义自会显现。”
在1962年6月给早年的家乡朋友埃里希·艾因霍恩的信中,策兰曾这样写到:“我从未写过一句和我的存在无关的东西——你看,我是一个写实主义者,以我自己的方式”。
策兰写作的语言本体哲学来源
策兰是仔细读过海德格尔的。根据对策兰诗人藏书的研究,策兰开始认真研读海德格尔著作是在1952年3月,首先阅读的是海德格尔名著《存在与时间》;他首次听说海德格尔还要早些,应该是在1948年,那一年年初刚从布加勒斯特流亡到维也纳不久的策兰认识时年22岁的女作家巴赫曼,并产生了一段延续多年对二人都产生深远影响的恋情。巴赫曼当时正在以《对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的批判接受》为题撰写博士论文,巴赫曼对海德格尔思想某些方面持赞许态度,同时对海德格尔过去的纳粹分子身份持批评的态度,这种矛盾以后也贯穿在策兰对海德格尔思想的接受和拒斥的整个过程。
策兰的藏书中有八十多位哲学家的作品,其中他做过读书笔记的有四十多位,但再没有哪一位哲学家作品像海德格尔作品那样激起他巨大的热情,他广泛阅读海德格尔作品,并做了大量笔记,在吸收海德格尔语言观和哲学观的同时,策兰甚至直接从海德格尔颇具诗意的语言中获得创作诗歌的灵感,像著名诗篇《带着一把可变的钥匙》中的核心意象“语言之屋”以及《从黑暗到黑暗》中的“摆渡人”意象都来自于海德格尔著作。
德里达关于策兰的文章,也可以一读;该文的最后部分,也可以理解为是语言本体论:德里达论策兰:语言,永不为人所有。
海德格尔关于诗歌与语言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语言向诗人说话,而不是一位通过自己的想象力来创作诗歌的自主的创造者促成了诗歌的出现。德里达和海德格尔的观点很相关,但有差异。而策兰是如此表述的:“我肯定,在这里起作用的不再是语言本身,而总是一个从存在的特殊角度说话的’我’,他总是关注大致的轮廓和方向。”
策兰本人关于诗歌、语言的一些说法
策兰在翻译波德莱尔时曾这样感叹:“诗歌就是语言中那种绝对的唯一性”。
在回答不来梅一位高中老师时,策兰曾这样很耐心地说:“对一首诗来说,现实并不是某种确立无疑的、已被给定的东西,而是某种处在疑问中的事物,是需要打上问号的东西。在一首诗里,真正发生的……是这首诗自身。只要是一首真正的诗,它便会是它自身(现实)发生的质询的意识。”在1958年《对巴黎福林科尔书店问卷的回答》中,他说得更为明确:
“真实,这永远不会是语言自身运作达成的,这总是由一个从自身存在的特定角度出发的’我’来形成它的轮廓和走向。现实并不是简单地在那里,它需要被寻求和赢回。”
在毕希纳奖受奖演说中,策兰在“为诗一辩”时就曾引用了法国哲人帕斯卡的一句话:“不要责备我们的不清晰,这是我们的职业性”。耐人寻味的是,就是这样一句话,有人把它译为“不要抱怨黑暗,因为我们为它而生”(见法比安·勒托夫《伤痕诗学》,Hoffnungsfunke译文)。
在给朋友汉斯·本德尔的信中,他直承写诗就是“祈祷练习——用精神的感官”。
策兰曾经说过,诗歌是一种“浓缩了我们所有年期记忆”之聚合体。以《凝结》的这首短诗为例:
还有你的
伤,罗莎。
你的罗马尼亚野牛的
犄角之光
替代了星星于
沙床之上,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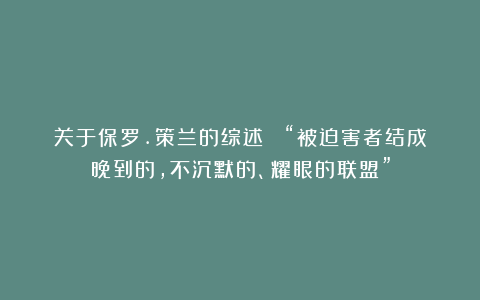
灰烬般强悍的枪托中。
策兰给自己布加勒斯特时代的密友所罗门的一封信中:“在诗集《换气》第79页,罗莎·卢森堡透过监狱栏杆所看到的罗马尼亚水牛和卡夫卡《乡村医生》中的句子汇聚到一起,和罗莎这个名字汇聚到一起。我要让其凝结,我要尝试让其凝结。”
保罗.策兰手稿
以下为保罗·策兰《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王家新 译)的摘录——
在所有丧失的事物中,只有一样东西还可以触及,还可以靠近和把握,那就是语言。是的,语言。在一切丧失之后只有语言留了下来,还可以把握。但是它必须穿过它自己的无回应,必须穿过可怕的沉默,穿过千百重谋杀言辞的黑暗。它穿越。对所发生的一切,它对我没有言及,它只是穿过它。它穿过它并重新展露自己,因为这一切而变得“充实”。
在那些年月和后来的日子里,我试着用这种语言写诗:为了言说,为了确定我自己的位置,为发现我自己从何处来,到何处去,为了勘探出我自己的现实。
正如你们所见,它意味着移动,意味着事情的发生,意味着在途中,并试图找到自己的方向。每当我被问及对此的感觉时,我便提醒我自己,沿着顺时针转动的方向,那也许就是问题所在。
因为诗歌不是处在时间之外的。诚然,它要求成为永恒,它试图穿过并把握时间——是穿过,而不是跳过。
一首诗,是一个语言的例证,因此对话是本质性的,它可以作为一个“瓶中信”被投向海中,带着一种希望——当然并不总是那么强烈:它可能什么时候被冲到什么地方,也许那正是心灵的陆地。正是以这种方式,诗歌成为一种路程:它们向前跋涉。
向着什么?向着一些敞开的事物,那可居住的地方,向着一个可接近的你,也许,一种可接近的现实。
我认为,现实就是这样被留在一首诗中的。
并且我也相信,不仅我自己带着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一些年轻诗人的努力方向。在一个人造之星飞越头顶,甚至不被传统的天穹帐篷所庇护的时代,人们便暴露在这样的未知与惊恐中,他们把这种存在带入语言,被现实压迫并寻找着这现实。
对策兰诗歌技巧的一些分析
简单来说,策兰的诗歌似乎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时期。北岛说他更喜欢策兰中期的诗,策兰晚期的诗歌更为破碎、浓缩。《死亡赋格》和《花冠》可以说是策兰最有著名的两首诗。
兰的阅读极为庞杂,他读报看书,从文学到地质学、植物学,甚至科学著作等等,而某些偏僻的专业术语在策兰诗歌中频频出现,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给策兰诗歌带来陌生化的奇异效果。策兰诗作中有很多地质学、矿物学以及生物学等领域里的专有名词。
除了词语本身所携带的深远含义(通过不同语境下的引导或者通过冥想本身),策兰还经常使用复合词来才持续地给词语施加压力,让一个词语在内部即产生某种扭结作用,那么这个复合词就比单纯利用意象自身的呈现更具主动地创造作者渴望的诗意。举几个例子:策兰1970年在离世后出版的首部遗作《雪之部》(Schneepart),德文der Part源自法文词la part,其基本释义为“部分”、“份额”,又指声乐或器乐的声部以及戏剧中的角色,故《雪之部》又可以译为《雪的声部》或《雪之角色》;策兰还喜欢把两个常用词用某种方式组合起来,让新词变得陌生,比如“gedichtlang”(像诗歌一样长的);或者随便组合可辨认的词语,但却具有了新的意义,比如“Seinswurzeln”(存在之根)。这些手法加强了策兰诗歌中单个词语可能携带的含义,让词义和诗歌都变得更丰富也更含混,同时也使策兰诗歌的翻译变得困难重重,这些富于创见的复合词,在别的语言罗嗦的解释中只能是诗意尽失。
这种给词语施压的方法和观念,也必然使策兰诗歌在用词上变得越来越俭省。策兰诗作越到后期越是像在做减法,诗和诗句都变得更短,试图将情感和政治历史方面的压力直接灌注到单个词语内部,让它们最终产生炫目的效果。
作为诗歌译者的策兰
和许多诗人一样,策兰也是一位杰出的诗歌译者,他翻译过四十多位诗人的作品,其中被广泛称道者包括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瓦雷里的《年轻的命运女神》以及狄金森等诗人诗作的翻译。曼德尔斯坦姆和翁加雷蒂,策兰也是通过翻译他们的诗和他们“相遇”的。策兰1958年开始翻译曼德尔斯坦姆的诗作,并立刻为他的诗作所折服,这种“极其欣赏”也包含一些外部因素,比如他们同为犹太人,也都是杰出的译者,对母亲都怀有深沉的爱,两人都因为各自出身遭受过政治和文学上的迫害,曼德尔斯坦姆也曾受到一次无根由的剽窃起诉,而当时策兰正遭受诗人伊凡·戈尔遗孀对自己的莫须有的剽窃起诉,并深受困扰,这件事也使策兰在整个六十年代堕入精神分裂的深渊。当然对曼德尔斯坦姆诗艺上的钦佩才是最根本的,在给一位编辑的信中,策兰道出他热爱曼德尔斯坦姆的原因,这些话语用来比喻策兰自己似乎也完全合适:“在他(指曼德尔斯坦姆)那一代俄国诗人中,我不知道还有哪一位跟他一样处在时代的最前列,思考时代又超出时代,一直把一件事情想得通通透透,想到了时代的各个细节,大大小小的事件。他用的那些字眼直面时事,并且经得起时代的考验。既是开放的,又与世隔绝。”在总的观念上,策兰和曼德尔斯坦姆确实颇为接近(尤其是“思考时代又超出时代”这句),可是具体到诗歌风格上,两人还是有较大差距。
而曼德尔斯坦姆的诗歌则是旺盛地繁殖式的,曼德尔斯坦姆有将视觉场景迅速诗化的能力,他的诗歌中意象更多更具现场感,在诗句方面曼德尔斯坦姆也不惮于让一些直白的口语入诗。这些特征都和策兰诗作相去甚远。曼德尔斯坦姆的诗作总体而言是即兴式的,可以迅速触及事物瞬间的神秘,意旨同样非常丰富,而策兰诗作则有明显雕琢用力的痕迹,就这一点而言,策兰对曼德尔斯坦姆产生艳羡之感实在是自然而然。策兰也翻译过翁加雷蒂的不少诗作,虽然谈得不多,但是策兰和翁加雷蒂其实渊源更深。两人在诗歌的极度凝练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句子都很短,往往一两个词就是一行,诗句之间的空隙很大,在引导读者注意力和想象力自主的发挥方面都有很强的愿望和功效。同时,翁加雷蒂所强调的“词语应该是对沉默的一次短暂开裂——正如马拉美所为。词语是一个断片,颤抖着立于被匆匆触及却层层掩隔的世界和立刻又在这世界之上合拢的宁静之间”,也一定会引起正试图从沉默中挖掘深意的策兰高度认同。两者明显的差异在于,翁加雷蒂对这个世界存在的意义持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他的诗句虽短,但在单位意义上仍然是完整的,而策兰哪怕在极短的诗句里也不忘使用他惯用的扳手,把平常的或者在他看来庸常的语义扳断。
阿多诺对策兰后期诗歌的评论
在阿多诺看来,艺术就应该是“密封”的,就应具有某种“密教性”,它不是任何外部事物的模仿和表现,而应忠实于自身的法则。顽固地背对社会场面,在语言的秘密的自我封闭的表现中,才有可能以相反的形态刻印真实的社会经验。正因此,在一个充满了“交流”的“虚假性”的社会里,“艺术只有拒绝追逐交流才能保持自己的完整性”。
这样,在一个文化消费和资本的逻辑一统天下的世界上,诗的“密封”被提升为一种伦理,一种“最低限度的道德”。他在论贝多芬时就谈到了这一点:“人独自局限于音乐,与羞耻有关”。
这就是为什么阿多诺会高度认同策兰的后期诗歌。从策兰式的“密封”中,他感到的是对艺术尊严的维护,是某种顽强的“抵抗性潜能”。因此在《美学理论》中,他专门把“密封诗”的问题提了出来。他当然并不认同那种关于策兰的诗“与经验现实隔绝”、“晦涩难解”的论调。为此他回顾了马拉美以来现代诗歌的历史,“密封诗歌可以说是这样一种类型诗歌,它并不取决于历史,而是完全依据自身来生产称之为诗的东西”,但同时,他又指出策兰诗歌与传统的“密封诗歌”的深刻区别:
“密封诗歌曾是一种艺术信仰,它试图让自己确信生活的唯一目的就是一首优美的诗或一个完美的句子。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在保罗·策兰这位当下德国密封诗歌最伟大的代表性诗人那里,密封诗歌的体验内容已经和过去截然不同。他的诗歌作品渗透着一种愧疚感,这种愧疚感源于艺术既不能经历也无法升华苦难这一实情。策兰的诗以沉默的方式表达了不可言说的恐惧,从而将其真理性内容转化为一种否定。”
以下摘自王家新《阿多诺与策兰晚期诗歌》一文:
多年来,阿多诺一直想好好写写策兰,因为在他看来策兰和贝克特一样都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作家,但他一直犹豫不决,没有动笔。不过,他后来关于贝多芬的札记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策兰晚期的诗。在他关于贝多芬的论著中,有两、三章都是在谈贝多芬的“晚期风格”,阿多诺这样指出:
“重要艺术家晚期作品的成熟不同于果实之熟。这些作品通常并不圆美,而是沟纹处处,甚至充满裂隙。它们大多缺乏甘芳,令那些只知选样尝味的人涩口、扎嘴而走。它们缺乏古典主义美学家习惯要求于艺术作品的圆谐”。
阿多诺在这里所说的,不正可以用来描述策兰的晚期做品吗?
阿多诺还多处谈到这种“晚期风格”的特征:“压缩”、悖论、反讽、非同一性、脱逸(“脱缰逃跑的公牛”)、分裂、突兀停顿、“微观”眼光、碎片化,等等,“贝多芬的复调音乐有其全新的意义:一种将不相类、解体的元素连结而逼出来的解决。不行也得行。那些卡农即由此而生”。“晚期风格兼含两型:它完全是外延型所代表的解体过程的结果,但又依循内凝原则,掌握由此过程散离出来的碎片”。“作为瓦解之余、弃置之物,这些碎片本身化为表现;不再是孤立的’自我’的表现,而是生物的神秘本性及其倾复的表现”。“客观的是那碎裂的风景,主观的是那唯一使之发亮的光。他没有谋求它们彼此和谐综合,他,作为一股分裂的力量,将它们在时间中分开,以便将它们存储永恒,也许。在艺术史上,晚期作品是灾难”。
这些,恰好也都是策兰晚期诗的特点。它们构成了策兰晚期诗歌的精髓和难度所在——那是需要一个诗人付出巨大代价才能达到的艺术难度。这样的诗,对于一般的读者,自然像“天书”一样难解。的确,策兰晚期的“成熟”,正是苦涩的成熟,是阿多诺意义上的“灾难般”的成熟。
深受阿多诺影响的萨义德也曾有过一部专论《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和文学》,对“晚期风格”进行了阐发:它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它不是和谐,而是不妥协、不情愿和“尚未解决”,“在人们期盼平静和成熟时,却碰到了耸立的、坚难的和固执的——也许是野蛮的——挑战”。“晚期风格并不承认死亡的最终步调;相反,死亡以一种折射的方式显现出来,像是反讽”。等等。
不过,我们最好还是直接去读阿多诺。正是从“晚期风格”入手,他不仅使我们真正感到了贝多芬晚期的伟大,也感到了他的“现代性”之所在。贝多芬晚期所重获的那种颠覆的、批判的、嘲讽的艺术精神,是他前行的动力,也正是现代消费社会最缺乏的,因为阿多诺会说:“贝多芬从不过时,原因可能无他,是现实至今尚未赶上他的音乐”。
保罗.策兰的传记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