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哲学的界限及其超越
——论唯物史观的本质
01
历史哲学的界限
02
历史哲学的完成
03
历史哲学的超越
(1)参阅卢梭:《论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起因和基础》,北京:商务印书馆,第61页、第82页。
(2)李明辉教授赞同黎德尔观点,主张“将康德的历史哲学理解为’历史编纂之批判’,进而理解为’历史非理性之批判’(不是’历史理性之批判’)”。邓晓芒教授认为这是有道理的,并且针对把康德思想黑格尔化的理解提出了反驳,明确指出,“康德是把人类文化的历史合目的性看作自然目的论中的一个更深的反思阶段的表象,而不是一个超越于经验世界之上的’历史理性’的产物。因此康德不使用’历史理性’一词(这是黑格尔的用语),而到处采用’天意’这一说法。”参阅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第185页以及注释2,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3)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6页。
(4)卡西尔:《国家的神话》,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321页。
(5)(6)(7)(8)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61页,第13页,第285页,第348页。
(9)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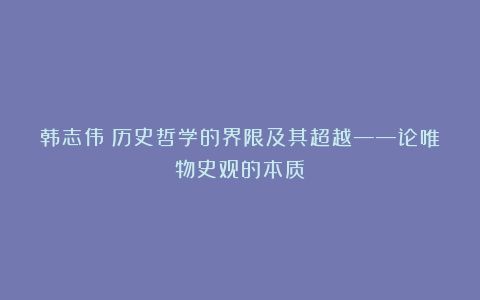
(10)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1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119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13页。
(13)洛维特:《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7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834页。
(16)《主义马克思经典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7)《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84页。
(18)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版,第100页。
本文出处:《东岳论丛》2011年第7期
文章采编:韩潇
排版:祁御
审核:说怿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