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藏”是弘艺丰于2024年推出的收藏文化传播专栏,从寻真、尚古、造境、品物等方面梳理中国收藏文化史,为大众讲解收藏行为的历史渊源和美学内涵。正如苏轼在《赤壁赋》中所云:“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无尽之收藏、无尽之宝藏,尔与吾共享。
本期海报图片:(传)[北宋]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本期概要】王羲之在会稽召集的兰亭之会,因为留下了《兰亭序》这卷“天下第一行书”,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文人雅集。自永和九年(353)到元祐元年(1086),历经七百余年的又一个春天,北宋首都开封城西的王诜宅第,也出现了一场集合当世名声最为显赫的文人的聚会。这场聚会不仅诞生了一幅由顶级画家李公麟亲笔绘制的《西园雅集图》,还有米芾的书法诗文。影响深远的是,“西园雅集”这一绘画主题在后世得到一次又一次的重复,竟至形成一套绘画传统。
在《无尽藏|大唐“兰亭”诡事录》一期中,我们讨论过与“兰亭雅集”有关的扑朔迷离的历史,一件看似并无疑义的作品,实际上也存在一些经不起推敲的细节。事实上,在不少研究者看来,由于李公麟原作的失传,“西园”与“兰亭”一样笼罩着重重疑点,以致有人提出西园雅集一事从未发生。本期文章即围绕“西园雅集”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
图 |(传)[北宋] 李公麟《西园雅集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左右滑动赏画
《弘艺丰·无尽藏》NO.18
西园雅集:兰亭之后的又一盛会
壹
《西园雅集图》的原作者:李公麟
“西园”的主人是当时北宋的当红驸马王诜。他是宋初开国功臣王全斌的后人,世居河南开封,自幼好读书,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名满京城。与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当时文化界名流颇有往来,自视甚高。《宣和画谱》卷十二称王诜:“所从游者皆一时之老师宿儒……其风流蕴藉,真有王谢家风气,若斯人之徒,顾岂易得哉!”宋英宗欣赏他的家世与才华,将女儿蜀国长公主下嫁于他。
为了此次聚会,王诜专门邀请李公麟来现场作画。李公麟被誉为“宋画第一人”,同样出身名门,也中过进士。不过在官场未能得意,反而扬名画坛,成为王诜的座上宾。《宣和画谱》载:
(李公麟)尤工人物,能分别状貌,使人望而知其为廊庙、馆阁、山林、草野、闾阎、臧荻、占舆、皂隶。至于动作态度、颦伸俯仰、大小善恶、与夫东西南北之人才分点画、尊卑贵贱、咸有区别,非若世俗画工混为一律。贵贱研丑止以肥红瘦黑分之。大抵公麟以立意为先,布置缘饰为次,其成染精致,俗工或可学焉,至率略简易处,则终不近也。
文人们在诗文书法之外,也开始用绘画表达个性和态度,绘画不再只是记录的工具。李公麟擅长人物画,继承了顾恺之和陆探微的风格。他的画不仅形似,还能通过人物的动作和表情传达出他们的性格和地位,达到神形兼备的境界,远超一般匠人。文人画发展到他这一时期,标准已从“形似”转变为“得意”。
图 | 李公麟像
李公麟的书法和诗文也很出色,有“晋人之风”。《宋史》称他“好古博学,长于诗,多识奇字,自夏商以来钟鼎尊彝,皆能考定世次,辨测款识”,在金石学方面亦颇有建树。宋代文人虽在朝堂上受困于党争,但私下里仍然尊文重道,不以立场不同而轻人,故王安石和苏东坡这对政治上立场不同的“宿敌”同时都是李公麟的好友。
图 | [宋] 李公麟《五马图》局部,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贰
画面人物与构图
这场在王诜宅邸“西园”举行的北宋顶级聚会,王诜一共邀请了十五位好友,包括“唐宋八大家”中的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张耒、秦观、晁补之、黄庭坚;“宋四家”之一的米芾;从日本来到中国求法巡礼的圆通和尚,著名的修道高士陈景元,大藏书家王钦臣,词人李之仪,制墨高手郑嘉会,画家蔡肇、刘泾,还有就是以上提及的大画家李公麟。
图 | [宋] 刘松年《西园雅集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左右滑动赏画
好在有米芾的详细记录,使《西园雅集图》中的重要内容得以被后世画家再现。释文首先说:
李伯时效唐小李将军为著色泉石云物、草木花竹,皆妙绝动人;而人物秀发,各肖其形,自有林下风味,无一点尘埃气。
米芾首先简单介绍了这幅画的作者李公麟,说他模仿唐代小李将军的画风,描绘泉水、山石、云雾、草木、花竹等景物,技艺精湛动人。而他画的人物形象清秀,各具特色,充满了竹林七贤般的风度和意味,没有沾染一丝世俗的尘埃。
图 | 《西园雅集图》局部 苏轼等
接下来介绍出现在雅集图中的人物。为首的是东坡先生苏轼,他戴着乌帽、穿着黄色道服,正提笔挥毫;旁边戴着仙桃巾、穿着紫色裘衣,坐着观看的是王晋卿(王诜);戴着幅巾、穿着青衣,坐在方凳上凝神而观的是丹阳蔡天启(蔡肇);李端叔(李之仪)扶着椅子定睛注视;后面侍立着晋卿的家姬,戴着云环翠饰,侍立在旁,流露出自然而然的富贵风韵。
图 | 《西园雅集图》局部 苏辙等
周遭有盘曲茂盛的孤松,并有凌霄花攀援缠绕,红绿相间。松树下有一张大石案,陈设着古器和瑶琴,芭蕉环绕一旁。苏子由(苏辙)坐在石磐旁边,戴着道帽、穿着紫衣,右手倚着石头,左手拿着一卷书正在品读;黄鲁直(黄庭坚)则是那个戴着团巾、穿着茧衣,手拿芭蕉扇仔细观看的人物;李伯时(李公麟)幅巾野褐,拿着横卷,正在创作陶渊明《归去来图》;晁无咎(晁无咎)披巾青服,抚肩而立;张文潜(张耒)跪坐倚石观画;郑靖老(郑嘉会)戴着道巾、穿着素衣,按膝而俯视,后面有一童子拿着灵寿杖侍立一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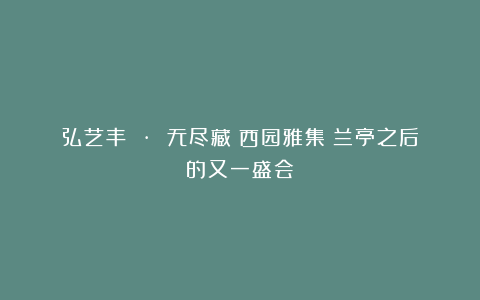
图 |《西园雅集图》局部 陈景元等
另有一组场景,描绘的是两人坐在古老的桧树下,其中一个戴着幅巾、穿着青衣,双手交叉在袖中侧耳倾听,这是秦少游(秦观);另一个戴着琴尾冠、穿着紫色道服,正在弹阮的是陈碧虚(陈景元),正和秦观交流音乐。
图 |《西园雅集图》局部 米芾等
米元章(米芾)自己戴着唐巾、穿着深衣,仰头在石头上题字;藏书家王仲至(王钦臣)双手交叉袖中,抬头仰观米芾。
图 |《西园雅集图》局部 圆通大师等
树林深处,只见一个头发蓬乱的顽童,捧着古砚站立;后面有锦石桥和竹径,在清溪深处蜿蜒,翠绿的树荫茂盛浓密。穿着袈裟的圆通大师坐在中间,正坐在蒲团上讲《无生论》;旁边还有一个戴着幅巾、穿着褐衣,专心聆听大师讲经的信众,这是刘巨济(刘泾)。两个人并坐在怪石上,下面有湍急的激流在大溪中奔腾而去。
相比之下,刘松年的版本非常接近原版人物,与米芾的描述几乎一致。而马远的版本则有他独特的风格:他将画卷从院外的小溪和翠绿的小路开始,家仆们从船上下来,忙碌地运送聚会所需的物品。苏轼独自出现,带着小童过桥,挥毫写字的人换成了米芾,人物从十六人增加到十八人,伺候的小童也多了几位。
图 | [宋] 马远《西园雅集图》,藏美国纳尔逊·艾金斯美术馆
马远没有拘泥于李公麟的画法,从北宋到南宋,从开封到临安,技法上已经有了很大变化。马远生活在南方,擅长画南方山水,细致刻画一草一木。他被称为“马一角”,喜欢在画面边角布局人物和山水,再加上南宋特色的大斧劈皴法,使整幅画显得苍劲有力,刚柔并济。
图 | [元] 赵孟頫《西园雅集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后世的画家基于米芾的记述,对《西园雅集图》的“二创”屡出新意。赵孟頫绘有《西园雅集图轴》、陈洪绶绘有《雅集图卷》,此外,唐寅、钱选、仇英、尤求、程仲坚、丁观鹏、石涛、华喦都绘有“西园雅集”主题的画作。正如米芾所说:
水石潺湲,风竹相吞,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呼!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辨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资,高僧羽流之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后之览者,不独图画之可观,亦足仿佛其人耳。
像这样汇集当世文学、诗词、藏书、金石、书法、丹青、僧道等等名流的文化盛宴,实在是人间难得的“清旷至乐”,它凝聚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终极理想追求。
图 | [明] 陈洪绶《雅集图卷》,藏上海博物馆
叁
理想还是现实——
对“西园雅集”的质疑
或许正是因为“西园雅集”和《西园雅集图》描绘的场景过于完美,后世有不少学者都表示不敢相信,于是围绕这幅画展开了连篇累牍的研究,试图说明这幅画纯粹出于想象。其中最具话题性的是由美国俄勒冈大学美术史系教授梁庄爱伦(Ellen Laing, 1933—)撰写的,题为《理想还是现实——“西园雅集”和〈西园雅集图〉考》(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 88,1968)的文章。她的结论振聋发聩、惊世骇俗,首先就否认了“西园雅集”的活动不曾存在,纯属“子虚乌有”,从而推导出《西园雅集图》的创作也纯属想象出来的文化乌托邦。至于“西园雅集”这个主题为何在中国画史上如此受欢迎,以至于成为传统人物画的一个重要母题,梁庄爱伦只能解释为“因为某些特殊的社会政治原因从中作梗”,似乎一切尽在不言中。
图 | [明] 唐寅《西园雅集图卷》局部,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她为何会得出如此颠覆性的结论?首先,这些人同时出现在一个特定场所,未免过于魔幻。参加雅集活动的“十六位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和艺术家”于“某年”的“某天”到王诜“在开封的西园雅集,他们吟诗、作画、弹阮,一同观赏书画作品,相得甚欢”,在她看来这根本不可能。其次,她说不同文献资料记载的参与者有出入,有的记载中以陈师道代替了郑清老,有的材料中李之仪、晁补之和郑清老的名字换成了王巩、元冲之和公素,有的材料中李之仪、郑清老的名字又分别被钱勰、陈师道所替代,等等。再次,“西园”二字在其他书里看不到,无论在与会者的文集中,还是汴京的地方志、园林史上,都没有提到王诜的“西园”。既然雅集的所在地既得不到落实,雅集活动本身就不能成立。最后,梁庄爱伦认为,当时人尤其是当事人的文字中都没有提供有关这次活动的任何材料,直至12世纪中期以后时过境迁,才出现了这方面的记载。
图 | [清] 石涛《西园雅集图卷》局部,藏上海博物馆
我们不难看出以上论证的漏洞。这些人在某时某地同时出现,固然有其“超现实”的可能,但这并不能成为否认雅集活动真实发生过的依据。王诜牵头的雅集活动在当时是远近闻名的“文人局”,《宋会要》《宣和画谱》《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均有明确记载,沉迷于聚会甚至成为日后政敌攻击他的把柄。即便并不存在某次聚会能一次性集齐上述提及的参加者,但仍可将米芾描述的画面场景理解为李公麟的艺术处理,而非据此断定雅集纯属虚构。
再者,鉴于《西园雅集图》可能综合了多场聚会的相关人物,后世记载中存在人名出入的现象自然也就不难解释。即便是现代的一场聚会,经过时间的流逝,回忆起来的内容也可能有所出入。至于以“西园”之名进行质疑,则更显偏颇。文人对地点的命名本就充满了象征、隐喻、泛指,一地多名实属常见,又怎能仅从名字入手就否认一个地方从未存在过?如果梁氏稍作查证,便能发现不少文人都在诗文中记录过王诜的园宅,只不过未直接冠以“西园”之名罢了。李公麟将此画作命名为“西园”,或许正是出于对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的仰慕,借此典故颂扬文人雅集之风流。
最后,不可忽视的是背后的政治因素——“西园雅集”的参与者多为旧党中人,为避免给政敌留下攻击的把柄,他们在诗文集中对此类活动往往讳莫如深,仅作含蓄提及,这也是不难理解的现象罢。
图 | [明] 仇英《西园雅集图》,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肆
结语
西方艺术史家的结论下得过于激进,不过因此引发的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也确实证明李公麟的画与米芾的题记存在一定艺术处理的成分。
如今基本可以确定的是,在元祐至元丰年间,王诜经常邀请一些对新法持异议的艺术家和文人前来私家园宅相聚,这些文化界名流宴饮、挥毫、赏画、吟诗、弹阮、题石、讲经、修道……相得甚欢。之后,作为与会者之一的画家李公麟便选取其中十六人合绘于一幅之上,并将其命名为《西园雅集图》。或许由于政治的原因,这幅作品并未被大肆张扬。
南宋以后,新党失势,旧党复辟,此图才公开地得到传播,成为人们追慕崇尚的话题。也许是李公麟本就创作了不止一幅,也许是后人传摹时发生了变动,于是后世流传的《西园雅集图》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形制和风格。至于李公麟的原作,则早就湮灭难寻了。
宋人清旷之乐,后世风流难再,与其费尽心思地考证雅集是否真实存在,不如不置褒贬地将之看作一种浓缩的文人理想。艺术的魅力不在“真”而在乎“美”,如果这幅场景和主题能给后世观者创造出足够的审美体验,那便完整了它的艺术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