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保管
石金生
我笔下的老保管,是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我们生产队的一位实物保管员,他叫石金生(1928.7——2008.7,中共党员)。村中也只有这一户石姓人家,听说是外迁到本地的,因为人耿直厚道,大公无私,虽然名不见经传,但在我心里他能被称得上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全村人的心目中口碑都是极好的。
我记忆中的老保管是个黑红色脸膛的汉子,个头不高,可能是因为长期从事体力劳动的缘故,有点驼背。外八字脚,经常总穿着一身老蓝色粗布衣衫,肩上搭着一条长方形抓绒毛巾(应该是便于擦汗),还有一个旱烟斗挂在腰间。他的做事风格是:走路快如风,说话如洪钟,干活如刀切葱(快速利落),他是个直性子爱暴躁。也许就是因为这些特点,在近三十年中大家总推选他作为生产队里的保管员,还担任过多年的生产队长。
那还是人民公社的年代。基层工作是由县——公社——大队三级集体管理,小队是最基层的单位。土地集中使用,集体劳动,集体分配是当时的农村生产模式,也就是所为的大锅饭(并非是在一个锅里吃饭)。所以有一个大公无私的生产队保管员尤为重要。因为全队里所有的生产资料:农药、化肥、粮食、种子、饲料等都归保管员一人管理保存,集体仓库一把大铁锁的钥匙他要随身携带着,以备不时之需。“文革”后期,派性斗争的余毒久聚不散,在农村反映也很尖锐。“造反派”与“老保派”相互拆台,相互诋毁,相互提防,打架斗殴时有发生。而老保管却能独善其身,两派人员都能拥戴他。
然而,千万不要以为当了集体保管员就有多么的风光无限,高高在上,权力就可以随便支配了。听村上的老人们说:1958年的大跃进时期,浮夸风盛行,很多基层领导为了迎合上级的浮夸政策,毫无根据的向上级汇报吹嘘农村亩产能达到数千斤甚至上万斤。当上级工作组派人检查落实粮食数量时,有些生产队就在仓库里围起巨大的粮囤,粮囤的下面铺上厚厚的稻草麦糠之类,然后用凉席或被褥覆在上面,最后再铺上一层小麦来充数。而我们队的石金生保管员却没有主张作假。当上级工作组巡视到我们队仓库时却看不到有粮囤,只看到几袋预留的粮食种子,就有些气急败坏,命人要把种子也带走,老保管拼命护着种子,据理力争的说:“种子是留着来年种庄稼用的,不能带走!”工作组就把老保管本人带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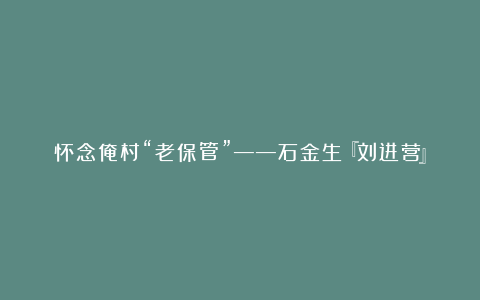
老保管农业经验很丰富,按节令种植与收获都能把握的很好,农田管理也很有诀窍。他曾经指导我怎样锄地,告诉大家“六月草半打倒,砍断不如埋住好”的经验。他身为保管员,分发东西是他最大的麻烦事。无论是分粮食还是分柴草,都是由他掌握大称的。比如红薯、萝卜都是要在原来种植田地里即时过称分给每家每户的,细粮和柴草是要在打谷场上分给各家各户。经常是分完东西都已经是披星戴月了,老保管只能忙完最后才顾上搬运自家的东西回家的,这种情况下没少受到家人责怪。
老保管很多时候是很严厉的,他不苟言笑,以至于我们常常看到他就有点怕。但他有时也温和的。清楚的记得:在我十三岁(读四年级)那年暑假的一天,老保管看见我就把我叫住了,他面带笑容的说让我跟他走,然后把我带到了队里的养驴棚门口对我说,这头小驴驹四五个月大了,因为母驴缺奶,小驴驹缺少营瘦得很,你暑假没事就放这头驴驹吧,每天给你记4个工分。我听了心里又高兴又有顾虑。高兴的是自己也能挣工分了,忧虑的是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能胜任,小驴尥蹶子(liaojuezi)不知道能不能控制得住,还担心万一自己把驴放死了负不起这个责任的。老保管看我犹豫,就和颜悦色的给我讲了放驴的方法技巧,还说“你要是把这驴驹养胖了可是有奖励的哦!我打消了顾虑,欣然接受了任务。暑假结束时,小驴驹真的被我养肥了,老保管在群众会上还表扬了我,并且在后来的几年里每逢暑假,老保管总要交给我一头小牛或者驴驹让我放养——放养就是每天牵着它到野外吃青草,及时让它喝水,不让渴着饿着了。
每当回忆起那几年为集体放牛、放驴的暑假生活,总觉得充满着无比的快乐和幸福感,十分怀恋那段日子。那里面也蕴含着老保管对我关切爱、鼓励、信任和期望。它承载着我少年时代的美好印记。把这些叙述出来,仍觉得言犹未尽。我想让后辈们记住:我们村曾经有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保管,他为集体为群众呕心沥血,做出过很大贡献。聊以寄托我对老保管(二伯伯)深切的怀念和哀思!
主 编 | 马营 副主编 | 陈峰 题 字 | 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