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F版下载:http://ldmzyj.
作者投稿系统: https://ldmz.cbpt.cnki.net
内容提要:二战后美国的海外军事干涉在行动上呈现多边主义特征,积极招揽包括盟国、安全伙伴、所干涉地区国家等其他国家,组建临时的军事联合阵线开展军事干涉。以往研究认为正式同盟义务对该国选择是否参与美国领导的多国联合军事干涉起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美国的对外干涉超出了联盟条约的防御义务,盟国也并不一定都会参与美国的联合阵线。本文从美国盟友选择性参与美国的多国联合军事干涉现象出发,研究盟国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的动因与理论机制。本文基于对军事干涉与联合阵线的文献回顾,运用成本收益分析、冲突转移理论与武力使用偏好分析,从领导人个人层面因素提出领导人任期限制与鹰派倾向影响盟国领导人做出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决策的假设。通过对二战后美国领导的八次军事干涉联合阵线中56个盟国的参与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领导人任期限制因素对于盟国参与联合阵线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盟国领导人在做出联合阵线参与决策的过程中,主要基于制度约束下对个人任期限制的理性考量,较少为其武力使用偏好所左右。
关 键 词:军事干涉 联合阵线 盟国 任期限制 鹰派倾向
作者简介:梁佩锋,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漆海霞,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
2011年初,叙利亚全国陆续爆发抗议政府的大型示威活动,随后反政府势力不断壮大并积极开展叛乱活动,恐怖组织“伊斯兰国”趁机逐步壮大。2014年9月,美国国会授权美军打击“伊斯兰国”,并发动空袭行动正式对叙利亚内战进行军事干涉。在美国建立打击“伊斯兰国”多国联盟的号召下,14个国家参与到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行动中,其中美国的传统北约盟友英国、法国等纷纷积极响应。
美国军事干涉呈现多边主义的特征,积极招揽盟友和安全伙伴,以组建多国部队的方式向所干涉地区的国家进行军事干涉。冷战后美国主导的6次大规模军事干涉中,都能看到多国部队的身影,如1991年海湾战争有34国参与,1995年波斯尼亚战争有24国参与,1999年科索沃战争有19国参与,2001年阿富汗战争有48国参与,2003年伊拉克战争有49国参与,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则有15国参与。
许多研究军事干涉的学者都认为,正式联盟在多国参与联合军事干涉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对二战后美国军事干涉案例的考察,我们发现美国的多国联合军事干涉更侧重于以临时的联合阵线形式,即与意愿相近的国家组建联合阵线(coalition of the willing)进行军事干涉,联合的对象并不局限于盟友国家。除此之外,由于美国的对外干涉超出了联盟条约的防御义务,盟友国家也并不一定都会参与美国的联合阵线。例如,尽管收到了美国的邀请,英国并没参与美国领导的1983年对格林纳达和1994年对海地进行干涉的联合阵线中。然而,英国却参与了1991年伊拉克禁飞区行动和1993年索马里干涉行动的美国联合阵线。如何解释美国的重要盟国英国选择性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或者更进一步,影响美国盟国选择性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的因素是什么呢?这是本文主要研究的问题。
一 文献回顾
近年来多国联合军事干涉频频发生在南欧、中东、非洲,引起被干涉国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政治危机,加剧了国内冲突向外蔓延的风险,对国际和地区安全造成重大威胁。因此,研究多国联合军事干涉形成的影响因素,有助于发生国内冲突的国家预见可能发生的大规模干涉,提前采取适当的危机管控措施,避免外国势力在本国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从而维护国家及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一)国际权力格局与国际规范的影响
在探究体系结构因素对军事干涉的影响时,学者主要从冷战时期出发,讨论两极体系对一国进行军事干涉决策的影响。尹美英经实证研究后发现,影响美国在冷战期间对他国国内冲突进行干涉的因素包括苏联及其盟国是否干涉,以及被干涉国冲突一方是否信奉共产主义。本杰明·福特汉姆在对美国军事干涉国内或国际冲突的实证研究中发现,当盟国参与冲突,或敌国对冲突进行干涉时,美国军事干涉国内或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会显著增加。然而,马克·马伦巴赫等人的实证研究则发现敌国进行军事干涉对美国军事干涉决策的影响仅在冷战期间才出现统计上的显著性,这更加体现了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敌对状态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影响。
除此之外,国际规范也是学者在体系层次中用以解释军事干涉决策的因素。玛莎·芬尼莫尔运用建构主义框架分析干涉规范的变化,讨论特定的武力使用即军事干涉目的的系统性变化。她认为,共享观念与规范结构塑造了国家对利益的认知,建构了武力使用的行动目的与意义。社会目的的新信念通过建立新的行为规范和行动理性,建构了军事干涉新的意义和规则,最终改变国家的军事干涉行为模式。
(二)盟国偏好的影响
基于潜在干涉国与内战发生国的战略互动视角,以往研究从两国的军事联系、经济联系与族群联系出发,讨论潜在干涉国的军事干涉决策。首先,当潜在干涉国与内战发生国之间存在军事联盟关系时,潜在干涉国为维护其对内战发生国的联盟领导地位,可能对内战发生国进行军事干涉。迈克尔·芬德利的实证研究发现,与内战发生国政府存在联盟关系时,潜在干涉国干涉内战并支持对方政府的概率显著上升。但当军事联系从军事联盟放宽至军事援助时,尹美英的实证研究显示美国对内战发生国的军事援助的数量增加并不会导致美国军事干涉内战的可能性上升,这说明军事联系的深度对潜在干涉国的军事干涉决策影响有限。
其次,潜在干涉国与内战发生国的经济联系影响干涉国的军事干涉。当潜在干涉国与内战发生国中的一方有经济联系,潜在干涉国为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会倾向于干涉并支持与其有经济联系的一方。为了衡量潜在干涉国与内战发生国的经济联系,学者主要运用内战发生国战略自然资源禀赋,或两国间贸易关系的重要程度来探析。文森佐·博夫等学者通过研究石油资源在军事干涉中的推动作用,分析潜在干涉国做出干涉决策的经济动机。当内战发生国石油资源储备丰富、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处于垄断地位且潜在干涉国对石油需求较高时,更可能对内战发生国进行军事干涉。本杰明·福特汉姆认为,经济联系对美国军事干涉决策具有间接影响,这体现于长期的贸易联系可以促成同贸易国的安全同盟,从而对军事干涉决策产生影响。
除此之外,潜在干涉国与内战发生国的族群联系也影响潜在干涉国的军事干涉决策。斯蒂芬·塞德曼认为,共同的族群、宗教、文化使得潜在干涉国民众自发产生对国外同族的身份认同,族群身份认同继而塑造选民的对外政策偏好。因此,当一国内部冲突中一方与潜在干涉国领导人的支持选民团体有族群联系时,面临选民的军事干涉要求,领导人为赢得选民支持,会选择军事干涉并支持与选民有族群联系的一方。马丁·奥斯特沃·诺姆进一步研究族群在内战发生国与潜在干涉国的政治地位对干涉国军事干涉的影响,他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当潜在干涉国的边缘族群与内战发生国的一方存在跨国族群联系时,潜在干涉国为防止国内分裂主义的产生,更可能对内战发生国进行军事干涉。上述文章从干涉国与被干涉国的战略互动出发,并不能解释在现实中当干涉的对象不同时,英国、法国等国家会选择性追随美国参与多国联合军事干涉的现象,因此,对于本文研究问题的解释存在一定的不足。
潜在干涉国的干预决策不仅受到与内战发生国战略互动的影响,还受到其他潜在干涉国之间战略互动的影响。芬德利的研究阐述了潜在干涉国之间的战略关系对干涉选边问题的影响,当互为敌人的一方对内战发生国进行军事干涉并支持内战发生国政府时,另一方进行干涉并支持内战发生国反对派的概率大幅上升,反之也成立。当同盟国对内战发生国进行军事干涉并支持政府时,潜在干涉者进行干涉并支持政府的概率也上升。与芬德利等讨论潜在干涉者之间的战略关系不同,斯蒂芬·根特从潜在干涉国之间的战略偏好差异出发,提出潜在干涉国偏好差异影响联合干涉的概率。当潜在干涉国的偏好相同时,各方会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对搭便车行为的厌恶使得潜在干涉国在利益相同时不太可能进行联合干涉。潜在干涉国更倾向于加入与其利益不同的干涉国所进行的干涉,以便于通过加入改变干涉收益。上述讨论潜在干涉国之间互动的两篇文章都存在不足。在芬德利的研究中,同盟国进行干涉并支持反对派,与潜在干涉国进行干涉并支持反对派的概率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联盟关系对于选边性军事干涉的影响仍有待研究。此外,由于军事干涉要求的军事行动超出了大多数联盟条约的义务规定,联盟条约对联盟成员参与多国联合干涉不具有约束性,且非盟友国家也可以参与军事干涉,因此,联盟因素在国家参与多国联合干涉动因的解释机制上存在缺陷。根特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具有联盟关系的大国战略利益差异对干涉决策的影响,而对具有联盟关系的次强国家以及小国的干涉决策研究不足。
潜在干涉国自身的特征,如潜在干涉国的政权类型、潜在干涉国的国内政治互动、潜在干涉国的地缘毗邻度以及潜在干涉国的区域利益诉求也对潜在干涉国的军事干涉决策有影响作用。关于潜在干涉国政权类型对军事干涉决策的影响作用,以往的学者将国家政权类型分为民主政体与独裁政体进行二元分析。布鲁斯·梅斯奎塔等学者提出,领导人出于政治生存需要,其外交决策需要得到“胜利同盟”的支持,即维持领导人权力所必需的选民团体的许可。鉴于民主国家定期选举的制度,民主国家的胜利同盟比独裁国家的胜利同盟影响更大。同时,国家提供的私人产品只在胜利同盟内部分配,而公共产品在所有选民中分配,胜利同盟的规模越小,胜利同盟成员获得的私人产品就越多。因此,胜利同盟较小的独裁国家领导者倾向于用私人物品满足胜利同盟需要,而民主国家则倾向于使用公共物品满足胜利同盟。根据这一逻辑,古贺运用实证研究检验了政权类型对国家军事干涉决策的影响,发现独裁国家倾向于对能带来更多私人产品的国家进行军事干涉,不太注重干涉成功的概率,而民主国家出于维护政权需要,对干涉成功概率十分关注,因此,民主国家干涉决策十分谨慎,干涉成功率也较高。
杰弗里·皮克林在批评已有政权类型二元简单分类的基础上,按照政权成熟度将政体分为四类,研究其对国家海外军事干涉的影响。其实证研究发现当面临精英与民众骚乱时,成熟的民主国家和过渡中的独裁国家领导人倾向于对外干涉,而成熟的独裁国家和过渡中的民主国家则相反。具体而言,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国内领导人在面临各种利益集团的政策要求时,可以利用对外干涉转移利益集团对国内问题的关注。对于过渡中的独裁国家,领导人的决策受到胜利同盟中精英的影响,通过对外干涉可以转移精英注意力,或者用干涉获得的私人产品满足精英需求。按照上述理论,独裁国家在干涉中更关注私人产品,而民主国家更关注公共产品,但从经验事实上看冷战后的许多民主国家表现出通过干涉获得私人产品(石油等自然资源)的渴望。因此,政权因素的解释机制应用存在疑惑。
潜在干涉国国内政治互动也能影响其军事干涉决策。乔恩·韦斯特恩运用美国历史上的五次干涉案例分析,认为在美国的军事干预决策中,政府、精英和民众的互动有重要影响。虽然不同的精英团体在干涉意愿和干涉动机上存在差异,但信息传递能力更高的精英团体能够通过媒体更有力地传递其对于干涉的意愿与理由,从而影响民意。媒体对别国内部冲突报道存在滞后性,在媒体报道较少的初期,信息只能通过政府获得,政府可以对冲突信息进行控制。随着媒体报道增多,主导信息传递的精英团体可以利用信息影响民意,从而利用民意对政府施压。民意对于政府的干涉决策起重要作用,如果干涉决策缺乏民众支持,领导人为政治生存考量,倾向于不对别国进行军事干涉。
潜在干涉国与内战发生国的毗邻性也影响着干涉国的干涉决策。雅各布·凯斯曼引入内战的传染性概念,解释如果一国内部冲突对地区稳定的威胁性越大,其周边国家会越倾向于对冲突国进行军事干涉。针对非周边国家的干涉行为,凯斯曼将内战传染性与潜在干涉国的区域利益诉求结合,指出当冲突国内部冲突向邻近国家传染时,若潜在干涉国在这些邻近国家存在区域利益,则潜在干涉国的区域利益受到冲突传染的威胁。因此,随着内战蔓延到对潜在干涉国有区域利益的周边国家的可能性增加,潜在干涉国进行军事干涉的概率上升。
(三)领导人的影响
对于军事干涉的决策,不仅取决于体系结构和国家因素,还受到具体决策者(领导人)的影响。领导人主要通过观念机制影响干涉决策,这里的观念既包含领导人个人信念,也包括集体信念。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学者曾认为既有信念影响个人使用军事手段实现目标的倾向性。在既有信念的影响下,一件特定事情的发生可能不会改变领导人或集体关于军事干涉的信念。基于对既有信念的解释,约翰·内文和杰弗里·皮克林的研究都发现只有在遭遇一系列干涉失败的情况下,国家军事干涉的可能性才会降低。
基于既有信念的解释,伊丽莎白·桑德斯认为领导人信念在干涉发起与干涉策略的选择中起重要作用。她将领导人分成“内部关注”型与“外部关注”型两类,内部关注型领导人认为冲突国外交政策的威胁性与其国内政治制度存在因果关系,外部关注型领导人倾向于直接从冲突国的外交政策中诊断威胁而不关注其国内政治制度。两类领导人对于威胁来源的信念影响了其对干涉的分析及对干涉策略的选择。内部关注型领导人倾向于实施变革性军事干涉,通过干涉变革他国政治制度,而外部关注型领导人倾向于实施非变革性军事干涉,仅通过干涉变革他国外交政策。
上述对于信念的影响作用解释存在一定的缺陷。领导人在外交决策上的判断虽然基于既有信念,但这些判断是领导人及其顾问在大学或政府机构等体系制度下的产物。因此,领导人的决策受制于信念形成背后的制度,而不仅仅受信念本身的影响。对此,笔者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从领导人个人层次出发,找到影响盟国参与美国领导的多国联合军事干涉的因素。
二 研究假设
借鉴以往领导人因素对冲突发起与卷入影响作用的解释机制,笔者将以“任期限制”与“鹰派倾向”作为核心自变量,提出研究假设与解释机制。在研究假设基础上,笔者将运用面板数据logit模型检验核心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
(一)军事联合阵线
在现有的学术研究中,学者们对军事联合阵线这一概念形成了概念性与操作性定义。威廉·盖姆森对军事联合阵线作了经典的概念性定义,他认为军事联合阵线是“临时的、以方式为导向的、个体或团体之间的联盟,联盟成员之间目标各异”。哈维·斯塔尔和阿拉斯泰尔·史密斯给出更为具体的定义,认为军事联合阵线是“战争中站在同一阵线战斗的国家”。在盖姆森定义的基础上,斯科特·沃尔福德则侧重于危机形成阶段的定义,认为军事性联合阵线是“在国际危机中,由两个或以上国家组成,对另一国家威胁使用武力的国家集团”。随着关于军事联合阵线的实证研究不断深入,军事联合阵线的操作性定义也逐渐形成。多湖淳强调军事联合阵线中需要有一国采取部署军事力量的实质性行动,并且联合阵线的主导国在提供联合阵线力量与军事行动指挥中占主导。泰伦斯·查普曼提出,联合阵线是由在危机中处于同一阵线的国家组成,但查普曼所指的同一阵线既包含军事层面也包含外交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在军事合作领域中也存在与联合阵线(Coalition)相近又容易混淆的概念——联盟(Alliance),两者经常被互换使用,但在概念上两者存在较大差异。从两者结构而言,联盟是基于通过正式的条约或协议达成的安全合作安排,其形成决定了其结构高度制度化,联盟成员在联盟条约的机制下承担规定义务,达成互惠。联合阵线则是国家或国际组织在特定情况下就具体问题领域达成共同立场或行动结成的非正式合作,特定情况包括国际冲突或危机等。联合阵线的形成是基于参与国与联合阵线发起国进行双边谈判的结果,联合阵线参与国所承担的义务根据具体情况单独确定。联合阵线的形成体现了其结构的松散性。
从二战后的军事联合阵线组成阵容来看,参与联合阵线的国家大多与联合阵线的领导国存在联盟关系,因此,参与国做出参与联合阵线的决策和其与领导国的联盟关系之间的逻辑值得深思。参与国做出参与联合阵线的决策是否是因为两国联盟关系的存在,或是联盟条约的设置而产生?又或是国家为了维护联盟承诺,导致被牵连而被迫参与军事行动?由于联合阵线参与国并不局限于与联合阵线领导国存在联盟关系的国家,因此,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应该分为两种情况。当联合阵线成员国并非领导国的盟友,则“联盟关系导致做出参与联合阵线的决策”的逻辑并不成立,在此情况下非盟国针对共同目标与共同利益组成联合阵线,联合阵线目标达成后则解散。
针对正式盟国而言,“联盟关系的存在导致做出参与联合阵线决策”的推论建立在联盟可靠性的理论上,这一理论认为缔约盟国对联盟条约精心设计,为其设定不同程度的军事合作机制,能够提高联盟可靠性,而可靠的联盟关系会促使在未来该国处于军事冲突时其盟国能够提供战时援助并威慑对手。按照上述定论,应用在联合阵线参与决策中的逻辑应该为,盟国对盟约中军事合作机制的设计能够提高联盟可靠性,使得盟国做出参与联合阵线的决策,在军事冲突中援助另一方。然而,即使联盟条约明确规定了国家将采取何种行动、何种方式援助盟国,国家在做出参与联合阵线决策后,在行动上也可能随着实际利益的变化而产生与规定偏离的情况,这与联盟条约能够揭示国家未来行动意图的观点相背离。
本文重点研究的是军事干涉中的联合阵线,即国家间为实施对外军事干涉所形成的临时性合作安排形式,联合阵线的参与国需要承担派遣作战人员、搜集提供情报、进行后勤援助等义务。与正式联盟条约侧重于防御义务相比,军事联合阵线的任务侧重于军事进攻,超越了一般联盟条约义务规定的范围。因此,参与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并非联盟成员的义务,多边军事联盟成员可以选择性参与军事联合阵线。在此,本文需要考察的问题是,美国的盟友为何作出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决策?
以往关于军事联合阵线参与动因的研究,有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早期的军事联合阵线参与动因研究侧重于运用联盟理论进行案例分析,阐明联盟关系对盟国参与的影响作用。无可否认的是,联盟政治是影响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参与的关键因素,对盟友提供的安全保障与经济利益促使国家为盟友的军事干涉行动提供军事支持。但是这些研究较多侧重于研究一次军事干涉案例中的联合阵线情况,或是仅通过案例追踪重点研究盟友中大国的参与情况,并没有解释清楚所有盟友内部对于多边军事干涉行为参与上的差异。随着国际政治领域定量化研究趋势增强,对于军事联合阵线参与动因的定量研究逐渐增多。多湖淳通过对体系层面、领导国—参与国二元关系层面、参与国国内层面与联合阵线行动性质层面等关键因素的实证检验,发现与美国拥有共同语言、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联合阵线获得联合国授权等因素是影响各国参与美国领导的联合阵线的重要因素。在多湖淳研究的基础上,此后学者们集中研究特定层面上的核心自变量。在美国—参与国二元关系层面,大卫·莱克通过建立各国对美国的安全等级指数与经济等级指数指标,发现国家安全等级指数与经济等级指数越高,即在安全上与经济上越依附美国,则越可能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联合阵线。斯尔詹·武切蒂奇通过研究英语和英语圈属性变量对联合阵线参与的影响作用,发现英语与英语圈属性使得国家形成身份认同,这一身份认同促使国家与美国更加亲近,更愿意去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联合阵线。玛丽娜·亨克则集中研究美国与各国建立的嵌入性外交联系对各国参与美国军事联合阵线的影响,她指出外交联系便于美国与潜在参与国传递利益偏好的信息,以及建立利益支付的渠道,实证结果证明与美国嵌入性外交联系程度越深的国家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联合阵线概率越高。斯科特·沃尔福德研究领导国与潜在参与国对外政策偏好差异对国家参与军事联合阵线的影响,其实证结果显示若领导国与潜在参与国对外政策偏好越一致,潜在参与国追随美国参与联合阵线的概率越高。在潜在参与国国内层面,多湖淳深入研究了国内政治状态与经济状态对于国家参与军事联合阵线的抑制作用,当国内出现骚乱或暴力抗议,或者正在发生经济衰退时,国家分配军事资源到国外开展军事行动的意愿降低,因此参与军事联合阵线的可能性降低。在潜在参与国领导者层面,斯科特·沃尔福德提出政治不安全的领导人为了赢得继续执政的机会,会更愿意做出参与军事联合阵线的决策,认为政治不安全的领导人为了赢得继续执政的机会,会更愿意接受联合阵线,企图以国外层面的成功证明领导人的能力,避免可能失去领导职位的结局。
从上述案例研究或是定量研究来看,以往的学者们对于军事联合阵线参与动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领导国—参与国二元关系层面。然而,关于军事联合阵线参与行动决策,无论是领导国—参与国二元关系层面还是国内政治层面等因素,这些因素最终都是通过影响领导人的决策考量发挥作用的。但现有直接着力于领导人个人决策层面的研究较少,已有关于领导人层面影响因素的研究集中在政治不安全程度,其隐含的解释逻辑为领导人决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寻求连任。但在现实生活中,拥有限制领导人任期长度的法律制度的国家比比皆是,并不是所有的领导人在执政任期届满后都能拥有继续参与选举的机会。当民主国家领导人面临任期限制时,决策的出发点自然排除了通过在国外战场上证明自身执政能力以寻求连任的考量。其次,刨除民主国家领导人任期受到的法律约束影响其决策考量外,领导人自身对于武力使用的偏好也可能对决策产生影响作用,然而以往的研究对领导人自身偏好影响作用的涉猎较少。对于大多数实行民主制度的美国盟国而言,任期限制因素与领导人对武力使用的偏好是否对领导人参与军事联合阵线组建的决策具有影响作用,这是本文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领导人因素
民主国家领导人任期受到限制在国际政治中并不罕见,常见的任期限制有以下几种形式:(1)领导人在连任竞选中落败;(2)领导人计划退休,任期届满后自愿不选择连任竞选;(3)法律规定领导人在特定任期届满后不能继续执政。在这几种形式下,领导人因为法律限制了其任期长短,因此,这些领导人被形象地称为政治上的“跛脚鸭”。由于任期受到限制,“跛脚鸭”领导人通常面临着任期最后阶段的问题。在任期的最后阶段,领导人对其他政客的政治影响力逐渐下降。然而,任期限制也改变了领导人在最后任期内的激励,在无须担忧选举连任的情况下,领导人在政治决策上具有更多的自由裁量权,其决策的出发点也从寻求连任成功转移到更多强调谋求公共利益。
现有国际关系研究对于民主国家领导人任期因素的研究,集中于任期限制与领导者做出发起冲突决策两者之间的关系。然而,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机制,并通过不同的研究数据获得了实证结果支持。因此,对于任期假设通过何种机制影响武力使用的另一种方式——军事联合阵线,还须具体分析不同解释的影响机制。
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现有的学者们集中于任期限制对领导人的成本或收益方面的差异分析,解释任期限制如何改变领导人做出发起冲突决策的激励。詹姆斯·费伦(James D. Fearon)在关于国内观众成本与国际争端的研究中提出,失败的国际冲突会招致国内政治观众的批评,降低选民支持率甚至失去执政合法性,从而提高谋求连任的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国内观众成本。因此,谋求竞选连任的领导人对国内观众成本较为敏感,基于避免国内观众成本增加的风险考量,会对发起或卷入国外冲突采取谨慎的态度。对于任期受限的跛脚鸭式领导人而言,他们并不需要谋求竞选连任,对选民的偏好关注需求较小,因此,其对国内观众成本的敏感性较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跛脚鸭式领导人会更倾向于参与国际军事冲突。
任期限制同样会改变领导人的收益分析。贾科莫·基奥查和海恩·戈曼斯认为,发起国际冲突可能为领导人带来执政时间延长或因任期限制改变带来的收益。首先,国际冲突通常发生于选举之前,到最后任期的领导人可以利用国家卷入国际冲突的机会,以避免国内政权更迭带来局势动荡为借口来延迟选举,从而实现执政时间延长的目的。其次,在任期届满前取得国际冲突的胜利可以为领导人积累政治资本,使其有机会推翻以往关于政治权力更迭的规章制度,包括对于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按照上述逻辑,如果跛脚鸭式领导人拥有推翻任期时长限制的政治野心,卷入国际冲突便为其提供了实现政治野心的机会。
实证检验结果为成本收益分析解释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肖恩·齐格勒等人在任期限制改变领导人成本收益分析的假设上,对48个具有任期限制约束的民主国家在1976—2000年的冲突卷入决策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即将任期届满的领导人相比要竞选连任的领导人而言更有可能做出卷入冲突的决策。此外,葆拉·康科尼等人在其关于选举问责制与民主和平的研究中提出,在武力使用决策上,任期受限的领导人在决策考量上不受选民群体偏好所限,其国内观众成本较低,因此,会比可以连任竞选的领导人更倾向于参与国际军事冲突。其实证结果也支持面临任期限制的民主国家领导人更容易做出冲突发起决策。
事实上,在任期限制与领导者做出发起冲突决策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已有学者从冲突转移理论讨论任期限制约束如何改变领导人做出发起冲突决策的激励。冲突转移理论认为,民主国家领导人卷入国际冲突的动机是将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从国内问题转移到国际冲突中。当国内问题对民主国家领导人的国内政治支持水平产生负面影响、危及其连任竞选结果时,民主国家领导人可以通过实施高风险的外交政策,在国外使用武力发动军事冲突,将民众注意力从国内问题转向国外冲突。如果政府在国外使用武力并取得成功,那么国内的观众可以重新评估领导人与其政府的能力,并且增加对现任领导人的政治支持,从而加大其竞选连任成功的概率。
然而,任期限制改变了领导人对于发起转移性冲突的激励,不同于可连任竞选的领导人担忧国内问题对其连任竞选产生负面影响,任期限制使得跛脚鸭式领导人无须参与任期届满后的选举,因此,不必如可连任竞选的领导人一般担心本任期内产生的国内问题对其日后选举带来负面影响。即便是在任期内面临负面的国内问题(如经济衰退等),最后任期内的领导人也无须像可连任竞选的领导人利用冲突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按照这一逻辑而言,可连任竞选的领导人对于冲突卷入的倾向应高于受到任期限制约束的领导人。杰夫·卡特和蒂莫西·诺德斯特伦在关于任期限制与国际冲突的实证研究中,运用1960—2001年间各国领导人与军事冲突观测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任期限制对冲突发起呈负向影响,即受到任期限制约束的领导人更不可能卷入国际冲突。肖恩·齐格勒等人的研究也部分证实了该观点,他们发现在国内发生经济衰退时,拥有重新选举机会的民主国家领导人做出冲突发起决策的可能性更高,但经济衰退对于跛脚鸭式领导人发起冲突决策却没有相关性。但由于该研究仅包括1970—2000年48个具有任期限制约束的民主国家数据,其研究数据的时间与空间维度不如上面杰夫·卡特和蒂莫西·诺德斯特伦研究的完善,因此,研究结果仅部分证实上述观点。
尽管上述研究都是围绕任期限制与冲突发起等之间的关系,其具体问题与本文有所差异,但是两者研究方向大致围绕同一主题——领导人任期限制与国外武力使用的理性决策之间的关系。因此,对于属于多边军事合作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其行动成本由各国分摊,军事资源更为集中,从领导人理性决策角度出发,属于比单边发起军事冲突更为便利的国外武力使用选项。以往研究表明了任期限制对于武力使用的多种可能性关系与理论解释,因此,本文基于与以往研究不同的解释机制,做出两种竞争性假设,并在接下来的实证研究中求证何种解释机制符合领导人关于军事干涉联合阵线的参与决策。
从成本收益分析出发,当面临美国领导的军事联合阵线的参与邀请时,在面临军事干涉联合阵线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谋求竞选连任的盟国领导人会对参与军事干涉联合阵线采取谨慎的态度,以避免国内观众成本增加的风险。任期受限的跛脚鸭式盟国领导人并不需要谋求竞选连任,因此,其对国内观众成本的敏感性较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跛脚鸭式盟国领导人会更倾向于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基于上述逻辑我们可以作出以下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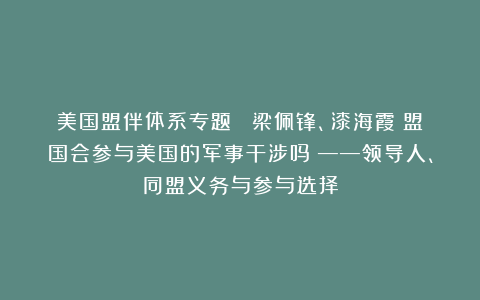
H1a(任期预期假设):相比能够再次竞选连任的领导人,任期受到限制的盟国领导人作出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联合阵线决策的可能性更高。
从冲突转移理论出发,当面临美国领导的军事联合阵线发出的邀请时,在选举连任的激励下,拥有再次竞选连任资格的盟国领导人更有可能选择参与比单边军事行动成本更低、综合军事实力更强的军事联合阵线,希望通过海外军事合作的成功增加国内支持并转移国内观众注意力。而对于任期受到限制的盟国领导人而言,其选举连任资格被法律剥夺使其无须考虑往后的政治生存问题,其决策出发点转移至谋求公众利益。在避免军事冲突通常被认为符合公众利益的前提下,任期限制促使盟国领导人极力避免卷入国外的军事行动,因此,选择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联合阵线的可能性会更小。基于上述逻辑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假设:
H1b(冲突转移假设):相比能够再次竞选连任的领导人,任期受到限制的盟国领导人做出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联合阵线决策的可能性更低。
上面的论述主要讨论了任期限制这一法律约束对于领导人理性考量在国外武力使用决策的影响,但上述研究讨论皆基于一个共同隐含的假设,即领导者对于武力使用的偏好是相同的。实际上,领导人对于武力使用的偏好各不相同,其对武力使用决策存在显著影响。按照武力使用的偏好,领导人可以大致分为态度较为强硬的鹰派与态度较为温和的鸽派,鹰派领导人在冲突中通常对另一方具有怀疑、敌意和侵略倾向,倾向于减少与另一方的合作和信任,而鸽派领导人则相反。以往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在国际冲突中鹰派领导人与鸽派领导人的冲突行为存在差异。
在衡量领导人武力使用的偏好时,以往的学者较多使用政府政治取向这一指标。具体而言,学者们认为民主国家的右翼政党政策更支持军事方面,如强调海外军事存在、重整军备及军事自卫等,其态度更为强硬,具有敌意与侵略倾向。而左翼政党政策更侧重非军事领域并且注重和平,如强调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与敌国进行谈判等,其态度相对温和,更为强调互信与合作。在应对国际冲突中,不同政治取向的冲突行为变化体现了其对武力使用偏好的差异。格伦·帕尔默等人的研究发现,右翼政府关于武力使用的国内成本较低,相比于面临武力使用国内成本较高的左翼政府而言更有可能卷入国家间军事冲突。菲利普·阿雷纳和格伦·帕尔默,以及乔·克莱尔在各自关于民主国家冲突行为的研究中也证实了在不同经济条件与不同的联合政府组成结构下,右翼政府更有可能使用武力发起冲突。
尽管通过政府政治取向衡量武力使用偏好较为方便,但由于以往学者对于政治取向与武力使用偏好间关系的研究主要基于欧洲议会政府的行为,这种研究存在研究对象较为狭窄的问题。近期关于武力使用偏好的研究转向于研究与领导人个人特质有关的信息来衡量其对武力使用的偏好,这种方法建立在领导人的背景与既往经历会影响他们在任职期间衡量武力使用作为政策选择可行性的假设。迈克尔·霍洛维茨和艾伦·斯塔姆发现,任职前曾服兵役但未参与过战斗的领导人,比起没有军事经历的领导人更有可能发起冲突。这种通过领导人既有经历衡量武力使用偏好的方法,将研究范围扩大到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并且能够更为集中的衡量领导人个人而非整个政府的武力使用偏好。
在迈克尔·霍洛维茨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杰夫·卡特和蒂莫西·诺德斯特伦提出用一系列军事经历指标衡量领导人的武力使用偏好。运用霍洛维茨对于领导人个人属性与冲突发起决策关系的实证结果,杰夫·卡特和蒂莫西·诺德斯特伦提出衡量在领导人经验层面鹰派倾向的七项指标,并通过七项指标的整理得出领导人经验层面的鹰派倾向得分。此外,他们还提出领导人理论层面鹰派倾向的三项指标,包括先前的军事服役经历、反叛运动参与以及军事教育经历,整理得出领导人理论层面的鹰派倾向得分。通过实证检验,他们发现无论是经验层面还是理论层面,鹰派倾向越高的领导人作出军事冲突发起决策的概率越高。
按照以上研究逻辑,具有鹰派倾向的领导人具有更强的武力使用偏好,更愿意实行好战的政策,因此,更有可能在面临美国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邀请时参与联合阵线组建。反之,具有鸽派倾向的领导人武力使用偏好较弱,因此,在面临美国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邀请时参与联合阵线组建的可能性较小。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第二个假设:
H2(领导人鹰派倾向假设):鹰派倾向更强的领导人更有可能做出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的决策。
三 研究变量、数据与模型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盟国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分析的单位为“盟国—美国领导的联合阵线”,因此,美国的盟国构成了联合阵线的潜在参与国名单。在此,笔者运用“战争相关指数”数据库(COW)中的“正式联盟数据集”,筛选出与美国签订正式防务协议的盟国名单,并将在一个联合阵线建立当年就已与美国联盟的国家假设为联合阵线的潜在参与国。考虑到盟国也有可能成为美国军事干涉的目标国(如1983年格林纳达军事干涉),美国针对的目标国应排除在联合阵线的潜在参与国名单之外。在本文中,美国领导的联合阵线被定义为:至少一国接受美国的要求部署武装力量到作战区域,但在军事行动中由美国提供的军事力量占主导,并且美国的军官作为多国部队的指挥官,或美国军事指挥官在行动中通过协调指挥友军行动步骤。根据上述定义,在二战后(1946—2004年间),共有8次军事干涉形成了满足上述条件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军事干涉联合阵线案例和盟国参与情况数据根据正式联盟数据集、多湖淳和玛丽娜·亨克的研究数据整理得出(见表1)。
为了检验上述假设,笔者在杰夫·卡特和蒂莫西·诺德斯特伦的研究模型和数据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进。首先,笔者改变了其原有的分析单位,原本的研究是按照“领导人—年份”进行观察,本文将其转换成“盟国—美国领导的联合阵线”分析单位,方便进行面板数据处理。其次,原有研究关于美洲领导人的任期限制数据缺漏较多,部分领导人的鹰派倾向数据存在缺漏,笔者尝试通过使用乔治城大学提供的“美洲政治数据库”中选举制度的数据对任期限制数据进行补充,并使用LEAD数据集对领导人的鹰派倾向数据进行补充,从而拓展并更新了原有数据集。
(一)变量测量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因变量为盟国参与美国领导的联合阵线,这是一个虚拟变量,若盟国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则编码为1,反之则编码为0。这里的联合阵线参与具体操作化定义为:盟国在美国政府的正式/半正式的要求下,向作战区域部署至少20名(一个排的规模)士兵,或提供了便利军事行动的后勤部队/海陆军事基地。上述的操作性定义要求参与行为必须具有军事性,排除了外交性参与(通过国际机制为军事干涉提供政治性支持)或经济性参与(为联合阵线的军事干涉提供资金支持)的参与方式。盟国的联合阵线参与情况数据来源于多湖淳和玛丽娜·亨克的研究数据。
本文涉及的核心自变量之一是任期限制,这是一个虚拟变量,若领导人在参与联合阵线当年到该届任期届满后被法律禁止担任下一届本国政治首脑职务,则编码为1,没有任期限制约束则编码为0。任期限制导致不能担任下届政治首脑职务的具体条件存在以下三种情况:(1)领导人在连任竞选中落败,但本届任期尚未结束;(2)领导人计划退休;(3)法律规定领导人在特定任期届满后不能继续执政。值得注意的是,本文定义的任期限制仅限于领导人本届任期届满时被法律规定失去担任政治首脑的职务,但并没有排除在特定国家选举制度之下,其在本届任期届满并间隔特定任期之后重新获得参选资格的情况。某些国家的选举制度规定,领导人在本届任期届满后受到任期限制,但在间隔特定数量任期之后可获得再次竞选总统的资格。此外,某些国家的宪法将领导人的任期限制为非连续任期(如葡萄牙、智利、秘鲁、乌拉圭等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领导人能够担任有限或是无限个任期,按照本文定义还是属于受到任期限制。任期限制的数据来源于杰夫·卡特和蒂莫西·诺德斯特伦的研究,并通过乔治城大学提供的“美洲政治数据库”中选举制度的数据对任期限制数据进行补充。
对于任期限制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笔者采用肖恩·齐格勒等人提出的“任期限制强度”变量作为任期限制变量的替代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各国的选举制度不同,对领导人任期限制与再次竞选的时间也存在差异。肖恩·齐格勒等人在研究中对强任期限制与弱任期限制进行区分并作出界定:当领导人在本届任期结束后永远都不能参与选举谋求连任,则定义为强任期限制;当领导人在本届任期结束后不能立即连选连任,但在间隔特定任期数量之后可以重新参选,则定义为弱任期限制。在这一界定基础上,肖恩·齐格勒等人构建任期限制强度变量,该变量为有序分类变量,若一国对领导人无任期限制则赋值为0,弱任期限制则赋值为1,强任期限制为2。本文采用肖恩·齐格勒研究的测量方法,通过对上述任期限制变量数据整理后得出任期限制强度变量数据。
本文另一核心自变量是鹰派倾向,用以衡量领导人对武力使用的个人偏好。以往研究中部分学者侧重使用政治取向衡量领导人的鹰派倾向,但这一测量方法建立在领导人组建的政府与其具有相似武力使用偏好的假设上,将领导人的偏好与政府全体成员的偏好等同起来。然而,政府精英内部往往涉及讨价还价的过程,政府政治取向往往是政府成员妥协的结果,并不能很好地代表决策者个人——领导人的武力使用偏好。因此,本文转而使用通过领导人个人特质与军事经历衡量领导人武力使用偏好的方法,并且采用杰夫·卡特和蒂莫西·诺德斯特伦提出的“经验层面的鹰派指数”作为自变量。除此之外,笔者还采用两人研究中提出“理论层面的鹰派指数”作为鹰派倾向变量的替代指标,对“经验层面的鹰派倾向”做稳健性检验。
领导人经验层面的鹰派倾向得分是根据杰夫·卡特和蒂莫西·诺德斯特伦提出的衡量领导人经验层面鹰派倾向的七项指标的满足数量汇总得出,即满足前五项对领导人冲突发起具有积极的显著性影响的其中一项或多项,则加同等数目的分数;满足后两项对领导人冲突发起具有消极的显著性影响的其中一项或多项,则减同等数目的分数。
根据以往军事经历对领导人冲突发起决策的影响,杰夫·卡特和蒂莫西·诺德斯特伦同时建立了理论层面的鹰派倾向三项指标。第一项为先前的军队服役经历,社会化理论认为军队服役经历使得军事人员受到来自军队的社会化规训,培养出比平民更加重视武力使用的观念,与平民相比更容易观察出特定事件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效力与紧迫性,并更倾向于将使用武力作为可选且更好的政策工具。第二项为领导人加入反政府军经历,以往研究认为参与过反政府武装叛乱的领导人对于军事行动带来的风险承受能力更高,以暴力夺取政权的信念使其更相信武力的效用。第三项为领导人接受军事教育的经历,军事学院的培养增强了领导人对军事手段的熟悉程度,使其更相信武力的效用;与此同时,大多数军事教育并没有为学生提供参与战争的机会,缺乏实战经历使得学生缺乏对战争风险和结果的充分认识,从而难以调节由军事社会化产生的好战心态。因此,在无法对战争进行更理性的收益分析和胜负预测之下,接受过军事教育的领导人更容易产生好战的心态,更为推崇武力使用作为可选的政策工具。理论层面鹰派倾向的构建基于上述三项指标的加总,即理论层面的领导人鹰派倾向得分等于领导人满足上述三项指标中一项或多项的数量。
在研究领导人任期限制与鹰派倾向对于领导人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决策关系时,不得不考虑其他变量的影响作用。因此,在讨论了关键的因果变量之后,笔者根据以往研究,提出了一部分可能对因果关系有影响的控制变量。
第一类控制变量为盟国与美国的关系。在以往研究中,斯蒂芬·根特提出,潜在参与国与干涉发起国对目标国的战略偏好差异影响参与联合干涉的概率。当双方针对目标国某些问题领域存在分歧时,表明双方战略偏好存在差异,此时选择联合干涉,双方可以利用以上战略偏好分歧对政策收益施加影响,从而满足自身涉及目标国的战略收益。因此,本文将盟国与美国的战略偏好分歧作为控制变量。本文关于战略偏好差异指标采用斯蒂芬·根特的测量方法,即以美国及其盟国相对于目标国家的相似性程度(similarity score)差异来衡量。相似性程度是柯蒂斯·西格诺里诺和杰弗里·里特通过比较两个国家之间的同盟组合差异来计算的,用以衡量国家在对外政策上的相似性。假设美国及其盟国对目标国具有不同程度的对外政策相似性,那么他们在针对目标国的军事干涉所涉及的问题上将会有不同的战略偏好。相似性得分可以通过ATOP数据库来获取。美国及其盟国的战略偏好差异计算公式为:
战略偏好差异=▏S盟国,目标国-S(美国,目标国)▏
除此之外,斯尔詹·武切蒂奇认为一致的身份认同对各国参与美国的军事联合阵线具有重要影响。以语言作为身份认同变量,斯尔詹·武切蒂奇研究发现,共同的主要语言——英语构筑了美国与其主要盟国的身份认同,对于其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有显著的积极性影响。因此,笔者将主要共同语言纳入控制变量之中。本文采用斯尔詹·武切蒂奇的测量方法,共同的语言指标定义为盟国的官方语言为英语,或该国70%以上人口的常用语言为英语,符合上述情况的国家则编码为1。各国常用语言数据来源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出版的《世界概况》。
第二类控制变量为盟国自身实力与地缘政治。自身实力主要指盟国参与军事干涉联合阵线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地缘政治主要衡量的是与目标国地理距离的远近给盟国带来的威胁。从军事实力层面,军事实力较强的盟国拥有更多的军事资源,能够在作战区域投放较大军事力量,更有能力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在多湖淳、大卫·莱克和斯尔詹·武切蒂奇关于联合阵线参与的研究中,实证结果均显示军事实力对国家是否参与联合阵线决策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因此,本文将军事实力纳入控制变量中。军事实力这一变量对联合阵线建立当年的军费开支进行测量。军费开支数据来源于“战争相关指数”数据库中的“国家物质能力数据集”。为减少方差增大带来的误差,笔者会对军费开支数据进行对数变换。
从经济实力层面,多湖淳提出国内经济状态影响政府为参与联合阵线筹备预算资金的难易程度。当经济高速增长,政府对财政收入增长持有乐观预期时,政府更愿意为参与联合阵线筹备资金;当经济形势严峻时,政府的工作重点是用财政刺激经济恢复增长,此时拨款给外派军队无疑是以经济振兴的资金与时间作为对外干涉的成本。因此,面临经济衰退形势时政府为参与联合阵线筹备资金的难度更大,筹措成功的概率更小。以前一年国内经济是否出现衰退为自变量,多湖淳的实证研究发现经济衰退对国家参与联合阵线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因此,本文对国内经济衰退这一变量进行控制。依照多湖淳的测量方法,本文运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衡量国内经济衰退情况,若联合阵线成立前一年潜在参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低于-2%,则该变量赋值为1,本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
从地缘政治层面,与干涉目标国地理距离较近的盟国面临着目标国对地区稳定性的威胁,其较近的地理距离使得盟国能迅速向作战区域投放军事力量,更有意愿与能力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在以往研究中,如多湖淳、大卫·莱克、斯尔詹·武切蒂奇、玛丽莲·亨克等人在各自的研究中都采用共同的区域(same region),即对潜在参与国与目标国是否处于同一区域进行测量,并发现其对联合阵线的参与决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笔者认为这一分类的测量方法体现不出地理毗邻程度的高低。因此,笔者转向运用“战争相关指数”数据库中的直接毗邻数据对盟国与目标国的地理距离进行测量,该数据集测量国家之间的毗邻程度,并根据陆上/海上毗邻距离远近将国家间毗邻距离分成五类进行编码。
第三类控制变量为盟国与干涉目标国的战略关系,不同于盟国与美国的密切关系能够使得参与干涉收益增加或成本减少,盟国参与对干涉目标国的军事干涉,会削弱盟国与目标国的关系,致使参与干涉遭受额外的损失。在本文中笔者主要研究盟国与干涉目标国是否存在联盟关系,联盟关系的数据来源于“战争相关指数”数据库中的“正式联盟数据集”,若盟国在联合阵线建立当年已经与干涉目标国联盟,则赋值为1。
第四类控制变量是背景性因素,主要指行动合法性与时代特征。军事干涉行动的合法性影响各国领导人是否参与军事干涉的决策考量,而联合国安理会对于军事干涉行动的授权是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此,学者们都将联合国安理会是否授权作为重要变量,联合阵线合法性这一变量采用的指标是事先是否获得安理会授权对干涉目标国使用武力。若联合阵线建立前安理会曾授权美国或其领导的多国部队使用武力,则编码为1。数据为笔者整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得出。从时代特征层面,冷战前后国际格局发生变化,冷战后美国建立起以自身为中心的联盟体系,盟国对美国的经济与安全依赖程度加深。因此,是否处于冷战时期对于是否追随美国参与军事干涉产生重要影响。冷战这一控制变量属于虚拟变量,本文以1991年作为分界线,若联合阵线形成时期在1991年之前则赋值为1,在1991年及之后则赋值为0。
(二)模型分析
本文的分析单位为“盟国—军事干涉联合阵线”,从时间和截面维度而言属于面板数据,且本文的因变量——“盟国是否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为二分类的虚拟变量,因此,本文的模型估计选择使用面板数据Logit分析法,所用分析软件为STATA 15.1。关于面板数据Logit方法,常用的估计方法包括固定效应估计、随机效应估计、混合回归效应估计。由于有较多的盟国从未参与过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22个国家,142个观测量),在使用固定效应估计模型时上述样本会被去掉,导致模型估计的样本全面性被削弱,因此本文预先排除固定效应模型。本文将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和混合回归模型对面板数据进行模型估计,并运用两个模型进行LR检验,比较两者的有效性。
在整理数据中,作者发现由于有新的联盟建立(如1999年波兰、匈牙利、捷克与美国结盟)或以前的联盟瓦解(如1984年美国宣布中止《太平洋安全保障条约》对新西兰的联盟义务),每一次军事联合阵线对应的分析对象——盟国的数量是动态变化的。为了更好地应用面板数据Logit分析,作者在数据整理时将1945—2004年期间曾经与美国结盟的国家都纳入其中,并增添“参与联合阵线期间是否为美国盟友”的虚拟变量,若符合条件则编码为1,保证数据为平衡的面板数据。在后续的Logit分析中,笔者将会分析当“参与联合阵线期间是否为美国盟友”的变量编码为1时的实证结果。按照上述假设,本文的面板数据Logit模型公式应为:
四 实证结果
下文中的表2与表4呈现了本文的实证结果,表2显示的是单个核心自变量对盟国做出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决策的实证结果,而表4显示的是综合两个核心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模型估计。在模型中,正值系数意味着该国更有可能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负值系数意味着更不可能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
表2的模型1和模型3分别为对任期限制和对经验层面鹰派倾向单个变量的随机效应Logit模型估计,模型2和模型4分别是对上述两个核心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为了观察随机效应模型和聚类混合回归模型估计效果,笔者对4个模型进行了LR检验。表3呈现了4个模型的LR检验结果,从P值一栏可发现模型1在0.1的水平上拒绝H0:ρ=0的原假设,模型2、3、4在0.01的水平上强烈拒绝原假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4个模型都应使用面板随机效应模型,而不宜进行聚类混合回归。
从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来看,模型2用任期限制强度变量对任期限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任期限制强度变量系数为负值且在0.05的水平上显著,与模型1中任期限制变量的系数一样均为负值,因此,任期限制变量通过稳健性检验。模型4用理论层面鹰派倾向对经验层面鹰派倾向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理论层面鹰派倾向变量虽然不显著,但是其与经验层面鹰派倾向变量系数一样都为负值,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通过了稳健性检验。
表2的模型呈现对任期限制单个变量的回归估计结果,任期限制的系数为负值且显著,而且对发生比率(odd ratio)的评估表明,若盟国领导人面临任期限制,那么盟国参与联合阵线的发生比减少82%,这表明任期受限的领导人更不可能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这与冲突转移假设相符合。相比于单边发起冲突,军事干涉联合阵线行动成本更低,综合军事实力更强,战争烈度较低,出于对竞选连任预期的理性考量,拥有再次竞选连任资格的盟国领导人预期通过海外军事合作成功证明自身执政能力,增加国内支持,因此更有可能选择参与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对于任期受限的盟国领导人而言,无须考虑往后政治生存使其失去在海外使用武力的激励,因此作出参与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决策的概率更低。此外,这也表明任期限制对领导人采取追随美国的态度与否产生影响。在美国对多边军事合作的号召下,拥有再次竞选连任资格的盟国领导人会在连任成功的预期下选择追随美国,以维持和美国的盟友关系。在预期顺利连任的情形下,没有任期限制的领导人会更倾向于选择追随美国而非相反,以避免因得罪美国而在下一届任期中招致美国在特定领域的打击。以往的研究也发现,美国对预期参与而实际上却没有派遣军队参与联合阵线的国家,通常会以不提供任何军事援助或减少军事援助的数量来施加惩罚。然而,在选举制度的约束下,任期受限的领导人由于其作为领导人的政治生涯中断,在任期届满前的最后阶段无须考虑其与美国未来的盟友关系应该如何发展,因此,其并不担心拒绝美国邀请带来的政治成本,而选择不参加军事干涉联合阵线的可能性更高。
模型3是鹰派倾向变量的检验,可以看出经验层面鹰派倾向变量系数为负值,且在0.1水平下显著,发生比率(odd ratio)结果表明若盟国领导人的鹰派倾向增加1个单位,那么盟国参与联合阵线的发生比减少44%,上述系数方向不支持假设2。可能的原因是,以往有关领导人武力使用偏好与冲突发起决策的研究中,学者们使用个人特质与军事经历建立鹰派倾向指数的方法只能衡量领导人总体的鹰派倾向,从而体现其对于武力使用的一般偏好。除此之外,以往学者们的研究对象——冲突发起也是一个比较广泛的研究对象,缺乏具体的冲突目标与相关因素考量。然而,领导人的鹰派倾向可能是有具体指向性的,其可能针对干涉目标国展现强硬态度,也有可能对美国的多边军事行动产生怀疑,从而对美国的军事行动展现强硬态度。因此,用缺乏目标指向性的总体鹰派倾向去测量可能有明确目标的鹰派领导人倾向并检验其与参与军事干涉联合阵线的关系,会面临一般理论应用于具体问题上的适用性问题,最终导致实证结果不能满足假设2。
表4呈现的是综合检验两个假设的logit模型,其中模型5是随机效应logit模型,模型6是混合回归logit模型。为检验两个模型的效用,我们对其采用LR检验。在对随机效应面板logit模型和混合回归面板logit模型进行比较时,表5的检验结果表示在01的水平上拒绝混合回归的原假设,认为存在个体影响效应,因此,随机效应面板logit模型比混合回归面板logit模型更有效。本文最终选择模型5的随机效应面板logit模型。
根据模型5,可以观察出任期限制变量的系数为负数且在0.01水平下显著。从发生比率结果评估来看当盟国领导人任期受限时,领导人做出参与美国领导的联合阵线决策的发生比下降84%。因此,笔者得出任期限制对盟国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决策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作用,这一结果支持冲突转移假设。然而,鹰派倾向变量的系数为负值且缺乏统计显著性,这说明模型5的实证结果与模型3一样不支持领导人鹰派倾向假设,可能的解释如前文所述。基于对核心自变量综合回归的实证结果分析,我们可以认为盟国领导人在是否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的决策过程中,其决策考量较多受到选举制度连任预期的理性约束,而非领导人总体的鹰派倾向。
对模型5控制变量的分析中,可以观察到与以往研究不一样的结果。首先,笔者关注盟国与美国关系层面的控制变量,这一类变量包括战略偏好差异与共同的主要语言。以往的研究结果发现,干涉领导国与潜在参与国对目标国的战略偏好差异越大,则潜在参与国做出参与联合干涉决策的可能性越高,其背后的逻辑是两国对干涉目标国的战略偏好差异越大,参与国为谋求自身偏好的利益会减少搭便车的行为,而对联合阵线采取实质性的军事参与,以求通过实质性的参与改变干涉的收益分配。从模型5中对干涉目标国的战略偏好差异变量回归结果来看,该变量的系数为正值但并没有呈现统计显著性,战略偏好差异每上升一个单位,盟国领导人做出联合阵线参与决策的发生比增加3.61倍。该实证结果的系数方向支持以往研究的结论,但是没有通过统计显著性的检验。这一结果可能的解释是,盟国在对参与联合阵线进行决策考量时,除了考虑本国参与对目标国的干涉后能获得来自目标国或目标国所在地区的战略利益多少之外,还会考虑参与联合阵线后领导国美国支付的利益多少。在联合阵线的组建过程中,美国为实现多边军事干涉,会通过与盟国达成利益支付承诺吸引其参与联合阵线。因此,即便盟国与美国在涉及目标国的战略偏好差异较小,但如果美国承诺支付的利益能够满足盟国的要求,盟国领导人基于利益考量及维持联盟关系,会倾向于参与美国领导的联合阵线。因此,该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受到影响。
其次,共同的主要语言变量系数为正值,从发生比率比评估来看当盟国与美国具有共同的语言身份认同时,领导人做出参与美国领导的联合阵线决策的发生比增加1.34倍,这一系数方向与本文的预期相一致,但是其显著性水平没有通过统计检验。可能的解释是,盟国在考虑是否追随美国参与多边军事干涉时,其考虑的是美国作为主导国能够带给他们的安全保障与经济利益,其参与联合阵线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对美国这一领导者的象征性认可,是确认美国的领导者权威及其行动正当性的举措。因此,在盟国做出参与联合阵线的决策时,其背后的身份认同会受到美国附属国身份认同的影响,而共同语言的身份认同受到挑战。
五 结论
本文从美国盟友选择性参与美国的多国联合军事干涉现象出发,研究盟国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的动因。以往关于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联合阵线的研究缺乏对盟国个体选择差异性的讨论,且集中于领导国—参与国二元关系层面动因的讨论,对参与国领导人的个人决策层面动因的研究较少。笔者在已有研究基础上提出领导人任期限制与鹰派倾向对于盟国领导人做出是否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决策有影响作用。
从理论机制来看,领导人任期限制对于领导人的海外武力使用决策的影响作用有两种不同方向的解释机制。从任期限制预期成本收益角度而言,失败的国际冲突会导致选民的反对从而提高国内观众成本,没有任期限制的领导人为了降低国内观众成本会对海外武力使用采取谨慎态度,而任期受限的领导人则对国内观众成本敏感性较低,相比之下会更倾向于参与国际冲突。从冲突转移理论而言,当国内问题对领导人的国内政治水平产生负面影响时,拥有连任竞选资格的领导人可以通过发起国际冲突的方式转移民众注意力,增强对现任领导人的政治支持及其连任竞选成功的概率,而任期受限的领导人无须考虑连任竞选,因此没有动力发起国外冲突。基于上述两种解释机制,笔者提出了任期预期假设与冲突转移假设,研究选举制度约束下领导人基于任期预期下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参与决策考量。领导人鹰派倾向影响其武力使用的偏好,从而影响领导人海外军事干涉参与与否的决策。因此,笔者提出领导人鹰派倾向假设,讨论武力使用偏好影响下领导人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参与决策考量。
基于以上假设,笔者对二战后美国领导的 8 次军事干涉联合阵线中56个盟国参与情况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任期限制因素对于盟国的联合阵线参与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即存在任期限制的领导人更不可能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这符合笔者提出的冲突转移假设。对于可以继续竞选连任的领导人而言,参与联合阵线不仅存在基于转移民众国内问题注意力、增强选民支持的激励,也基于连任预期下维持与美国的友好联盟关系,从而采取对美国的追随选择。对于任期受限的领导人而言,其无须考虑往后的政治生存问题,使其缺乏赢取选民支持、考虑未来与美国关系的激励,因此更有可能拒绝美国军事干涉联合阵线的邀请。实证结果显示盟国领导人的鹰派倾向对盟国的联合阵线参与存在负向的抑制作用,因此领导人鹰派倾向假设没有通过检验。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为以领导人的个人特质与军事经历衡量领导人总体的鹰派倾向,体现的是对于武力使用的一般偏好,并没有目标国家的指向性,因此,用领导人总体鹰派倾向变量去检验其与军事干涉联合阵线参与情况之间的关系,会有一定的适用性误差。对控制变量的实证结果来看,我们可以获得与以往研究不同的结论。以往研究注重考察领导国与参与国二元关系对于联合阵线参与动因的影响,认为联盟关系与共同语言影响国家参与美国领导的军事联合阵线的决策。但当笔者将研究主体限制为美国盟国时,实证研究发现盟国与美国对目标国的战略偏好差异变量缺乏统计显著性,而盟国与美国拥有共同语言这一变量仅在单个核心自变量回归模型中才达到统计显著水平,其解释力度有限。
综上,本文发现在盟国关于是否参加美国领导的军事干涉联合阵线的决策中,盟国—美国二元关系层面因素对盟国的联合阵线参与决策影响有限,更大程度上是盟国领导人个人因素在起作用。盟国领导人在联合阵线参与决策的过程中,其决策考量主要是基于制度约束下个人任期限制的理性考量,较少为其武力使用偏好所左右。本文打破了以往研究综合考虑各国参与美国领导的多国联合军事干涉动因得出的一些错误判断,以盟国选择性参与美国领导的多国联合军事干涉为切入点,研究盟国这一与美国具有特殊关系的群体是否参与美国领导的多国联合军事干涉的影响因素。本文的研究发现对于我们分析当前局势下各国是否可能选择参与军事干涉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 徐 睿)
(本文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4年第5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本文有删节,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