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苏州评弹的主要演出场所,书场内云集了来自不同社会阶层、性别的群体。这些群体的书场生活经文学创作和再现后,体现出“真实”与“虚构”并存的特点。虚构的男女说书形象,既可以是战争叙事下的时代隐喻,又可以是围绕身体书写的欲望体现。真实的书场生活帮助江南地区的儿童完成了初始社会化的过程,又让我们听到了社会底层群体的声音。
社群角色的多样书写:
民国以来苏州评弹书场生活经验的文学再现
作者简介: 周 巍(1981—),山东泰安人,常熟理工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江南社会文化史。
引文格式:周巍.社群角色的多样书写:民国以来苏州评弹书场生活经验的文学再现[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7,34(1):67-71.
基金项目: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YSC002);常熟理工学院重点学科资助(KYX201613)
书场是苏州评弹的主要演出场所[1]。书场里,艺人、听客、书场服务人员(包括场东和堂倌)围绕着苏州评弹在其间频繁交往和互动。这些交往和互动,可以称之为书场生活,是不同群体社会角色实现的主要途径,也是信息流通和情感交流的媒介,故有人形象地评价书场处处是“禅关”。
民国以来,书场生活既见诸当时的报端,又被作家以散文、小说等形式为读者建构了一个充满现代想象和时代隐喻的文学世界。在这个文学世界里,有截然不同的“说书人”形象,有经历社会化过程的儿童,有书场内外的堂倌和听客,可以说不同的阶层、性别、身份、角色均囊括其中,不失为当时社会及生活的诠释途径和有益补充。
一、时代隐喻与战争叙事
文学作品中有关战争的叙事,既有对战争整体性的观照,又有“去现实性”的个体体验和经历。以说书人为主角的文学作品,较偏重后者。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抗战成为主旋律的时代背景下,国人态度分化严重,并各自作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乱世中,书场成了很好的“避难所”。“台上艺人手舞足蹈,台下听客傻傻呆呆,听伊之信口开河,东拉西牵,明知是假,偏以作真。并随之忽悲忽喜,忽惊忽叹,及散则纷纷出场。翌日则又相偕齐来,就像到课堂上课一般,终日奔走,终日若此。”。
有此深厚的群众基础和影响,肩负着社会教化重任的说书人成为那个时期作家笔下寄托哀思之所在。另外,选择说书先生这个老百姓最熟悉的公众形象,既反映出说书艺人在战争期间的生活不易,更是民众真实生活的写照;既揭露平民大众在战争中的无奈,也在时时刻刻地提醒读者,正义的力量、希望的种子就存于每个人的心中。
芦焚、洪文蔚笔下的说书人是芸芸众生的代表,将战争的苦难与民众的悲哀展现尽致。芦焚笔下的说书人说着王侯将相、草莽英雄的故事,将听客带进想象的世界。“什么学者、什么大僚,全由他去!我甘心将这些名衔让给别人,在我自己的大名下面,我毫不踌躇的写上—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撒谎家!”[2]说书人让听者暂时忘却了战争的苦痛和无奈,但现实的苦难却让他自己举步维艰。“他的长衫变成了灰绿色;他咳嗽,并且唾血。间或他仍旧吼,但是比先前更衰弱,他的嗓子塌了,喑哑了。”[2]随着物价飞涨,听客给的钱已经无法支撑说书人日常的生活开支,“’再请八个,一个馒头的钱,还有六个,还剩四个,只剩三个了,哪位一动手就够了。’时常他将收到的钱数一下,他叹息日子艰难,让客人另外给他增加”[2]。
社会的变迁,让这位说书人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最重要也是最不幸的,乃是他时常发病,不能按时开书,有时候中间要停好几天。”[2]洪文蔚笔下的说书人,同样是战争影响下苦难众生的代表,瘦弱、忧虑、无奈、病痛、苦难:“说书人老了,花白的头发,皱皱的脸子……苦恼只剩得一付皮包底骨子。……说书人的咳声,也一次次地重了……在北风里,我又见到了苍老的说书人,听到了他重重骇人的咳声。”芦焚、洪文蔚笔下的说书人也许真有其人,创造了另一个“精神空间”,在战争时期,成为不少人的“精神鸦片”,在那个想象的空间里,有正义、有希望。
蓝戈笔下的说书人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化身,是愤世嫉俗者,面对世道不济、人心涣散,认为“众人皆醉我独醒”。他试图以拥有的知识和对社会的广泛影响力而有所作为,在战乱时显得格外突出。洪文蔚笔下的说书人阅人无数,看清了台下听客的浑噩:“他是一个落拓不羁的闲人,但也是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他在广漠的昏迷的人群里面欢歌、狂呼;他也在广漠的昏迷的人群里指点和哀诉。他高歌这人群之所以应当高歌者,他狂呼这人群之所以应当狂呼者,他指点这人群应走的大道;他也哀诉这人群之使人悲戚者,他更有他的那块永远随着他的长方醒木,当头痛击一班昏迷不醒的人们。……最后他终于力竭地倒下了,然而却没有一个曾经听过看过他的人们为他惋惜,因为他们仍然是那么地昏迷不醒呀!”
范烟桥
前三篇小说的说书人均为男性,而到了范烟桥的小说《无花果》[3]中则变成了女性。这一女说书形象的出现明显受到战争时期知识精英借“妇女问题”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影响。范烟桥没有把这位女说书视作寻常欢场女子,而是通过创作《无花果》以提高女说书的爱国品格,让其在国难当头之际于“爱情”与“爱国”之间作出取舍,最后个人情爱让位于救亡爱国的宏大叙事。
二、身体书写与欲望想象
罗兰·巴特从阅读的角度将身体提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在他那里,文本字里行间埋藏的不是“意义”,而是“快感”,阅读不再是人和人之间的“精神”交流,而是身体和身体之间的色情游戏。[4]抗战胜利后,文学作品描写中的说书先生,由男易女,略去职业生活不讲,将“私生活”无限放大。这类小说通过男性视角观察女人与周遭社会之间的性别关系,进而形成和建构起男性作家的自我世界和主体意识。于是,风光无限的女说书先生以其时髦的身体、享乐主义的行为方式成为文人笔下的欲望符号。
克拨登在连载小说《书场孝子》中,描写了一位涉世未深的女说书张凤君,最后她的心理与身体的防线都被攻破,揭露出女说书从艺生涯风光背后的艰难与不堪。每一期的标题都非常醒目:“小娘皮小娘皮要喜快啦”“你是不是处女?”“摸一摸怕啥难为情”。
整部小说发生的背景主要在舞厅中。舞厅是都市男女交往的重要空间之一,“引发了新一轮的男女交际模式的变化”[5];舞厅是“既表征摩登、文明,又生产种种败德、腐烂气息的矛盾场所,十分适于进入各种语境中完成不同的都市想象”,而且“舞厅男女相拥嬉玩的场面被理所当然地征用为上海的代表景观”[6]。《书场孝子》中的舞厅,似乎也正体现了这种在充满“败德、腐烂气息”场所中的男女交际模式,张凤君扭动的身体勾起了男性的窥视欲望。
小说《春老虎》则把女说书的物质交易和性爱叙事发挥到了极致,她们的身体已经成了另类“商品”。小说的标题带有很强的“情色”意味,如“发现了女说书的秘密”“看病变了捉奸”“你们怎样发生了关系?”“上海的女人都骚”。小说中出现较多的词是“发现”,似乎刻意强调女说书在“书台”上下的形象差异:“大家都说梅玲君怎样规矩,男人想不到她的身体,今天却被我捉住了秘密,原来她与秦小开有这么一手,不知他化了多少金条,才接受了他的肉条?”
这部小说,极力表现了女说书的物欲和情欲的本能冲动。她们在传统的道德规范面前,似乎变成了脱缰的野马、城市中美丽妖娆的“交际花”,游走于“醉翁之意不在酒”的男听客中。女说书虽然看似体现了自我能动性,但充其量是男性作家想象的产物。她们靠色相换来的物质享受,是建筑在依附男性听客的基础之上的。正如高彦颐所说:“女性从家庭生活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取自由最大时,也正是其依靠公众领地的男性程度最高时。”[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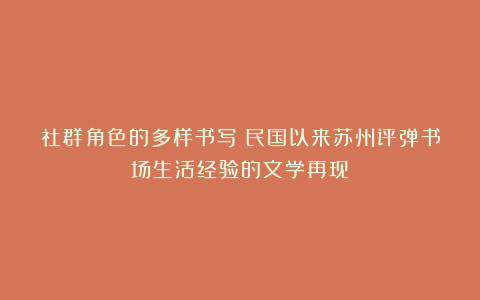
除此以外,还有些小说把地点放在书场、堂会中,她们虽然不再是风月情事的主角,但说书家的职业身份依然难以逃脱“色与艺”的品评。“色”是身体特征的直接反映。柳郎的小说《书坛风月》,共三回,事件发生在书场,事件的主角换成了书场场东、书场堂倌、男女听客。他们品评着女说书的“色与艺”,年轻听客小赵把女说书当成了“性幻想”对象,“一本正经的心里漂浮着一种忆测,是美丽的一种幻想……那娇小的影子,那剪水的眼波,丰腴的曲线,和那活泼温静的举止,恐怕是任何年青人要被陶醉的”。
上述几篇小说,既为我们提供了建构都市欲望想象的评弹语境,也让我们深切体验到身体书写背后“性”主题的无所不在。正如波德里亚所说:“性欲是消费社会的’头等大事’……一切给人看和人听的东西,都公然被谱上性的颤音,一切给人消费的东西都染上了性暴露癖。”[8]
女说书的形象与身体、欲望相联系,在抗战胜利之时,作家通过对人类最基本的感情—男女之情—的描绘唤起读者对生活的信心。不过,小说反映的男女之间的亲密关系很难说是上海普通市民的行为规范,但一定程度上象征着时人对性别、情爱、金钱等的关注程度和基本态度。
三、童年忆往与初始社会化
社会化,是指个人成为社会主体的认知和行为的过程,可以通过象征性地奖励和惩罚各种不同的行为,教导业已建构起来的规范和价值,所以社会化是一种学习过程,学习与某种特定社会角色或社会身份相契合的过程。[9]社会化过程的目的,在于学习特定的文化模式,进而维持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从幼年期到少年期,人类学习文化意义与社会技能,也与他人和社会总体建立起终生的社会和情感联系。
评弹书场或许是苏州乃至江南人儿时踏入的第一个社会场所,书场特殊的环境氛围,对孩子们成长时期的行为与思考方式产生了影响。孩子们在书场里,开始了与社会最初的互动。民国以来,作家主要通过散文等形式较为真实地回忆和再现了儿时的生活体验与人际互动,其间并没有民族政治的宏大叙事与诉求。
在作家笔下,苏州评弹书场是“儿时的乐园”,这是对书场空间和生活的另一种诠释和再现。所谓“儿时的乐园”,首要的在于评弹书场里有足以吸引儿童的食物—小吃零食。孩子无法集中精神与大人们一样认真听书,吵闹着要买零食,而大人们为了让他们安静,也尽量地满足。这些小吃,成为孩子们对书场最深刻的记忆。
作家吴人犹记得卖小吃的老太太在书场里经营花生、南瓜子、西瓜子、葵花子的情景,计量器是一只极小的浅口酒盅,“她用酒盅舀了两盅花生米放在前排长椅子的木条上”。另外,孩子们还被其他有趣的东西所吸引,比如水烟筒、大铜壶,对台上的说唱却不感兴趣。
经历了最初的不合作与注意力分散以后,孩子们便开始关注书场中艺人的表演。听书还成为了“儿童时代的娱乐”。书台上艺人说着各种有趣的故事,既有让人敬佩的英雄事迹,也有让人捧腹的滑稽人物,还有纠缠不清的富家千金与穷书生之间的故事。慢慢地,他们从艺人的表演中,获得了各种人生经验,接受了真善美的社会教育,也开始幻想朦胧的男女之情。
包天笑小时候经常跟着长辈们出入书场:“《描金凤》、《珍珠塔》、《玉蜻蜓》、《白蛇传》、《三笑姻缘》之类。这些大书小书,我都听过,但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儿童,都是喜欢大书,不喜欢小书。因为大书是描写英雄气概,小书只是扭扭捏捏,一味女人腔调而已。”[10]
包天笑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孩童都有足够的资财支付听书的费用。为了能在书场内觅得地方,亲耳聆听说书先生的现场表演,大人们站着“听戤壁书”,小孩们则想出了“凑钱派代表”“听隔窗书”的办法。儿童文学作家金曾豪小时候就是靠着这个办法进书场听书的:“每个人凑点钱,供一个人去听书,次日找个时间让他向大伙传达。派出的代表是我们中最能模仿说书人的,他受此重托,竭力地绘声绘色,却远远没有原版的生动迷人。……听隔窗书不是全天候的,天凉,书场的窗子关起来,隔窗书就听不成了。天热,窗子开着,可水上的蚊子多,得不停地和它们战斗。听隔窗书是难于过瘾的。总是有了阻隔,声音渺远飘忽;更重要的是看不见说书人,使评弹的魅力大为逊色。”[11]
1949年以后,许多人还都有着和包天笑、吴人那样从小被长辈们带到书场去听书的经历。这个阶段,不仅让孩子们培养起了对评弹的兴趣,同时也是他们向大人学习某种社会角色或社会身份的过程。社会化是模塑人的过程,在其中,未掌握社会资源的儿童在很大程度上处于被动习得的状态;成人社会的生活框架、价值观念、理想追求等,对儿童来说,都显示出外在的强制性,总之,这是一个以成人为本位的社会;儿童在既定的社会里过着异化的生活。[12]
苏州的书场里,孩子们的初始社会化也是一种被动习得的状态,但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为孩子们以后获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提供了很好的前期准备。苏州书场的环境氛围,不断规范着从小听书的孩子们的日常行为,影响着他们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孩子们从最先被动接受书场逐渐转变为主动接纳书场,在娱乐中接受社会教育,接受文化熏陶,传承数百年来的生活方式。
四、结语
民国以来,作家围绕书场生活的体验创作了以说书先生为“客体”的文学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形构了男说书先生与女说书先生两种迥异的形象,受到西方对于男性与女性气质差异理论的影响。
这种影响主导了后来对于传统社会及近代社会中女性地位与作用的看法,在文学、艺术、电影等领域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成为中国传统男性话语霸权的一种很好的理论依据。西方认识论认为,条理化和理性的认知者是男性,而女性则是由感觉和情感所控制的。男性的形象成了理智、正义的化身,女性的形象则与身体、欲望相联系。而以童年书场生活为主要内容的散文,则体现了作者的“主体”身份属性和地域文化认同。
参考文献
[1] 吴琛瑜.书台上下:晚清以来苏州评弹书场与苏州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 芦焚.说书人[J].万象,1943(3):18-21.
[3] 范烟桥.论女弹词[J].金星特刊,1941(4):57-59.
[4] 汪民安,陈永国.后身体:文化、权力和生命政治学[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3.
[5] 马钊.诱拐的命运:20世纪40年代北京的男女交际、传统礼教和法律原则[M]//杨念群.感觉·图像·叙事.北京:中华书局,2007:300.
[6] 陈文婷.上海舞女:以休闲报刊与小说为中心(1927—1949)[D].台北:台湾大学,2002.
[7] 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M]. 李志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28.
[8] 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刚,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8.
[9] VAN ZOONEN L.女性主义媒介研究[M]. 曹晋,曹茂,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46-47.
[10]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55-56.
[11] 金曾豪.听书杂忆[J].少年文艺,2002(4):44-45.
[12] 小田.江南场景:社会史的跨学科对话[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310.
图源/网络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公众号
2018.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