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少民 站在今天做明天的艺术
文|刘云西子
图片提供 | 坪山美术馆、美成空间、沈少民
版式设计 | 乐天
图文未经《Hi艺术》授权,不得擅自使用
他是艺术家,是诗人,是科技进步的怀疑论者。
沈少民的作品和他的诗歌一样,朴素而凝练的形态却充满诗性的抒情,简化而直接的结构却承载反思的力量。
诗歌和艺术对于沈少民而言就如水之于鱼般重要的存在,诗歌可以是方案,不存在边界,也没有藩篱。他用文字的方式抵达思想的最深处,用残酷却真挚的作品直面现实的深渊。他在科技进步带来的乐观主义中秉持悲观主义的远见,坚定而坦诚地发出对既有经验的质疑,在无畏而炙热的对抗中呐喊。
艺术家 沈少民
以诗意的尺度质疑今天
这位60年代出生的艺术家,似乎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内在动力。他拥有如科学家一般锐利的眼光,捕捉一切潜在的可能。在可能的间隙外,探索科技领域最隐秘的角落,用艺术的方式寻找与科技的对话。
在《我是我自己的结果》中,两把装有驱动电机的巨型卷尺以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彼此丈量各自的尺度。放大了的标尺失去了原本作为“尺”的度量功能,用标准的象征物测量标准,真正标准的定义到底在哪里?它不禁发出疑问,标准是否还存在?科技呈现的景观并不全然是真实,假象也无处不在。
你用
自己的长度
制定
别人的标准
——沈少民《尺》
它们是沈少民近几年多领域跨媒介创作的聚焦,是他思辨性的实验,也是他自2000年起对艺术与科学关系探索结果的延续。他独树一帜的跨学科视野在语法的持续变革中,以幽默却也严肃的质疑和浪漫主义的诗性,书写了他个人的科学简史。就像戏剧性的荒诞中夹杂着无奈和讽刺,科技带来的结果似乎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
诗歌和艺术的支点架构起了“沈少民的科学简史”。关于想象力和无用的思考得以链接,二者的辩驳和反思,成为彼此的他者和标尺。沈少民曾说过,他不是专业的诗人,他的诗,只是一种隐藏在文字之中的装置方案。但是在他这里,科学与技术的故事被拟人化,诗歌用浪漫而抒情的方式勾勒出了人类明日的许诺,艺术中的怀疑主义调侃并质疑科技进步的乐观主义。那些科学史中被抛弃的试错实验也以他抽象的想象力审视着艺术的实验性和创造力。
你烤热了城市的客厅
凉爽了你自己的睡房
——沈少民《空调》
《空调》300×300×230cm 空调蒸发器、空调冷凝器、金属框架、建筑板材、钢化玻璃、门、灯 2022
《竞技场》710×326×40cm 四足机器人、金属框架、建筑板材、羽毛 2022
不被定义的艺术家
我盯着 盘子里的死鱼看
看着 看着 就看成了活鱼
我再盯着 盘子里的活鱼看
看着 看着 就成了大海
我再盯着大海看
看着 看着 就看成了 一望无际的盐滩
——沈少民《一条鱼》
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
我
用一生的时间
都在
找寻自己
——沈少民《我&自己》
《磕头机》抽油机改装制作 室外装置 美国芝加哥千禧公园 2007
对人类生存现状的关注曾在《盆景》(2006年)的“活体装置”中初露端倪。它是对自由的控制无处遁形,无形的暴力和被控制的强权的讽刺,它像被戴上了沉重的镣铐,以更加赤裸的方式引入一种潜藏着的暴力。放大植物改造的过程也定格了盆景制作的每一步,绳子与铁丝被迫扭曲交叠的缠绕最终指向消亡。产业化的制作工具犹如手术器具般冰冷得让人不寒而栗。它们锋利而直白地指涉被扭曲的自然、现实的我们无法逃脱无处不在的强权控制和暴力模式。只有“反思”是我们能够用以抵抗的自由权利。
沈少民往往从自身周围的问题开始关注,为了避免自己沦落为被颠覆的对象,他拒绝空洞的批判。他的视角往往从悲悯情怀出发,以真实为手段,营造出绝望而残酷的现场。在当代艺术的创作中不断寻求自我突破和实验,也许就像他30年前说的,只有“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才能时刻站在当代艺术的最前沿。
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
沈少民的创作,自始至终都在发掘科技的现代性和工业化变革背后隐藏的语境。它是先进的、革新的,却也是扭曲的、暴力的。它们诉说科技革新的现在,却不关心充满未知的将来。所有对现实本质的揭示和创作,都不是艺术家凭空想象出来的,它们汇聚了沈少民的个体经验。他试图以艺术家的身份和艺术家的方式寻求一个感性的结果。这个结果,没有规定的形态,可以是诗,可以是画,也可以是承载他观念的影像。
我把一条直线
走成了一个圆
——沈少民《生命》
《生命的长度》30×30cm×16 布面丙烯 2022
在《我摸到了上帝的声音》中,沈少民将《圣经启示录》的经文以盲文的形式镶嵌在发射太空船的火箭残骸上。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解的符号,在盲人的触摸中却能够阅读这些太空降下来的信息,它们承载着关于世界末日的内容。正如艺术家说过:“面对宇宙的无限,人类本质上如同瞎眼。”人们总是想以征服一切的野心摸索潜藏在宇宙背后的真相,但人本身的渺小却无法左右任何事情。对于这样的悲观态度,他说过:“正因为在思考,所以才悲观。”
沈少民清醒而思辨,他不为科技进步而赞颂革新带来的一切便利;他的艺术先锋而前瞻,他知道思考未来才能更好地面对现在。明确且强烈的隐喻,占据沈少民创作中的重要位置。它是对这个世界思考的深化与延展,也是对科技的悲观远见和审视。“站在今天去做明天的艺术”,是他最响亮的口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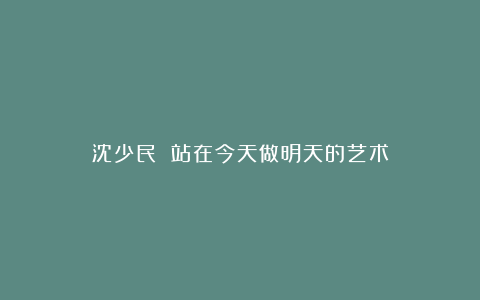
艺术家 沈少民
在我这没有差异,也没有界限
Hi艺术(以下简写为Hi):展览主题为“沈少民的科学简史”,为什么会取一个这么宏大的标题?想要引发怎样的讨论或反思?
▼
沈少民(以下简写为沈):这个题目并不宏大,实际它带有点讽刺。策展人定这样一个题目,是因为我大多数作品都跟这个有关,而且我很早就介入科学之中,策展人也知道我很早就有一个方案叫“科学的接力”,这应该是我十几年以前的一个方案。
我的方案就是选取了各个领域中我比较感兴趣的几位科学家,比如理论物理领域,还有人工智能、生物学领域,把他们放弃的项目接过来做。我这么做的原因并不是说要给它一个科学的结果,而是我用艺术家的方式给它一个非常感性的结果,最后这个结果可能是一首诗,可能是一幅画,可能是一个影像,也可能是一句话或者一个汉字这样的方案。后来策展人觉得我还有很多没有完成的,包括十年以前的一个方案,与这次展览的一些方案一起。他觉得很像一个简史,就写上了这个名字,实际上跟“史”没什么关系。
▼
沈:我一直很关注科技艺术,因为这个词也很时髦。最近几年有很多策展人做了一些科技艺术的展览,当然也有很好的一些展览,但是其中大部分展览我觉得都是炫技,可以说都是利用现在比较先进一点的技术,甚至有些都不能称为作品。因为这里边没有任何思考,只是一个技术的呈现,我是非常反对这个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实验室叫“科学+艺术”,而不是“科技+艺术”。
Hi:展览围绕艺术、诗歌和科学三个领域展开,聚焦于这三者,你是怎么看待这三者之间的差异性?
▼
沈:在我这没有什么差异,也没有什么界限,因为有些作品是从我的诗歌里边想到之后这么做的,有的是先有这个方案,后有诗歌,所以它们是这种关系,并不是说什么诗配画或什么画配诗等等,不是这种概念。它们都是在一个线索里边,诗歌跟作品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用自己画自己》100×7×220cm×3 纸本素描 2022
Hi:科学发明和科技进步是不断进行实验和纠错的过程,艺术的实验性在你看来与科学实验的过程有相似之处吗?
▼
沈:首先,二者的工作方法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呈现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艺术家不是说生产一个东西它就是艺术,它不是生成具体的一个东西的概念。所以我们做一个作品,比方说这个作品跟科技有关,实际上并不是说我做一个用科技技术做一件作品,而是我把科学家在试错纠错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失败的产品也好、作品也好,拿到展览中,让大家对科技和对未来有一个反思和关注。
我这次的展览你们从作品上也能看到,我是对科学和科技的一个重新思考。有的是带有质疑的,并不是说我们用一个什么先进的技术去做一件作品,就是借用一种先进技术,我觉得科学艺术家一定是走在科技前面的人,而不是跟着技术跑。
“沈少民的科学简史” 展览现场 坪山美术馆 深圳 2022
Hi:作为50、60年代出生、最早一批将科技与艺术结合实验的艺术家之一,可以谈一谈对当下年轻人或者新一代艺术家以及他们玩儿科技的看法吗?
▼
沈:不同时代的人可能对这个话题有不同的思考,比方说我也接触过很多国外留学回来的一些年轻艺术家,有的学算法,有的学交互艺术,他们在受教育也就是学艺术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是用一些科技手段去做艺术了。
有些艺术家,在他接触艺术的时候或者学艺术的时候,已经带有这种基因。而不是说我们有一个新的技术,我拿来就做一个很炫酷的东西,这是两回事。像我这个年龄的艺术家,我们可能都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我们更多地去思考和质疑。我觉得艺术家就要质疑一切,而不是说去跟着技术去跑。我这次展览的一些作品并没有什么高科技,都是很简单的。比方说空调,空调是在大家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家用电器,但是追溯到当年它刚出世的时候,你能说它不是一种科技吗?
我通过一个最简单、但也已经是很早期的科技产品,让大家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误解为说沈少民也挺时髦,怎么说这也是科技加艺术对吧?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的。
《被催眠的艺术家》6’54” 黑白影像 2017
Hi:你是如何看待外界称你为“跨界艺术家”?你的创作形式涵盖了绘画、装置、灯光、行为等等,在多种语言的表达中,有特别关注某一种形式吗?
▼
沈:我特别反对跨界这个词,因为别人我不敢说,起码我从来也不跨界,因为在我这就没有界限。而且我也不是学艺术出身,我没学过艺术,所以说在这我里也没有任何界限,我也不在艺术史这个系统里边去想作品去做作品,所以也可以说跟跨界是毫无关系的。
别人给我这样一个定义,当然我也不介意,但是这个词真的跟我没关系。我觉得《竞技场》这个作品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我用了一种以毒攻毒的方法对机器人产生一种质疑,未来如果有一天我们人类被机器人控制了以后,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如果把机器人的整个发展路径呈现在现场,那么我们也是一个很残酷的人。倘若这个机器人就是未来的我们,那么未来可能人类的结局就是这样的。
Hi:你曾提到反对艺术的过度商品化以及符号化,那你有刻意避免艺术商品化的走向吗?怎样避免这种走向?
▼
沈:比方说我早期的“骨头系列”作品,当时也是卖得非常好,但卖得最好的时候我就停止了。栗宪庭当时给我做过一个采访,还问过我这件事情,他说为什么这批作品卖这么好的时候却不再做了。我说正因为卖得太好,我就结束了这批作品。因为这样很容易成为商品,你不断地在复制自己的时候,我觉得会把自己带入到另外一个商业系统,我不想在任何一个系统里边去做我的艺术,去进入那种工作状态,这些不是我想要的。
《实验田2号 白菜》40x50cm 2004
痛苦产生诗人,痛苦也产生艺术家
Hi:你是怎么看待诗歌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关系?写诗的过程对你现阶段创作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
沈:我觉得诗歌本身不是说跟当代艺术有什么关系,诗歌本身就应该很当代。因为它的语言、它的语法更简单,我觉得诗歌应该当代。当然我觉得诗歌也有不同,有传统诗歌也有当代诗歌。
你可以用写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或者可以用一个装置,也可以用绘画,只是语法不同而已。但是每个艺术家的工作习惯不一样,比方说我写诗歌,以前我也没写过诗歌,前几年我才开始写诗歌,我有一段时间没做什么作品,因为我对当代艺术比较失望。我经常在网上看一些东西,我觉得那些比很多艺术家都有想象力。
Hi:你是怎样在诗歌与艺术创作的语境中自如转换的?诗歌写作的过程会给你的艺术创作带来灵感吗?
▼
沈:我不太喜欢用灵感这个词,我不是靠灵感做作品的,我是靠思考来做作品。当然可能会有社会上发生的某件事情,或者你的个人经历会触发你让你去思考一件事情。但我觉得这不是灵感,是你的生活本身或者你身处的环境,还有社会的变化对你的一种影响,然后找到一个合适的语法去表达你想要说的话,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的作品都不是一个很私密的那种情感的表达,它都是带有关注性的,我觉得跟社会学可能关系更大一些。
《我是我自己的结果》2016
Hi:你热衷于关注人类生命问题以及生存空间的问题,你的作品(包括诗歌)中也显露出一些悲观主义情绪,这种现实世界的悲观与情绪上的悲观是怎样以积极的方式推动艺术创作构思?
▼
沈:有句话说,痛苦产生诗人,我觉得痛苦也产生艺术家,因为痛苦会让你思考更深刻的东西。
我们今天所处的这种大的环境也好,这个时代也好,疫情连续三年,我觉得环境影响对一个艺术家很重要。我们这次也做了一个作品叫《我是我自己的结果》,它像迷宫一样,你通过这个通道,进入一个空间后再打开一扇门,当你走完所有的门,会走到一个空间,那里的镜子反射的是你,同时也会出现一首诗歌。因为你在进去之前要会接受一个扫描,里面的你在跟现实的你摆摆手。自己跟自己告别,其实也是一个很伤感的作品。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或者是这样一个时期,我觉得没有人不伤感,悲观是一个非常准确的给这个时代的符号。我自称为自己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光悲观也不行,你还得用一种积极的态度去对待。
Hi:你有做很多公共艺术的项目,那么在你看来,公共艺术项目在公众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对于社会大众有着怎样的影响力?
▼
沈:实际上在我这没有公共艺术、当代艺术之分。我们对公共艺术的理解,也是有很大偏差。比方说我们在一座广场上放一个雕塑,就理所当然认为这是公共艺术,我觉得这是不对的。今天的公共艺术,应该跟这个城市跟环境跟空间乃至跟建筑发生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跟观众的互动关系,对公众没有任何影响,就不能称之为公共艺术。
《我睡在自己身上》硅胶、工业盐、机械呼吸系统、皮毛、木质底座 2017
Hi:公共艺术的表现形式有很多,你觉得通过哪一种方式可以更好地激起公众参与度?公共艺术最打动人的地方在哪里?对你而言,公共艺术有特定的界限吗?
▼
沈:我觉得公共艺术不像之前我们对大多数人对公共艺术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一个广场,或者在一个空间里放一个雕塑,大家就称之为公共艺术。我觉得未来的公共艺术不应该是这个样子,更多的是跟人的互动,这种互动也包括情感上的互动。比方说我现在要实施的方案,那么我自己认为它就是一个公共艺术,我要找一个戒毒所跟这帮戒毒的人共同去创作,根据大家的兴趣,教他们画画也好、摄影也好。根据大家的兴趣,然后把整个过程拍一个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可能是我最后的作品,也许最后这些人可能通过画布找到出口,找到另外一种精神通道。
Hi:在2016年《这里没有问题》的展览访谈中,你有提到说:大多数艺术家都面临着在前人画好的圈里面思考作品和创作作品,你说自己也一直试图在找到一种方法。那么现在的你找到了吗?
▼
沈:我现在的方法就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方法,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觉得做一个作品,你可能选择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你会选择不同的语法。所以说方法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我不想用一个固定的方法或者是形成一种方法去做所有的作品,我觉得我的每件作品都是不一样的。
《永远有多远》硅胶、机械呼吸系统 真人大小 2012
Hi:在2012前后的作品中,动物、植物都是处在痛苦活着的状态,2016年的展览也有与生命有关的、视觉上给人以压抑情绪的作品,例如《永远有多远》中干瘪的、似乎处在弥留之际的老妇人。你为什么会这么关注生命的这些层面而非阳光积极的一面?
▼
沈:因为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当然也是一个积极的悲观主义者。你悲观你也不能什么都不做,那么就是你把想到的、看到的和你想表达的东西通过你的作品,让更多的人能看到。
当然我不是说想让每个人都跟我一样悲观,但起码这种情绪它也是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我觉得活在当下,如果一点悲观的情绪都没有,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很正常的人。
Hi:上个世纪的当代艺术领域,自博伊斯宣称“人人都是艺术家”之后,艺术与生活的固有边界似乎被打破了。在今天自媒体横行的时代,你认为当代艺术和生活的固有边界是否还存在?
▼
沈:我觉得这个边界会越来越模糊。我觉得我都怀疑说艺术家是一个职业也好,还是一个称呼也好,也会越来越模糊,很多网友他们做的东西也很智慧,也很聪明,这对艺术家来说也是一个考验。
“尺度:沈少民个展” 展览现场 美成空间 深圳 2022
《被算计的云》110×162cm 布面丙烯 2022
Hi:你认为当代艺术通过大大小小的网络平台实现了民主吗?虽然似乎人人都可以成为当代艺术的一份力量,但是他们所拥有的话语权有多少?
▼
沈:话语权我觉得一直都还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说艺术家没有绝对的自由。也不是说你能彻底地脱离这个圈子,所以我尽量与这个圈子保持一定距离,但我也觉得已经很难了。
Hi:你正如你多年前曾说过“艺术就是真诚,是态度”,在你现在看来“艺术”是什么?
▼
沈:真诚就是我做作品的一个态度,这是我一直坚持的,你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做一件作品,实际上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
《海的纪念碑》深港城市双城建筑双年展 溪涌展场 2019
Hi:90年代初你曾旅居澳洲,那里的生活环境与文化氛围和国内相比,带给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
沈:澳洲对我的影响,在于它让我打开了眼界,看到了一种我能感受到的自由气息,但是我感受最深的是那种无聊,它是一个非常有序的东西。澳洲我觉得它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高福利和待遇,大家都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去生活去工作,这反而让我无所适从。
我在澳洲并没有创造出什么太多的作品,我更多的是做了一些方案,但是当我把这些方案做出来以后,我发现在这儿并不能实现,所以我又选择了回国。我觉得自由都是相对的,在那里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又什么都不可以做、又什么都做不到。
《尺度19》111×84cm 综合材料 2022
《尺度21》90×90cm 综合材料 2022
Hi:你是如何看待全球疫情持续蔓延和笼罩下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当下你的思考方式或创作又受到了怎样的影响?
▼
沈:实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像我的作品《盆景》一样,都是被控制的自然的一份子。你可能随时黄码,或可能弹窗,也可能去不了你想去的地方,甚至都出不了门,这都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对于疫情我觉得谁都说了不算,只有病毒说了算。
对此我没有那么乐观,我也无能为力,我能做的就是把这种情绪和感受当做创作材料,通过作品传达。我不是那种喜欢关注一个事件然后再去做作品的艺术家,但是它一定会对我有深远的影响。我不会把一个非常容易识别的、跟疫情相关的符号做成作品,但是疫情本身对我的影响一定是深刻的,也是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