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柏拉图从《荷马史诗》中汲取营养并获取批判性的力量、亚里士多德从中获取《尼各马可伦理学》借以讨论美德的质料一样,尼采也从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的对比中看到了真理与生命的关系。
现代科学给了我们“一种毫无根据的理性乐观主义”,即相信能够获得全部的真理,真理将给人们带来彻底的自由。那些炫目的乌托邦、反乌托邦电影的前半部分往往给我们这种幻觉,直到谎言出现。对假象的偏好构成了生活最本质的内容,科幻小说和侦探小说是最好的体现形式,它们的重心从来不是无所不能的科技或心思缜密的凶手,而是背后超越时空的人性。
尼采需要回答:如何既不放弃科学的原则,也不欣然接受某种新谎言?他寻找到的线索就在奥德修斯身上。
柏拉图在《希琵阿斯后篇》探讨了奥德修斯式人物的问题。问题与另一个人有关:在荷马笔下,谁是最好的人?最好的人是那位按真理行事的正直朴实的阿喀琉斯,还是那位按谎言行事的狡诈多谋的奥德修斯?
“智术师希琵阿斯为荷马的道德解释作辩护,竭力证明阿喀琉斯是最好的人:因为他坚持’一个人必须大胆地说话,不顾一切后果’。阿喀琉斯认为’心里一套,嘴上一套’的人最可恨,而希琵阿斯也觉得这种人很可恨。二者都认为或者希望:真与好相互联系,好会成为真的助手。但苏格拉底却证明,荷马笔下最好的男人是奥德修斯,因为他鬼点子多多。奥德修斯自觉自愿地说谎,并且说话时顾及后果;这表明,奥德修斯既有能力又有知识,他不愿意把自己行动的结果托付给虔敬的希望——希望某种道德秩序会增强真实之物。如果把正义理解为能力与知识的结合,那么,奥德修斯就是正义的人;他的正义要求他说谎⋯⋯荷马笔下最伟大的人奥德修斯知道背信弃义的必要性;柏拉图也知道:他笔下的苏格拉底几乎公开为背信弃义的行为做辩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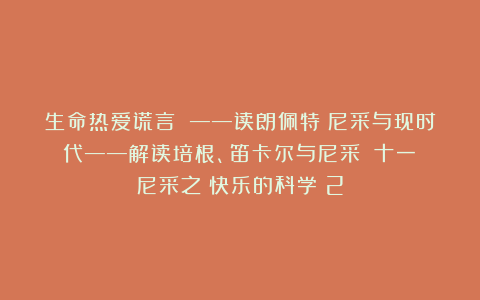
没有人知道荷马偏向谁,我们只能猜测,奥德修斯从《伊利亚特》走向《奥德赛》,而阿喀琉斯只存在于前一部著作中,或许说明了部分问题。另一个角度则涉及生活的经验,阿喀琉斯式的人物在现实中难以存活,马基雅维利式的、奥德修斯式的人物才能够如鱼得水。因为真理的光芒过于刺眼,很少有人能够承受;还因为权力不会允许可能唤醒民众意识的真理,所以真理的代言人只有监狱、流亡、死亡这些类阿喀琉斯的结局。苏格拉底不是好像要颠覆自己有关美德的哲学,“背信弃义”这个词在他的字典里只有工具性的使用价值,是为他推行自己的哲学开路。“谎言”是为正义的谎言,而不是作为恶的形式的谎言。
“柏拉图本人超乎善恶之外:他培育了一套柏拉图主义信仰(即相信真等于善),并借此建立了一种新善恶的统治地位;但柏拉图本人并不相信那套柏拉图主义信仰,他可不像阿喀琉斯那样幼稚。奥德修斯高于阿喀琉斯,狡诈多谋高于单纯的道德。在这个问题上,荷马与柏拉图这两位伟大对手的意见并无二致。但现在,道德柏拉图主义的最新形式(即现代科学,它相信说出真理是好的)却危及整个柏拉图主义大厦。真理言说者的整个制度遵循着勇敢无畏的阿喀琉斯的行为方式,不顾一切后果地说出真理;而公开言说真理的行为最终将要求我们必须看清关于言说真理的致命真理:真理反对生命,而生命热爱谎言。”作为新奥德修斯的尼采出场了,他“要恰如其分地言说真理”。
对于科学与生命之冲突的言说要小心翼翼,“谁一面夸耀自己在言说真理,一面揭露说谎的历史,谁就很可能正在说谎”。
我们需要小心地区分柏拉图和柏拉图主义,尼采反对的是柏拉图主义而非柏拉图。“所谓的柏拉图主义是一种信仰,即信仰’纯粹精神和善本身’,相信真等于善。”但柏拉图哲学隐微/显白的风格,一方面让柏拉图主义变得面目模糊,一方面又显得不仅限于后者。
“由于科学上的柏拉图主义和理性乐观主义信仰,科学如今成了反生命、反自然和反历史的东西。鉴于这种情况,科学还能否与柏拉图主义和理性乐观主义脱离干系呢?科学能否看清自己的道德基础和虔敬,而非简单地屈从于那个触目惊心的判断呢——科学本身就是虚无主义?⋯⋯如今,’诚实’这项最年轻的美德决定了科学的可能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尼采邀请读者反思那个由来已久的老问题,即真理与谎言的问题:最不道德的 polytropoi 者们都曾面对过这个问题,荷马和柏拉图面对过,培根和笛卡尔也面对过。尼采的结论是:新近的最大事件就是,上帝已经死于虔敬者之手。如果确实如此,那么,尼采的主要问题就是:接下来怎么办?虔敬者一旦把他们的虔敬投向他们自身,他们的智性良心一旦转而审查它自身,会发生什么?会发生虚无主义——这将是未来两个世纪的最大事件。接下来呢?为了克服伴随科学的自我追问而来的虚无主义,将有必要冒最大的危险说出真理。哲学虽然怀疑知道者,但仍有必要与知道者们结成联盟,以便克服他们刚刚面临的虚无主义。”
“上帝之死”的重点不在于将其视为一个假设、一个预言或者一个事实,而在于我们是否能够领会这件大事带来的一切后果,即此后我们将以何种面目应对世界和自我。只有直面“上帝之死”,才能直面虚无主义,“我们才能真正赢得我们的欢乐和无畏”。
回答真理与生命(谎言)的问题,就是既秉持科学,又对抗虚无主义的过程,这是一场无可逃避的奥德修斯之旅。奥德修斯需要返乡,我们需要在真理的意义上真正赢得生命(什么?你是说我从未赢得过生命?)。
评价:4.5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26071432@qq.com。)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