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画像中的鸡首人身、牛首人身神灵考
宋艳萍(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在汉代画像中,有一些鸡首人身和牛首人身的神灵形象,这与秦汉时期的宗教信仰有密切关系。为行文方便,下文简称鸡神和牛神。陕西、山西、山东、江苏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中,皆发现了鸡神和牛神形象,但两种神灵在各地的身份和地位存在差异。解析它们的身份,对于探索秦汉时人的宗教观念大有裨益。
一 陕西汉代画像中的鸡神、牛神形象
在陕西省绥德、米脂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中,有很多牛神和鸡神的画像。这两种神灵有时单独出现,更多为同时出现。陕西绥德汉墓墓门画像,只出现了牛神形象,见图1。在右门柱最上面,牛神肩生双翼,端坐于仙山之上。在神木大保当墓门左门柱画像中,亦有此神灵形象,见图2。在画像的最上面,牛神端坐于仙山之上。
图1 陕西绥德墓门右门柱画像
图2 神木大保当墓门左门柱画像石
以上为牛神单独出现的画面,在陕西其他汉代画像中,鸡神与牛神组队出现。如陕西榆林古城滩墓门左、右门柱画像,见图3。在墓门左、右门柱上,分别画有牛神和鸡神形象。两者皆肩生双翼,端坐于仙山之上,侧面相望。相似的画面还出现于陕西绥德墓门左、右门柱,见图4。在画像中,牛神、鸡神分别端坐于左、右门柱的仙山之上。此外,陕西榆林县画像墓左右门柱亦有类似画像,见图5。牛神、鸡神皆端坐于仙山之上。左边为牛神,右边为鸡神。
图3 陕西榆林古城滩墓门左、右门柱画像
图4 陕西绥德墓门左、右门柱画像
图5 陕西榆林县画像墓画像
在陕西汉画像石中,当出现西王母和东王公形象时,两者亦坐于仙山之上,而且西王母在左,而东王公在右。如陕西榆林郑家沟墓门左、右门柱画像,见图6。左门柱上,坐于仙山之上者,戴胜,为西王母形象;右门柱上,坐于仙山之上者,戴三山冠,为东王公形象。陕西类似画像还有不少。从以上画像可以看出,西王母、东王公与牛神、鸡神是两个组合。当左右门柱上是西王母、东王公时,西王母在左,东王公在右;当左右门柱上是牛神、鸡神时,牛神在左,鸡神在右。也就是说,牛神与西王母所处位置一致,而鸡神与东王公所处位置一致。牛神、鸡神,亦与西王母、东王公一样,坐于仙山之上,可见它们在人们心目中地位之重。
图6 陕西榆林郑家沟墓门左、右门柱画像
在陕西神木大保当出土的一幅画像中,牛神、鸡神的属性和地位有更清晰的展现,见图7。画像左边为牛神,右边为鸡神。两者皆肩生双翼,端坐于仙山之上,侧面相望。牛神旁边为象征着月亮的蟾蜍,而鸡神旁边为象征着太阳的三足乌。这样的组合,明显是将鸡神定义为阳性形象,而牛神为阴性形象。
图7 陕西神木大保当墓门楣画像石
陕西米脂党家沟汉墓,在墓门组合画像中,西王母、东王公与牛神、鸡神形象同时出现,见图8。在门楣画像中,中间有一座两层楼阁,两人端坐于下层厅堂之上,皆肩生双翼。左侧之人头上戴胜,右侧之人戴冠。从厅堂外玉兔捣药、九尾狐等元素看,戴胜之人应为西王母,戴冠之人为东王公。楼阁之外,东王公之侧有一只三足乌,代表太阳。西王母之侧有一只蟾蜍,代表月亮。这幅画像中,与太阳相配的是东王公,为阳;与月亮相配的是西王母,为阴。这种画像构成要素与神木大保当墓门楣画像(图7)相似,只不过图7中与太阳相配的是鸡神,与月亮相配的是牛神。图8中,在门楣画像下方,左右两侧是左右门柱上的画像。左门柱上为牛神,坐于仙山之上;右门柱上为鸡神,亦坐于仙山之上。从四者所处位置可清晰看出,西王母与牛神皆在左边,为阴;东王公与鸡神皆在右边,为阳。四者一起出现时,西王母、东王公在高处的门楣之上,牛神、鸡神在低处的门柱之上,显然西王母、东王公的地位要比牛神、鸡神高。这种现象在陕西米脂官庄M2前室东壁画像石组合图中有更清晰呈现,见图9。西王母、东王公与牛神、鸡神皆被刻画于左右门柱之上。左右门柱分别有三层画像。最上层,左右侧分别是西王母和东王公,两者皆肩生双翼,端坐于仙山之上;最下层,左侧为牛神,手持长戟,面门而立;右侧为鸡神,亦手持长戟,面门而立。两者的身份,明显为门吏。从这幅画像可清晰看出,当西王母、东王公与牛神、鸡神同时出现于门柱上时,显然前两者的身份比后两者高,后两者甚至成为前两者的门吏。
图8 陕西米脂党家沟汉墓画像
图9 陕西米脂官庄M2前室东壁画像石组合图
陕西绥德另一座汉墓墓门左、右石画像上,与这幅画像相似,见图10。左右两石呈对称状态,皆分为左右两格,分别又有三层。左石右格上层和右石左格上层,分别有两人,皆端坐于高山之上,华盖之下,四者身份不明。左石右格下层,为牛神;右石左格下层,为鸡神,两者皆手持长剑,相向而立。在这幅画像中,牛神、鸡神皆为门吏形象。
图10 陕西绥德苏家圪坨出土画像
由以上画像可知,在陕北,西王母、东王公崇拜和牛神、鸡神崇拜是混合交替的:在没有西王母、东王公时,牛神、鸡神地位很高,两者坐于仙山之上,地位与西王母、东王公相匹敌;但如与西王母、东王公相配出现时,前两者地位显然比后两者低,甚至变为后两者的门吏形象。牛神的地位和身份,与西王母相对应,即女性或阴性形象;而鸡神,与东王公相对应,即男性或阳性形象。
二 山西汉代画像中的鸡神、牛神形象
山西出土的汉代画像中也出现了牛神和鸡神形象。如吕梁离石马茂庄二号墓前室东壁左右侧画像,见图11。左侧画像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一神仙,坐于仙山之上,华盖之下。仙人肩生双翼,头上梳髻,为女性形象,或为西王母。下层为牛神,一手持棨戟,一手持袋状物。右侧画像也分上下两层。上层有一神仙,坐于仙山之上,华盖之下。仙人亦肩生双翼,戴三山冠,为男性形象,或为东王公。下层为鸡神,亦一手持棨戟,一手持袋状物。这幅画像中,东王公、西王母与鸡神、牛神组队出现。山西画像与陕西画像相同之处为:西王母搭配的是牛神,东王公搭配的是鸡神。可知山西画像依然将牛神视为阴性,即女性;鸡神视为阳性,即男性。牛神和鸡神,是作为西王母、东王公的门吏形象出现,身份比后两者为低。
图11 吕梁离石马茂庄二号墓前室东壁左右两侧画像
在山西吕梁离石马茂庄三号墓前室东壁左右侧画像中,亦出现了牛神、鸡神形象,见图12。左侧画像中,上部为仙人出行图,下部是一牛神形象,手中持一剑鞘状物,侧身站立。右侧画像中,上部亦为仙人出行图,下部是一鸡神形象,持戟侍立。这幅画像中的牛神、鸡神,虽未与西王母、东王公相配,但也和吕梁离石马茂庄二号墓前室东壁左右侧画像(图11)一样,皆为门吏形象。可知在山西汉代画像中,牛神与鸡神,无论是否与西王母、东王公相配,其身份皆为门吏,而不像陕西神木大保当画像(图7),两者坐于仙山之上,地位非常尊贵。
图12 吕梁离石马茂庄三号墓前室东壁左右两侧画像
三 山东汉代画像中的鸡神、马神、犬神形象
在山东出土的汉代画像中,亦有鸡神形象。如山东微山出土画像(图13),这幅画像年代为西汉时期。画面上方,一神仙端坐于堂上,旁有两仙人随侍。堂前站立五位神灵。最左边是鸡神形象,第二位是马首人身神灵形象(以下简称马神)。两者侧身面向右方,拱手而立。两者右边,是两个人首蛇身的神灵形象,皆手持祥瑞之物,侧身面向鸡神、马神。人首蛇身神灵身后还有一神人,拱手侧身而立。
图13 山东微山画像石
山东省滕州市桑村镇出土的画像中,亦可见鸡神、马神形象,见图14。画像最上面一层,中间为东王公,端坐于两龙相交而组成的座位上。其左侧为一羽人,羽人身后为马神和鸡神。两者皆手持棍状物,应为东王公的侍卫形象。
图14 1958年山东省滕州市桑村镇西户口村出土画像
山东省嘉祥县城南南武山出土画像中,不仅有鸡神、马神,而且还多了个犬首人身神灵形象(下文简称犬神),见图15。画像分为三层,最上层,东王公端坐正中,两侧分别有一羽人随侍。右侧羽人的身后,跪着三位神灵,分别是马神、鸡神、犬神。三者皆肩生双翼,手持谒板,虔诚地跪拜东王公。
图15 1969年山东省嘉祥县城南南武山出土画像
山东嘉祥县满硐乡宋山出土画像中,亦为马神、鸡神、犬神的组合,见图16。画像分为三层,最上层,东王公端坐正中,其左侧为马神,其右侧为鸡神、犬神。三者皆手持谒板,虔诚跪拜。
图16 山东嘉祥县满硐乡宋山出土画像
山东汉代画像中,多为鸡神、马神、犬神的组合,却未出现牛神形象。可知民间信仰系统,已与陕西不同。
四 江苏汉代画像中的鸡神、马神、牛神形象
在江苏出土的汉代画像中,与山东相似,亦有鸡神、马神形象。如徐州出土的汉代画像,见图17。画像左侧楼阁上端坐着西王母,戴胜,正接受四位神灵的拜谒。四位神灵,从左到右,第一位为人首蛇身神灵,第二位为马神,第三位为鸡神,第四位为神人。四者皆手中持物,躬身而立。
图17 江苏徐州西王母、弋射、建鼓画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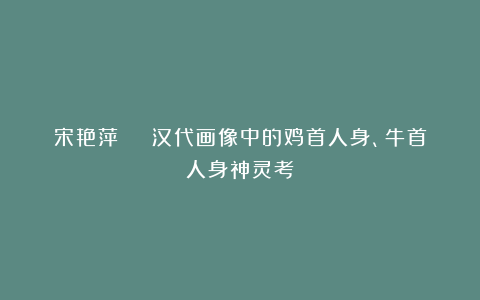
在江苏徐州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出土的画像中,出现了鸡神和牛神形象的组合,见图18。在画像的最右侧为牛神,其左边为鸡神。两者上方皆有榜题,可惜漫漶不清,故无法确知他们的身份。
图18 江苏徐州铜山县汉王乡东沿村画像
从以上两幅画像看,江苏出土的汉代画像中,既有鸡神与马神的组合,亦有鸡神与牛神的组合。
陕西、山西、山东、江苏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中,皆出现了鸡神形象,看来鸡神是民间被普遍信仰的神灵形象。陕西、山西地区,多为鸡神、牛神的组合;山东多为鸡神、马神、犬神的组合;而江苏既有鸡神、马神组合,又有鸡神、牛神的组合,这反映了汉代宗教信仰的地区差异。在陕西绥德、榆林、神木等地出土的画像中,鸡神、牛神高坐于仙山之上,地位甚至与西王母、东王公相匹敌。而山西出土的画像中,两种神灵只是作为西王母、东王公的侍卫,或者持戟的门吏形象。山东、江苏出土的画像中,鸡神和其他几种神灵,皆是西王母、东王公之下的神灵形象,他们恭敬地拜谒,听候差遣。
五 秦汉时期的丰怒特信仰
牛首人身和鸡首人身的神灵身份为何?学界曾有不同的争论。曾磊在陕西考察时,发现了一块未公布的画像石,上面有一幅牛首人身神灵的画像。可贵的是,旁边有榜题为“丰怒特”。后李零在《陈宝怒特解:陨铁与羚牛》一文中有专门论证,同时公布了这幅画像(图19),这就揭开了牛首人身神灵身份的奥秘,它就是来自先秦时期的神灵信仰——“丰怒特”。
图19 陕西 “丰怒特” 画像
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二十七年(前739),“伐南山大梓,丰大特。”此处的南山,即终南山,今为陕西省秦岭山脉。《诗经·小雅·节南山》中曰:“节彼南山”,即为此南山。《汉书·东方朔传》中对南山进行了详细介绍:“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从汧陇以东,商雒以西,厥壤肥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可见南山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且为丰饶之地,其上有梓树不足为奇。关于“丰大特”,学界有不同说法,袁海宝认为:“’丰’在古文中作’豊’,可以和’禮’通用, ‘丰大特’即’禮大特’,意为以大特礼敬梓树。’丰大特’所描述的是伐木之前的祭祀活动,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现象。”张黎明认为:“’丰’当通’逢’,意思是说: ‘砍伐南山大梓树时,遇到了一头大公牛。’”“是伐树遇牛的祥瑞事件,怒特祠因此而建”。可知两者都将“丰大特”视为一种事件,而非一种动物。我们从文献角度重新审视这一问题。裴骃《史记集解》引徐广之言道:“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于丰水之中。”徐广为东晋时人,他所说的“武都故道”,在秦代属陇西郡,在汉代属武都郡,治所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大㪚关东南。据徐广所述,武都郡故道县设有怒特祠,祠中画大牛,祠上生出树木,牛从树中跑出,藏身于丰水之中。徐广所述故事较为简单,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引《录异传》,对此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困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言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坠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
述说的故事情节为:秦文公时,派人砍伐南山上的大梓树,久砍不断,于是听信一病人所言,让人披发,用朱丝绕树,顺利将树砍断。树中冲出一头青牛,逃入丰水中。秦文公派骑兵抓拿,却无法取胜。此时一骑兵掉落马下,待重新上马后,发髻散乱,披头散发,把青牛吓得逃回丰水中,不敢再出现。《录异传》与徐广的相同之处为:皆指出是在武都郡设立的怒特祠,但《录异传》特别强调,怒特祠中所祭祀的神灵,是大梓牛神,即从大梓树中跑出的青牛。《搜神记》中有比《录异传》更为详细的描述,但故事情节大致相同。
因丰大特是秦文公在南山砍伐梓树时出现的,所以也被称为“南山丰大特”。据《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载,皇后拜祭宗庙时所佩戴的步摇,“以黄金为山题,贯白珠为桂枝相缪,一爵九华,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诗》所谓’副笄六珈’者。”皇后的步摇上饰六兽,这一礼制一直持续到南北朝时期。“南山丰大特”为六兽之一,显然是一种动物,所以袁海宝及张黎明将“丰大特”理解为一种事件是值得商榷的。
丰水,即今陕西沣河,宋代宋敏求对丰水的具体位置有详细考证:“丰水,出县西南五十五里终南山丰谷。其原阔一十五步,其下阔六十步,水深三尺,自鄠县界来,经县界,繇马坊村入咸阳,合渭水。”可知丰水发源于南山,汇入渭水。大禹曾在丰水畔治水,《诗经·大雅·文王有声》称颂曰:“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周文王迁都丰水西岸丰邑,周武王在丰水东岸始建镐京,两者合称“丰镐”,而丰水就是两邑的分界。从图20可以清晰看到丰水的地理位置,发源于南山,其西侧为丰,东侧为镐。大禹、周文王、武王皆在此建功立业,可知丰水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独特,丰大特传说与丰水关系密切,这应该是陕西地区将之作为重要神灵来信仰的原因之一。
图20 西周时期中心区域地图(局部)
秦代时,“丰大特”已经被神化为神牛形象,立怒特祠祭祀。到汉代时,更是将其描绘成牛首人身的神灵形象。陕西画像石榜题“丰怒特”,其实是“丰大特”与怒特祠的合称。“怒”有“盛大”之意,所以“丰怒特”其实就是“丰大特”。梁刘孝威谢南康王《饟牛书》中提到:“秦公怒特”,即指秦文公时的怒特,也就是丰大特。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注解“丰大特”道:“今俗画青牛障是”,可知丰怒特信仰一直延续到唐代而不息,其形象为青牛。
六 陈宝信仰及历史演变
陕西汉代画像中的鸡神,曾磊认为:“按照陕北画像石牛首人身、鸡首人身神灵多为对偶神的特点,’丰怒特’画像对应的极可能是’陈宝’。”笔者赞同这一说法。陈宝信仰在《史记》《汉书》《后汉书》中有明确记载。《史记·封禅书》中曰:
作鄜畤后九年,文公获若石云,于陈仓北阪城祠之。其神或岁不至,或岁数来。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从东南来,集于祠城,则若雄鸡,其声殷云,野鸡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陈宝。
文中提到的“作鄜畤(白帝祭处)后九年”,为秦文公十九年(前747)。秦文公获取一枚若石,于是在陈仓北阪城立祠祭祀。若石化作神灵,来去无固定时间,有时一年不来,有时一年来多次。神灵总是夜间来,光芒四射,好似流星,从东南方聚集到祠城,形状好似雄鸡,声音宏大,引起野鸡夜间啼叫。东汉苏林认为若石“质如石,似肝”,可知若石为石质,红褐色之物。秦文公将若石以“陈宝”命名,即陈仓之地的宝物之意,所立之祠称为陈宝祠,以一牢祠祀。《竹书纪年》中有陈宝祠的记载:“二十四年,秦作陈宝祠。”此二十四年为周平王二十四年,是为公元前747年,正与《史记·秦本纪》所记“(文公)十九年,得陈宝”时间相吻合。《汉书·郊祀志》中记载了与《史记·封禅书》相似的内容。此外,扬雄的《法言·重黎卷》、《西京赋》李善注、《通志》等文献中,也有关于陈宝祠的记载,都与《史记·封禅书》基本相同。
《史记·封禅书》认为陈宝祠设于“陈仓北阪城”。关于“陈仓北阪城”的具体地点,历来有不同说法。颜师古认为其在“陈仓之北阪上城中也”,即陈仓城的北部山坡,地点仍在陈仓城中。唐代李泰所编著《括地志》中曰:“宝鸡神祠在岐州陈仓县东二十里故陈仓城中。”宝鸡神祠即陈宝祠,位于故陈仓城中。此“故陈仓城”,应该就是秦汉时期的陈仓城。三国时的韦昭认为陈宝祠“在陈仓县”。陈仓县,“在今陕西宝鸡市东二十里渭水北岸。”秦时属于内史,西汉时属于右扶风。陈仓城应为陈仓县的治所所在之地。唐代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曰:“祠在陈仓城”,陈宝祠的具体位置得以确定,即在秦汉时期的陈仓城中。
《史记·封禅书》中已将若石所化神灵视为雄鸡形象,东汉时若石变为石鸡形象。东汉辛氏所著《三秦记》中道:“太白山西有陈仓山,山有石鸡,……或言是玉鸡。”认为陈宝为陈仓山上的石鸡所化神灵。石鸡所在之地为陈仓山,也就是说,秦文公是于陈仓山获取若石,即石鸡,而在陈仓城内设立陈宝祠进行祭祀。《括地志》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宝鸡神祠在汉陈仓县故城中,今陈仓县东。石鸡在陈仓山上。”
除了陈宝祠,秦文公还在雍州立郊祀和四畤,以祭祀上帝和四帝。但相比于四畤和郊祀,对下层百姓影响较大的是陈宝祠。秦汉时期对陈宝祠非常重视,列入国家祀典,定期祭祀。秦代以一牢祭祀,而西汉时,“雍太祝祠以太牢”。太牢是祭祀规格中最高者,牛、羊、猪三牲全备。以太牢祭祀,可见陈宝祠与郊祀规格相同。西汉皇帝还亲自前往雍州祭祀陈宝,可见对其非常重视。建始元年(前32),汉成帝听从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的建议,将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祠徙置长安南北郊,废雍五畤及陈宝祠。永始元年(前16)三月,因成帝无子嗣,皇太后认为这是因废雍五畤及陈宝祠所致,宣布废止长安城南、北郊,恢复甘泉泰畤、汾阴后土祠,以及雍五畤和陈宝祠等。陈宝祠自汉成帝永始元年复置后,一直持续到西汉末期。东汉时,因定都洛阳,远离雍州,而且洛阳城建立了完善的郊祀制度,所以远在雍州的祭祠,包括陈宝祠都受到了冷落,连西汉设在雍州的雍太祝和五畤尉皆被罢免。东汉时期,陈宝信仰主要流传于民间,陕北的鸡神画像即为明证。
秦汉时期陈宝信仰一直延续,并影响到后世,陈宝的传说也在历史演进中越来越神秘化。陈宝的形象,在历史上几经变化。秦代时,陈宝为秦文公捡到的一块若石。若石化为神灵,经常夜间到陈宝祠。神灵为雄鸡形状,声音宏亮。从这些特征可以看出,在秦代人的心目中,陈宝为雄鸡形象。这一形象一直持续到汉代,所以陕西汉画像石中的鸡神,和东王公相对应,为男性,即阳性形象。刘向认为陈宝祠为“阳气旧祠也”,明确了陈宝的阳性特征。但到了魏晋时,陈宝的形象却发生了变化。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引用《列异传》的传说,对陈宝的故事进行了描述:“陈仓人得异物以献之,道遇二童子,云:’此名为媦,在地下,食死人脑。’媦乃言云:’彼二童子名陈宝,得雄者王,得雌者伯。’乃逐童子,化为雉。秦穆公大猎,果获其雌,为立祠。祭,有光,雷电之声。雄止南阳,有赤光长十余丈,来入陈仓祠中。”《列异传》据传是曹丕所撰。在《列异传》中,陈宝形象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从秦汉时期雄鸡的形象,变为童子的模样,而且一男一女都叫陈宝。陈仓人听闻得到男童者将成为王者,得到女童者将成为霸者,于是纷纷追逐二童子。二童子在陈仓人追逐过程中,都变为雉。秦穆公打猎时,获取雌雉,于是立祠祭祀。而雄雉止驻于南阳,但会经常来往于陈仓祠中。在《列异传》中,秦代所祠陈宝,不再是雄性,而成为雌性,这和汉代画像中陈宝雄性形象完全相反。《晋太康地志》中的记载和《列异传》基本相同。《水经注疏》列举了文献中关于陈宝祠的记载,并指出他们的传承关系和谬误之处,认为陈宝祠的记载始于《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此时并无二童子之说。到了《列异传》时,才开始有了儿童自化为雉,得雄者王,得雌者霸之说。这为了解陈宝形象在秦汉魏晋时期的历史演变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南朝宋人裴骃《史记集解》引瓒曰:“陈仓县有宝夫人祠,或一岁二岁与叶君合。叶君神来时,天为之殷殷雷鸣,雉为之雊也。在长安正西五百里。”瓒可能是东晋时期的傅瓒,或者西晋时期的薛赞,不论是谁,都说明在晋时已经有了叶君之说。此时陈宝被称为“宝夫人”,为女性形象。叶君为男性形象,一年或两年来祭祠与宝夫人相合。唐代司马贞认为陈宝即雌雉,陈宝祠即俗称的“宝夫人祠”,同时将雄雉与叶君联系在一起:“叶,县名,在南阳。叶君即雄雉之神,故时与宝夫人神合也。”叶为南阳郡下的县,叶君就是来自南阳叶县的雄雉之神。东晋干宝所著《搜神记》中,提到了一个重要观点:“其雄者飞至南阳,其后光武起于南阳”。雄者为雄雉,飞到了南阳,成为光武帝起于南阳的征候。《搜神记》将雄雉与光武帝相联,是具有突破性的观点。到了《东周列国志》,更是直接将叶君与光武帝联系在一起,“叶君者,即雄雉之神,所谓别居南阳者也。至四百余年后,汉光武生于南阳,起兵诛王莽,复汉祚,为后汉皇帝,乃是得雄者王之验。”《东周列国志》集合了以往所有的说法,既将叶君直接等同于雄雉,且将其作为光武帝”得雄者王”的验应,叶君成为光武帝得天下的受命之符。《东周列国志》的作者为明朝冯梦龙,说明到了明朝时期,陈宝的故事经层层积累,已然成型,此时学者们更感兴趣的,是光武帝与叶君的关系。
雄雉与光武帝相联,应该是魏晋之后才有的说法。搜索汉代文献,并未提到雄雉,或者陈宝和刘秀有关联的史料。如果西汉后期已经有了这种传说,刘秀是不会放过“得雄者王”如此重要的符谶的。
陈宝还有“天宝”之称。扬雄《羽猎赋》中曰:“追天宝,出一方。”李善注曰:“应劭曰:’天宝,陈宝也。’晋灼曰:’天宝鸡头人身。’”可知天宝就是陈宝。扬雄为西汉晚期人,说明至少在西汉中晚期,陈宝已有天宝之称。晋酌为西晋时人,他将“天宝”描绘为“鸡头人身”形象,这与汉代陕西、山西等地画像石中“鸡头人身”神灵形象完全一致,所以陕西、山西汉代画像石中的鸡神应该就是天宝,也就是陈宝。唐代李白作有《大猎赋》,里面也提到了“天宝”:“获天宝于陈仓,载非熊于渭滨。”这里的天宝也是陈宝。
七 陈宝、丰怒特画像的作用和意义
在陕西绥德、神木、米脂等地的汉代画像中,鸡神、牛神往往同时出现。牛神为丰怒特,而鸡神应为陈宝。两者为何会组队出现?它们在画像中的作用和意义何在?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丰怒特传说中,秦文公砍伐大梓树的具体位置,据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记载:“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这里的“仓山”,应为“陈仓山”。而《括地志》也明确提及秦文公得若石的地点亦为陈仓山,则丰怒特与陈宝的传说皆源于一座山,即陈仓山。据《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记载:陈仓山“亦名宝鸡山,鸡峰山。即今陕西宝鸡市东南四十里鸡峰山。”陈仓山应属于南山(即秦岭)的一部分。即使狭义上的南山,陈仓山也包括在内。所以《史记》记载的“伐南山大梓,丰大特”,所言不虚。秦文公时期所伐梓树在陈仓山上,而陈宝亦为陈仓山所得若石所化,则丰怒特和陈宝,皆为发端于陈仓山的神灵崇拜,这应该是汉代画像中两者组队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两者所承载的作用与意义。
“丰怒特”的故事中,两次提到了披发:一是披发将神树砍断,二是披发吓退青牛。这两次披发,作用皆为厌胜,即以披发的形式,让树神和青牛恐惧,令之屈服。《录异传》提到:“有骑坠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搜神记》中亦记载道:“故秦自是置旄头骑。”此外,《列仙传》中也有记载:“秦文公时,有梓树化为牛,以骑击之,骑不胜。或坠,髻解被发,牛畏之,入河。故秦因致旄头骑,使先驱。”《录异传》中的“髦头”即为《搜神记》及《列仙传》中的“旄头骑”,是秦代设置的一个兵种,士兵皆披散头发,作为先锋部队。汉代设旄头郎,简称旄头。据应劭《汉官仪》记载:“旧选羽林郎旄头,被发为先驱。”可知“旄头”是从羽林郎中选拔出来,披发,作为皇帝开道先驱侍卫。公孙戎即为汉高祖时的旄头;汉宣帝去祭拜孝昭庙时,即以旄头作为先驱;汉宣帝时燕王刘旦私建旄头先驱,成为其谋反的重要证据。汉代的旄头,源自秦代的“旄头骑”。而“旄头骑”的来源,如《录异传》及《搜神记》等所言,正是“丰怒特”的传说。士兵之所以披发,是要像披发吓退青牛的骑兵一样,战胜邪恶,克敌制胜,一往无前。
“丰怒特”传说中,披发能砍断梓树;骑兵披发吓退青牛,其实为一种巫术,即以披发的形式,达到让对方恐惧、折服的目的。这一巫术在秦汉时期非常盛行。据《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梦》记载:
人有恶瞢(梦),(觉),乃繹(释)发西北面坐,(祷)之曰:「皋﹗敢告(尔)。某,有恶瞢(梦),走归之所。强饮强食,赐某大幅(富),非钱乃布,非茧(一三背)乃絮。」则止矣。(一四背壹)
简文内容为:人作了恶梦,解发向西北方向而坐,并进行祷告,祈求将噩梦带走。通过这种方式,就能止住恶梦。《睡虎地秦简·日书乙种·梦》中亦记载了相似内容:
凡人有恶梦,觉而择(释)之,西北乡(向)择(释)发而驷(呬),祝曰:「(皋),敢告(尔)宛奇,某有恶梦,老来□之,宛奇强饮食,赐某大(富),不钱则布,不(茧)则絮。
简文内容为:作了恶梦,要面向西北方向,释发,并祝祷。此处所祈祷带走恶梦的神灵为宛奇,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梦》中的“”有别。除了两者,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伯奇食梦。”伯奇食梦还记载于敦煌本《白泽精怪图》中:“人夜得恶梦,旦起于舍,向东北被(披)发呪(咒)曰:伯奇,伯奇,不饮酒,食宍(完)常食,高兴地,其恶梦归于伯奇,厌恶息,兴大福,如此七呪,无谷(苦)也。”此止梦方法与《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梦》基本相同,皆为披发祈祷,只是方向上为东北,祈祷的神灵为伯奇。、宛奇、伯奇,三者皆食梦,已有学者指出三者其实为一种神灵。《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的《梦》及敦煌本《白泽精怪图》,均提到了披发,可见披发为止恶梦的重要方法。
披发不仅能止恶梦,还能祛鬼。据《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诘》记载:“人行而鬼当道以立,解发奋以过之,则已矣。”鬼阻挡人行走,解发奋力走过,就能压服住鬼。
披发能止恶梦、祛鬼,所起作用皆为厌胜。“丰怒特”传说中两次披发,其作用亦为厌胜。所以人们将丰怒特视为一种除妖、厌胜、辟邪的神灵。上文已述,汉代时,皇后步摇上饰熊、虎、赤罴、天鹿、辟邪、南山丰大特六兽,其中的南山丰大特就是丰怒特。这六种兽中大多数为凶猛动物,之所以将它们作为配饰,是因其凶悍,能压制邪祟,起到辟邪的作用。秦汉时人将丰怒特作为神灵崇拜,将其形象刻画在墙壁上,墓室中,是将之视作除妖、辟邪的保护神。
陈宝,是秦及西汉时期一直列入官方祭祀系统的神灵。汉成帝就陈宝祠的废立问题专门咨询刘向。刘向的回答是:“家人尚不欲绝种祠,况于国之神宝旧畤!……及陈宝祠,自秦文公至今七百余岁矣,汉兴世世常来,光色赤黄,长四五丈,直祠而息,音声砰隐,野鸡皆雊。每见雍太祝祠以太牢,遣候者乘一乘传驰诣行在所,以为福祥。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来,初元元年以来亦二十来,此阳气旧祠也。”刘向非常反对对祭祠进行变更,认为陈宝祠自秦文公始立以来,一直有福祥出现,高祖时五来,文帝二十六来,武帝七十五来,宣帝二十五来,元帝初元元年(前48)以来亦二十来,所以不能轻易废弃。根据刘向所言,可知陈宝的重要作用,为“福祥”。
福与祸,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先秦思想家们一直在思考这一辩证问题,道家对此有着更深的考量。老子在《道德经》中曰:“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认为福祸相依共存。在周代,太祝掌管六祝,郑司农注释“六祝”曰:“顺祝,顺农年也;年祝,求永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弭灾兵也;瑞祝,逆时雨、宁风旱也;策祝,远罪疾也。”从郑司农所言可以看出,六祝中顺祝、年祝、吉祝为求福纳祥;化祝、瑞祝、策祝为祛灾避祸。可知趋吉避害是人们最关切的问题。东汉桓帝时,荀爽曾在上疏中曰:“礼者,所以兴福祥之本,而止祸乱之源也。”皇甫规亦在贤良对策中提到:“诫以灾妖,使从福祥。”可知福祥与祛祸,在人们生活中最为重要。司马贞在《史记·秦本纪》述赞中曰:“祥应陈宝,妖除丰特。”可知两者出现在画像中的作用,陈宝为福祥,丰怒特为除妖,这正是人们求福祛祸思想的反映。两者的作用与汉代墓外石兽天禄与辟邪的作用相似。据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后汉天禄辟邪字》记载:“右汉天禄辟邪四字,在宗资墓前石兽膊上……墓前有二石兽,刻其膊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天禄为天赐福禄之意,所起作用为纳福;辟邪为辟除邪祟之意,所起作用为厌胜。陈宝、丰怒特,与天禄、辟邪一样,所起作用,皆为纳福祛祸。所以陕北地区多出现陈宝、丰怒特组合出现的画面。人们将这两种神灵视为吉祥、力量的化身,能保佑人们生命、财产的安全,能消除灾祸,带来福祥。陕北多地对两者的崇拜,甚至超过了西王母、东王公,这是陕北很多汉代画像中两者高居仙山之上的缘由。相比与祛祸,人们更喜欢福祥,这是陈宝更受欢迎的原因所在。所以在秦汉时期,陈宝祠被列入官方祭祀系统,享受太牢祠祭的待遇。而怒特祠在汉代并未列入官方祭祀系统,它的受众主要来自中下层民众。
山西与陕西临界,应该深受陈宝、丰怒特信仰的影响,所以会有陈宝、丰怒特组合出现的画像。但山西对西王母、东王公更为崇拜,所以两位神灵的地位要低于西王母、东王公,往往作为门吏形象出现。山东、江苏远离陕西,民间信仰已存在很大差异。山东甚至没有见到牛神,而是以马神、犬神与鸡神相组合。山东的一些鸡神画像,鸡首甚至接近于鸟首。所以,山东、江苏出现的鸡首人身神灵是不是陈宝,我们不敢妄下结论。姜生对江苏徐州铜山县汉王乡出土画像(图18)进行了研究,认为牛首人身的神灵名曰“罗縆”,是“天下鬼神之主”,即“北太帝君”炎帝(炎罗)。牛首之神左边的鸟喙之神,名曰“灵鸧”,是太上老君。姜生所言可备一说,是否正确,不敢断言。山东、江苏的鸡神、马神,地位皆低于西王母、东王公,这与山东、江苏等地西王母信仰氛围浓厚相关。西汉哀帝建平四年(前3),发生了一次大规模流民运动。据《汉书·哀帝纪》记载:“(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这次流民运动首先从关东兴起。关东,也就是函谷关以东的地区。马怡认为:“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省新安县)以东,其范围很大。不过,从道教的起源与活跃之地,从行筹者经历了二三十个郡国、奔走约两三个月(正月至三月)而抵达长安等情况看,该事件所涉及的郡国可能是在青、徐、兖、豫等州及冀州南部、扬州北部,即今山东、河南、河北、安徽、江苏等地,而不会远至更北或更南的地域。”今山东、江苏肯定是这次大规模流民运动的重要活动地区,说明西王母信仰早在此地盛行,并成为传播西王母信仰的重要基地。所以,鸡神、马神、犬神等神灵屈居西王母之下也就合情合理了。
虽然山东、江苏等地出现的鸡神、牛神的身份还不能厘定,但可以确知的是,陕北画像中出现的牛神为丰怒特,而鸡神应该就是陈宝。两者在汉代画像中的作用,前者为除妖,后者为福祥。陈宝、丰怒特画像的出现,为研究先秦秦汉时期的宗教信仰,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史料。
原文发表于《形象史学》2024年夏之卷(总第30辑),注释请参考原文。
编辑:希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