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医药史上,曾经有过一个治疗疫病的方剂。宋人用以治疫,“活人甚众”“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然而,同一个方剂,到了北宋末年至明朝中叶,同样是在治疫中,却出现了“杀人无数”“病者服之,十无一生”“被害者不可胜数”等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是古代医药学史上一桩褒贬不一的公案,这桩公案与一位名人有关。此方于世影响甚大,历代医家多有记述。方剂的名称是“圣散子方”,最早见载于庞安时的《伤寒总病论》。与其有关的这位名人就是大文豪苏东坡。
苏轼 (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北宋文学家、诗人、书法家。宋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东坡因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获罪,遭弹劾罢官,被捕下狱,差点被杀了头,史称“乌台诗案”。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这才免于死罪,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正月初一,苏东坡离京赴黄就任,二月一日到达黄州。此后直至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苏东坡前后在黄州呆了4年多。是年,黄州及邻近州郡大疫流行,死人无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位于湖北东部、距武汉78千米。对于黄冈,国人应该不会陌生,在当今新冠肺炎流行期间,黄冈一度成为湖北省除武汉以外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千古名词 《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苏东坡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谪居黄州时写成的。
同古代许多亦儒亦医的文人学士一样,苏东坡也非常热衷于医道,并在医药、养生和防疫方面多有建树。在进士及第入仕后,他经常拜访御医、医药名家、僧道和民间郎中,广泛收集在民间、道家、佛家间流传或秘藏的验方、偏方。著名的《苏学士方》,就是他的与医药和养生相关的文字作品,后来有人把它与宋代名儒沈括的《良方》合编为《苏沈良方》。
苏东坡在四川眉州老家有一个名叫巢谷的朋友。元丰五年九月,巢谷从眉州来黄州探望苏轼,直到第二年正月才离去。在黄州期间,巢谷用所藏的秘方“圣散子方”救治了不少身染瘟疫的人。苏东坡遂求方于巢氏。巢谷,字元修。行伍出生,亦通医道,“多学好方”,喜欢交结朋友,是一个危急之事可以托付的人(苏辙《巢谷传》,“缓急可托者也”)。
巢谷收藏的圣散子方“不知所从出”,其自称得之于“异人”。他对此方非常珍惜,连自己的儿子都不传授。在连年瘟疫肆虐、亟待解民于倒悬的情况下,巢谷终于禁不住苏东坡的再三央求,答应将药方传授给他。但要他指江水为誓,保证永不传人。
然而,苏东坡并没有践诺,他怀着一颗普济众生的仁爱之心,很快就将圣散子方传给了庞安时。庞安时(约公元1042—1099年),字安常,蕲州蕲水(今湖北黄冈浠水)人。苏东坡因病与之结识,后来二人成为很好的朋友。“安时以善医闻于世,又善著书,欲以传后,故以授之,亦使巢君之名,与此方同不朽也。”(苏东坡《圣散子叙》)庞安时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以善治伤寒著称,被后人誉为“北宋医王”。苏东坡将方子传给庞安时,是希望通过他让方子流传下去,惠及后世。
庞安时果然没有辜负苏东坡。1099年,他完成了《伤寒总病论》,书中记载了圣散子方。从此,圣散子方传于天下。其时,苏东坡已远谪海南,自身处境困难,但仍允诺为《伤寒总病论》作序。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哲宗驾崩,宋徽宗继位,苏东坡从海南儋州获赦北归。这一年,苏东坡写了《圣散子方》一书,书中仅收载圣散子一方。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中收藏有该书的宋代刻本及旧山楼赵氏抄本。
巢谷授方后,苏东坡按照“圣散子”的配方,“合此药散之,所活不可胜数”(苏东坡《圣散子叙》),使黄州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在苏轼的弟弟苏辙因受“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至任监筠州(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期间,该地也遭遇了一场大疫。“时大疫,乡俗禁往来动静,惟巫祝是卜。”(《雍正江西通志》卷六十“名宦四”)苏东坡得知后,也让他使用圣散子方,遂使筠州疫民所活无数。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东坡任龙图阁学士,在杭州做知州。这是苏东坡第二次来杭州任职。履新后的第二年春天,杭州大旱,颗粒无收,继而是持续了一年多的疫疾大流行。《宋史·苏轼传》记曰“大旱,饥疫并作”,即饥荒与瘟疫并行,百姓苦不堪言。于是,苏东坡又拿出圣散子药方,命下属按方司药,无偿分发给杭城民众。结果,“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所用皆中下品药,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所济已及千人。”(苏东坡《圣散子后叙》)不仅如此,在疫情趋于缓和后,他还派专人“作饘粥、药饵,遣吏挟医,分方治病,活者甚众”(《续资治通鉴长编》)。
圣散子方用于黄州大疫、筠州大疫、杭州大疫,三大“战疫”均大获全胜,且花钱又少。苏东坡曰:“用圣散子者……若时疫流行,不问老少良贱,平旦辄煮一釜,各饮一盏,则时气不入。平居无事,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圣散子方用于疫疾可谓药到病除,简直就是著手成春的万应灵药。
难怪苏东坡对圣散子方赞美有加:“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子女人相易,状至危笃,速饮数剂。而汗出气通,饮食渐进,神宇完复,更不用诸药,连服取瘥。其余轻者,心额微汗,正尔无恙。药性小热,而阳毒发狂之类,入口便觉清凉。此药殆不以常理而诘也。”(《圣散子叙》)
然而,就是这个被苏东坡百般推崇的圣散子方,在后人的应用中却屡屡出现了意外。
元祐辛未年(公元1091年),永嘉大疫,当地人纷纷效法“圣散子方”。结果,“被害者不可胜数”(明俞弁《续医说》卷三“圣散子方”)。永嘉医派创始人陈无择在《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也有相同的记载。
北宋宣和 (公元1119—1126年)末年,“金人围困汴京,城中疫死者几乎半数”(《宋史·五行志》)。“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宋·叶梦得《避暑录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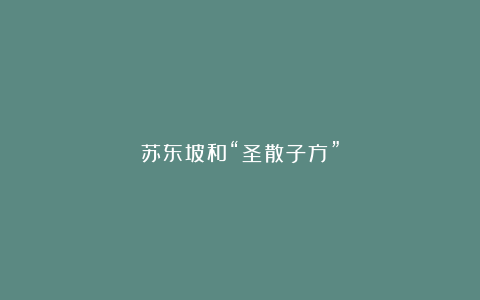
明代弘治癸丑年(公元1493年),“吴中疫疠大作,吴邑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无一生”(明·俞弁《续医说》卷三“圣散子方”)。
曾几何时,一个当年“活人甚众”的济世良方,变成了“杀人无数”的凶神恶煞。圣散子方也从名噪一时而渐次归于沉寂。同样的一个方剂,在后世的应用中竟会如此功过相左,实在令人始料不及。
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记载的圣散子方原文如下:
肉豆蔻(十个)、木猪苓、石菖蒲、茯苓、高良姜、独活、柴胡、吴茱萸、附子(炮)、麻黄、厚朴(姜炙)、藁本、芍药、枳壳、白术、泽泻、藿香、吴术(蜀人谓苍术之白者为白术,盖茅术也,而谓今之白术为吴术)、防风、细辛、半夏(各半两,姜汁)、甘草(一两)。
(今按:方中“肉豆蔻”一味,《苏沈良方》和《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均记为“草豆蔻”)
大致做一下方义分析:方中麻黄、细辛、附子、吴茱萸、高良姜温阳散寒;苍术、厚朴、藿香、半夏、石菖蒲、草豆蔻苦温燥湿,茯苓、猪苓、泽泻淡渗水湿,白术健脾化湿,防风、藁本、独活祛风胜湿;柴胡、枳壳、芍药、甘草合为四逆散,透邪解郁,疏肝理脾。
值得注意的是,在《伤寒总病论》中,庞安时是将圣散子方放在“寒疫”条下的,这说明庞氏对“圣散子”用于治疗寒疫这一点有清醒认识。可惜,他没有进一步强调,只载其方其叙,其他未置一言。
而从方药组成看,圣散子方全方偏温,用于时行寒疫病自无不可。但世上可有“一切不问”、包治百病的神药?试想,若当时黄州、筠州、杭州流行的是温热疫病,以此辛热燥烈之药治疗,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可见,作“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子女人相易”之语,则未免言过其实。
明代医学家张凤逵在《增订叶评伤暑全书》中指出:
“圣散子寒疫挟湿之方而设,永嘉、宣和年间服此方殒命者,是因为以寒疫之方,误施于温疫而致。”
明代学者俞弁更是在《续医说》中做了具体分析:
“昔坡翁谪居黄州,时其地濒江多卑湿,而黄之居人所感者,或因中湿而病,或因雨水浸淫而得,所以服此药而多效。是以通行于世,遗祸于无穷也。……殊不知圣散子方中,有附子、良姜、吴茱萸、豆蔻、麻黄、藿香等剂,皆性燥热,反助火邪,不死何待?若不辨阴阳二证,一概施治,杀人利于刀剑。”
所云观点鲜明,深中肯綮,有很强的说服力。
中医药之谓“疫”,包括多种烈性传染病,未可用一方通治之。由辛香燥烈之药组成的圣散子方,即使用以治疗寒疫,亦应辨证加减使用。倘若并非寒疫,或者是其他什么疫病,随便套用此方,则难免产生严重后果。
人之患病,五花八门。即便所患之病其证相同,其病程亦是千变万化,岂可一药而通治之?辨证施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根据四诊所收集的资料,通过分析、综合,辨清疾病的病因、性质、部位及邪正之间的关系,概括、判断为某种性质的证,而后据以施治。方宜据证而建立,药宜据证而增减;还应有因病而异,因人而异,因地域、气候、季节诸因素而异之判断。
如果辨错证、用错药,那就如同是火上浇油。是死于药,而非死于病也。如此,能不儆戒乎!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