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侯爵的遗孀是个声誉极佳的女子,她的两个孩子也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她让M市的一家报纸登出如下的广告:她在自己不知悉的情况下怀了身孕,即将出生的孩子的父亲应前来报到。为顾及家庭起见,她决计和此人结婚。”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开头,“声誉极佳”是基调,“不知悉的怀孕”是意外,“登出广告”是仿佛自取其辱又视死如归的行动。面对埃涅阿斯绝情的离去,狄多女王自焚表明心迹;面对将耻辱加诸在自己身上的陌生人,O侯爵夫人选择承受。
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薇拉面临的困境是选择挚爱的吉尔沙洛夫,还是将自己救出苦海的罗普霍夫。一个是爱情本身,一个是似乎唯有爱才可偿还的恩情。对于O侯爵夫人来说,不存在这样的两难困境,当母亲问她是否有什么办法作一个可以避免这一场不幸的表态时,侯爵夫人回答说:“最亲爱的母亲!这是不可能的,要把我的感激之情置于如此严峻的考验之上,这对我来说是件憾事。不再嫁人乃是我的初衷,我不愿意这样轻易地将我的幸福作第二次冒险。”
这里闪现出一个胜过薇拉的现代主义女性的身影,超越于简单的幸福主义之上的,是可贵的独立性和自我意识的觉醒。命运可以愚弄我,但我的态度始终如一。
爱的考验必须只有爱本身作为标准,因此考虑到他的卓越的品质,只要经过足够的了解,她说,“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他的愿望是那样强烈,我对他又负有义务,我将满足他这种愿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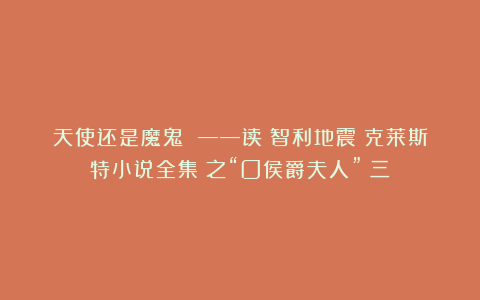
侯爵夫人终于显出怀孕的身形,母亲不相信她会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父亲和哥哥都要将她扫地出门。很多时候我们就像她一样,要使人们相信自己的无辜是不可能的,对此只能自我慰藉。家人谴责她的依据在于未婚先孕和公然的撒谎,因为一个女人不知道与自己上床的男人是谁是不可思议的。是否撒谎?也许是克莱斯特设置的迷雾,侯爵夫人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让我们穿透迷雾,认识一种现代性——永远不会有答案,只会有不安,灵魂在不安中、挣扎中生长。她决计回到自己的庄园,独自抚养孩子,但也不想放过或者说一定要认清那个人类中“无可救药的渣滓”,于是登出了“稀奇的启事”。
F伯爵在拜访中听闻了丑闻,赶去庄园重申他的求婚,遭到拒绝。当他看到报纸上的启事时,他告诉司令官(侯爵夫人父亲)说一定能找到这个人。当我们还疑惑于为什么他会如此肯定的时候,隔天报纸上就发表了一篇声明:“O侯爵夫人如愿在三号上午十一点钟在其父G先生的家里露面的话,那么她所寻找的人届时将会拜倒在她的脚下。”这一声明紧紧揪住了我们的心神,一切都将真相大白。唯一感到疑惑的是,犯下罪行的男人有什么理由让自己的丑行大白于天下呢?最下贱的人也残存着尊严,不可能甘心自取其辱。
时间一到,出现的是F伯爵,他单膝跪倒请求原谅。侯爵夫人“面容像火炭似的红,复仇女神的目光也没有她的目光可怕”。“我原想是一个缺德鬼,可没料到是一个魔鬼。”她说。“是什么原因使她觉得F伯爵比另外一个别的人更为丑恶”,这是一个具备显而易见答案的问题。
婚礼照常举行,伯爵夫人不久诞下一个男孩。一年之后F伯爵获得了谅解,二人举办了第二次欢快得多的婚礼。“伯爵很是幸福,有次他问妻子,在那可怕的三号她本来对任何缺德鬼都有所准备,为什么对他却唯恐避之不及,就像逃避魔鬼一般?伯爵夫人一面投向他的怀抱,一面回答道:假如他给她的第一印象不是一个天使的话,那么那时她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魔鬼。”
但问题永远在(就像阿狸永远站)。考虑到战争期间F伯爵救下了她,我们很难相信他会趁人之危占有了她,而对一个心有所属的恩人的举动,她竟会毫不知情。故事中只提到F伯爵在司令官家住了一晚,但没有丝毫的异常。更合乎常理的解释似乎是:兽性的俄国兵让她怀了孕,F伯爵充当了挽回局面的角色。真相和谎言与迷雾纠缠在一起,我们永远无法得知确切的真相。
斯蒂芬·茨威格说:“克莱斯特的世界像他本人一样奇特、没有时代性,它是一个远古的领域,远离一切目光和清楚的显像。像人一样,自然、世界只有在变得充满魔性时,在自然的变得神秘,普遍的变得特别,世界化为原始世界,超越了自身,进入闻所未闻、不可思议的领域,甚至可以说,当它变得过分、变得罪恶、脱离了规范时,才会使克莱斯特发生兴趣。和在人性中一样,在事件中他也只关注那些不正常的、脱离规则的东西(《O侯爵夫人》、《洛迦诺的乞讨女人》、《智利地震》),也就是说,总是关注那些人物看起来似乎冲破了神预先划定的圈子的时刻。他没有白白充满激情地阅读舒伯特的《大自然的阴暗面》:所有夜游症似的反常现象,所有意志移植、动物催眠术都是他那夸张的想象力所欢迎的素材,他对人类的激情还不满足,现在又借来了宇宙的神秘力量,好使他创造的人物更加陷于迷乱之中,感情的迷乱中还要加上事件的迷乱!特殊的东西永远是克莱斯特最喜爱的栖居之地:在这里他总能在阴影或深渊的某处感觉到那个处处强烈地吸引他但又令他抗拒的魔鬼;在这里他接触不到那些使他厌恶又害怕的凡俗的东西;在这里他能作为一个永远的无度之人越来越深入到大自然的秘密中去。甚至在世界本质中,他也像在感情中一样寻找最高级。”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不会执拗地怀疑O侯爵夫人被占有的不自知,也很难相信F伯爵犯下了他所承认的丑行。我们相信世界充满魔性,某些时候甚至会有违背理性的催眠术,但“不正常的、脱离规则的东西”正是为了体现世界的本质。在F伯爵那里,或者是不容置疑的骑士精神(如同屋顶上的轻骑兵),或者是淬炼出爱的火花的牺牲与忍耐。在O侯爵夫人那里,或者是女性尊严的顽强捍卫(哪怕被扫地出门,被最亲近的人羞辱和唾骂),或者是对真相的永恒的追问。
还有我们对天使与魔鬼的态度。一个魔鬼让我们震惊和厌恶的程度,永远比不上这样的情形——起初他是天使,慢慢地却变成了魔鬼。所以我们就像O侯爵夫人一样,对于此类情形,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考察,他究竟是天使还是魔鬼,是披着天使外衣的魔鬼,还是用魔鬼的伪装行天使之事。或者,一个冰冷但颇具真理性的事实是:我们根本无从分辨,因为每个人都集天使与恶魔于一身。
评价:5星
(本文内容为作者独立观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授权事宜、对本稿件的异议或投诉请联系[email protected]。)
微信号|琴弦在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