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今“新天地”一带可谓人文荟萃、翰墨生辉。刘海粟住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西门路(今自忠路)有黄宾虹、张大壮,白来尼蒙马浪路(今马当路)西成里住张善孖、张大千兄弟,丁悚旧居和漫画会则在贝勒路(今黄陂南路),葛罗路(今嵩山路)上有吴湖帆的梅景书屋和冯超然的嵩山草堂,更有陶冷月、林散之、陆俨少、谢稚柳……等等等等。这些名字报出来,差不多是半部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这些大师有的只在上海留下雪泥鸿爪,有的终老于斯。面对人生高低不同的境遇,各人有各人的活法,今天单说一位住在淡水路的大师:画花鸟“一只鼎”的常熟州老伯伯陆抑非。
陆抑非
1908-1998
上海的弄堂曲曲弯弯四通八达,马当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所在的马当路普庆里,和西面的淡水路就是通的,只是弄道狭窄,普通游客可能没有这么七转八绕的耐心。普庆里通淡水路的小夹弄很有意思,北面的房子是拉毛墙,南面却是红砖墙,只是隔开这么两米的距离,建筑的外形截然不同。小弄走到底,门牌变成淡水路219号后门,“非翁”陆抑非曾在此长期居住。普庆里已经征收,现已无法入内。
淡水路219号陆抑非旧居
陆抑非出生于江苏常熟的书香门第,名“翀”,字一飞,小名冲冲,来上海以后才根据“一飞”改为谐音的“抑非”。陆抑非的父亲陆辛甫曾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在上海震旦大学求学期间和于右任、邵力子是同宿舍的“室友”。陆抑非年幼体弱多病,在高二升高三时得了咯血病,家里让他在寺院里清修,叮嘱天天读经不要讲话。也许是这段经历的缘故,陆抑非一生的性格温和谨慎,所谓“祸不失为福,退不失为进,忍不失为得”。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他始终以幽默风趣的人生态度面对,遇到困难时,苏州老伯伯常常就是几句诙谐的“戏话”,一切也就云淡风轻。
29岁时的陆抑非
陆抑非中学就读于苏州著名的桃坞中学,该校由基督教圣公会举办,校长美国人马克·劳顿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梅乃魁”,还说一口流利的苏白。梅乃魁把桃坞中学当耶鲁大学的预科来打造,校风极为严谨,因此陆抑非的英语非常好,他收过外国学生,用英语教国画。1988年陆抑非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中国画短训班讲课,一开始用翻译,遇到翻译不准确,老先生得体地加以修正。美国人说先生你干脆直接说英语得了,陆抑非则坚持和翻译人员共同完成讲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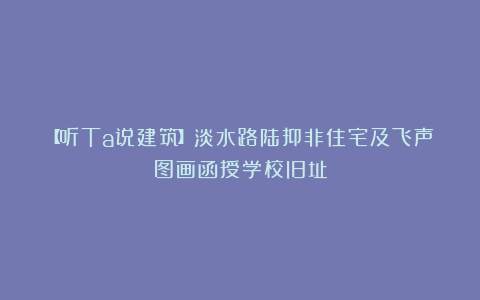
陆抑非能说流利的英语
1930年,年仅22岁的陆抑非来到上海。上海人开门七件事,陆抑非初时生活窘迫,做过不少工作,煤炭行做会计、花边行做绘图员,还在同德医学院教务处做过职员,业余时间才画点扇面贴补家用,一把扇子一角五分。后进入上海美专任教,生活才好起来。1935年,陆抑非在自己的居所创办了飞声图画函授学校,培养了不少绘画人才。可惜因为抗战爆发,学校不得不关闭。后入梅景书屋,原来的名字“陆一飞”由老师吴湖帆改为“陆抑非”。
飞声图画函授学校旧影
陆抑非住宅兼图画函授学校旧址今貌
陆抑非喜欢吃,评论起画来,经常用吃来作比喻,一针见血而浅显有趣。比如他评论挚友潘天寿的画笔味属咸,但咸中有鲜,像醉方乳腐。而恽南田的画是“甜”,但甜而不腻,是冰糖莲子。可惜这么喜欢吃的常熟老伯伯,有时也难免饿肚子。五十年代有几年食品供应紧张,某日清晨陆抑非还没吃早饭就匆匆赶到学校授课,临近中午饿得眼冒金星,苦笑地用苏白说:“先生要饿煞哉,样子勿像先生了。”学生赶紧帮他买了根油条,陆抑非咬了根油条,舒了口气:“奈么今朝先生饿勿煞哉,”学生劝他喝口茶免得噎着,陆抑非正色道:“现在勿要吃茶,让肚皮里再搽一搽。不然水冲下去,油都冲掉多可惜……”话锋一转,陆抑非说:“画花卉也是一样的,好作品要滋润,但也不可一味滋润,枯、湿、浓、淡要搭配好,才算一张好画”……虽说是寓教于乐,终究有点悲凉。
老年陆抑非
陆抑非喜欢评弹,蒋月泉、严雪亭、张鉴庭、姚荫梅都是他的至爱。他那么喜欢讲戏话,想来是受了评弹的影响。评弹讲究“说噱弹唱演,理味趣细奇”,“噱”字排在第二位。评弹讲究“阴噱”,哇啦哇啦喉咙汪汪响,那是有失体面的。陆抑非是个少年时代患过咯血症的人,而能在波诡云谲的时代活了90年,和他与世无争又怡然自得的人生态度是很有关系的。陆抑非六十年代就到杭州任教,后人也在浙江发展了,但他对上海、对淡水路这一带,还是充满了感情。他晚年有一次临写米芾的《苕溪诗帖》,写到“团枝殊自得,顾我若含情;漫游兰随色,宁无石对生”时,老先生连写十一遍“兰”字,还信手写了注解:“此兰字曾见于上海法租界一石库门高级弄堂弄口,横额上所写的梅兰坊三个漂亮潇洒的好字,却原来是从米芾帖上临摹下来的”。陆抑非对上海的感情,从这条注解可见一斑。可叹岁月留痕,梅兰坊还在,但陆抑非念念不忘的临摹米芾的横额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个简体汉字。
现黄陂南路梅兰坊弄口的题字
米芾《苕溪诗帖》中的“兰”字
当年梅兰坊横额上的字体
只能从这个字中去想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