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一到
中国人真是有一种天生的浪漫
借着一点闲、一炉火
在寒天雪地里,活得如此热气腾腾
“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
晴窗待雪,围炉煮茶,满室生温
有些时光,就是用来虚度的
炉火一升腾,那壶茶咕嘟咕嘟咕嘟……
世间的寒冷与荒凉便化为虚无
做点无用的事,说些无用的话
却是通往诗意与心灵的捷径
围炉煮茶,暖冬可亲
几时归来,围炉煮茶
像古人一样,将日子过得热气腾腾
越是寒冬凌冽,越要心怀热忱。就像唐朝的那场漫天大雪,白居易想起故人刘十九,写诗问到:“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此后千载,国人对冬日的美好期待,便定格成一幅诗意煮茶图。
想想很有意思,古人许多妙事,诸如雨天读书、寒夜围炉、松间煮雪……都不是在什么“好天气”发生的。
没办法出门的雨天、天寒地冻的冬夜,改变不了的风霜雨雪,人却在顺其自然之中预备下了一场又一场诗意的事。煮茶也好,温酒也罢,无边冷寂中,偏偏这里温暖如斯,等候知心人前来相会。
到了宋时,人们甚至为此设置了一个节日,时称“开炉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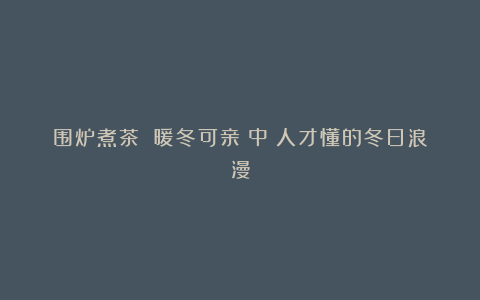
从十月初一,宋人便开始用炉火。开炉之后,及至冬至来临,连冬起九,好友轮流围炉宴请,至除夕守岁享年节之欢,再至二月初一日撤火,方告停歇。
就算是一百年前,郁达夫还在散文中写着:“凡在北国过过冬天的人,总都道围炉煮茗,或吃煊羊肉,剥花生米,饮白干的滋味。”
从古至今,生一炉火,将日子过得热气腾腾,就是国人迎接风雪的姿态。
活火,煮出妙味
缓缓升温,发挥老茶的滋味和香气
发明风炉者是茶圣陆羽,陆羽《茶经》介绍茶之器,开篇就是小风炉:“或锻铁为之,或运泥为之”。其形如古鼎,有三足两耳,炉内有厅,可放置炭火,下腹有窗孔,用于通风和出灰。
《高隐图》(局部) 明 陈洪绶
茶的清欢之味令人向往,但决定茶好不好喝的却是煮的过程。
虽然大家已习惯盖碗泡茶、电磁炉煮茶,但一盏小炉,一把陶壶,活火细煮,仍有属于它自己的优点,它能发挥老茶的滋味和香气。
那些年份较长、全发酵、甘醇浓烈的茶品,如熟洱、老茶头、红茶等,盖碗泡不开、电磁炉又常常煮的过快,这时用火炉陶壶刚刚好。
一般不锈钢水壶,水温只能到达98-99°,不能完全将老茶的茶韵激发出来,但若用陶壶煮,水温便可到100°。
所以除了备些常规的泡茶、煮茶器物,也可以备一盏风炉,一把陶壶。不只是为了陆羽的那份醇厚茶味,也是为了在煮茶时,体验到逐渐升温的过程,任由身体和心情被这件事搅得热了起来。
手工制作,器韵秀雅
一把壶,一盏炉,凝练造物之美
在茶事空间里,器物的美,往往凝练着文化的美、精神的美。
这些陶壶和风炉,外形与线条之如此优雅流畅,得益于匠人对器物的理解,再耗费良久,手工拉坯、修坯才制作完成。
无论是诗文印风炉还是国画风炉,也都是一笔一画手工印刻、绘制而来。
白泥做炉,烧制温度较高,成品率更低,但好处是更加耐火,利于茶事。它甚至可以干烧,也可以实现炉上加水,就是说一壶水烧尽,可以直接加冷水续煮,而不会坏壶。
三把不同形式的壶,能满足不同的审美需求,配以薄胎,很快便能茶香四溢。若是无意间看到壶身的手工痕迹,你会更加懂得它的细节美,好不欢喜。
煮云壶:拙朴敦厚,把手方便拿取,出水流畅。
听雨壶:器型优美秀丽,柔润挺括,观之典雅。
福禄壶:器型圆润中又带着趣味感,福禄福禄,可亲可爱。
印刻诗文款,“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将围炉煮茶的心境描写其上。
生活有“竹意”,心中有竹意。手工雕刻的浮雕山石,和手绘竹子清灵高雅,结合作画,十分巧妙。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岁寒苍松,不畏凌寒,高洁君子。
烹茶、赏器、食果
亲朋知己围坐,慢煮岁月悠悠
生一钵炉火,煮一壶清茶,和家人好友围坐,有壶有炉,还得有好杯、好茶、有好食。
THE END
广袤世界,感谢相遇
相逢相知相识一笑,很近很近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间风月如尘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