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喜爱的散文:陈振林6000余字散文《站成一棵树》刊文学名刊《阳光》2024年第9期。这是一篇怀念我老家的树、老家的人的散文。
站成一棵树
陈振林(中国作协会员)
“绿树村边合”,一个村子如果没有了一棵又一棵的绿树,就没有了村子的样子。
小时候,我不过六七岁,跟着母亲去到外婆家。出了我们的村子,上了一道高堤,就远远地望见一个村子了。那是外婆的村子,叫着“鱼鳞台”这样一个有趣的名字。其实还有二三里远哩,我们望见的是一片绿树的模样。那些树们,大大小小,高高矮矮,抱成一团,连成一片,成了一个岛屿的形状。近些,如果有风,是可以看到树们点头的姿势的,这是欢迎远到的客人。
外婆的家在村头的第一家。两位舅舅前后两间屋子,屋子不大,周围全部是树。那树们,像人,站在屋子的四周。外婆单独住着一间小屋子,小屋子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树,我觉得是村子里最高最大的一棵树。树是大柳树,能够长出像鸭嘴果实的那种树。那像鸭嘴的果实是倒垂的,过些时日会老,就会轻轻地掉在地上,像人随意地叹一口气。我们也会捡起这些果实,拿在手中把玩,但它是不能够食用的;不像枣树上落下的枣子,在地上随意捡起,擦一擦枣上的泥就能放入口中的。我在外婆村子里和伙伴们玩耍,即便是在村子里走得远了,无论玩到什么时候,只要能看到那棵大柳树,我是一定能够找到外婆的家的。
幼小的我就觉得,那棵树就是我的外婆,我的外婆就是那棵树。找到那棵大柳树,就找到了我的外婆。
我的外婆,普通寻常的一个老人,活成了一棵树。这个老人,在六十多岁的年纪得了“粗脖子”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医疗匮乏的年代,也只是这个称作“粗脖子”病的甲状腺肿,要走了老人的生命。外婆走了,我去到那个叫作“鱼鳞台”的村子也去得少了。那棵垂着鸭嘴果实的大柳树,仍站在村口。但我不想再看见那棵树,那树影像是外婆的身影。
我一直在外读书,后来参加工作也在外地。每次我回到生我养我的村子,同样,在三四里远之外,我也是先看到那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树们。他们,在欢迎着我回家。
村子里的树品种并不杂乱,以柳树、杨树和楝树居多,果树也不过是桃树和枣树,偶尔也杂几棵桑树、李树和柚树。我们村子所说的“杨树”“柳树”名称似乎与后来教科书上所说的正好相反,杨树成了柳树,柳树成了杨树。地域不同,叫法不同,这也许是“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的道理吧。但这一叫法据说也是有个故事的。隋朝建立之初,建立者杨姓家族为避讳,传告天下将“杨树”称之为“柳树”。隋朝疆域居北,此说法当时在北方流传甚广,并得以施行。不过,偏远的南方对这一说法还没有得到贯彻之时,隋朝已经走完了它三十多年的历程而寿终正寝。所以,之后的神州南北,北方人大多将“杨树”称作“柳树”,南方人仍将“杨树”称之“杨树”。也就有了一个值得玩味的事,那就是到底是“杨树”还是“柳树”,南方人与北方人一直争论不休。也便有了俗语“杨树不认得柳树”,也有说“喝了辰时酒,不认得杨和柳”,让生活多了些趣味。
柳树是村子里树木王国的大哥,长得最是高大,都垂着青绿的鸭嘴样的果。杨树有着柔软的枝条,迎风而飘,像细腰的美女跳起了舞蹈。春天里开满了或红或白的花儿的是桃树,大多站在屋子前边的角落处;等到炎夏到来之时,那挂满了桃儿的枝就成了孕肚的母亲一样,骄傲地扬起了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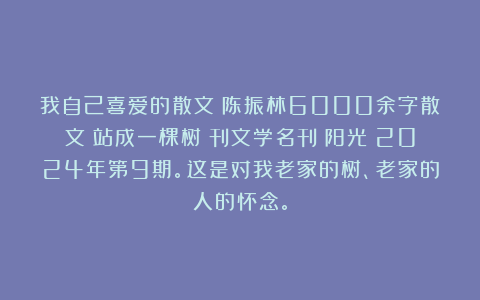
枣树是立在屋子后边的,身材并不高大。没有鲜艳的花儿,等到结了枣子,也不大有人理会。要是贪玩的小伙伴在从枣树边走过,正好是可以捡到几颗枣子的。那枣,鲜亮的颜色,用手擦擦枣皮上的泥土,就可以直接入口了。金秀奶奶屋子后边就有棵枣树,我曾捡起地上的枣儿来吃,脆,甜。金秀奶奶是村子里游走的一个人,她不停地走,口中不停地说着自己不懂的话语。她是有精神疾病的,村子里大人和小孩都叫她“邪子”。她是有家人的,听说丈夫在镇上的食品公司上班,儿子女儿也有工作。但我们极少看到她的家人来陪伴她,也不知道她的生活是怎样过了那么多年。金秀奶奶脸上的皱纹很多,像沟壑一般,横的直的都有。后来我上中学,在中学美术课本上看到一张苦难老妇人的图片,我疑心是不是就拿村子里的金秀奶奶做了样本。
村子里楝树多。从村口进去,有条宽不过三米的土路,平坦,一直贯通到村尾。村路的两旁,会见到三三两两的楝树。高不过五六米的样子,叶片并不茂盛,一粒粒如黄色玻璃球一样的果实才显眼。那果,有调皮的小伙伴用嘴咬过,苦,苦到了心底一般。据说,这楝树果实是有毒性的,当然不能食用。村子里的世珍伯,特别喜欢孩子;孩子们也喜欢他。他曾逗着我们小孩子们尝那楝树果实,也只是逗一逗,却让我们开心起来。世珍伯成家,娶了个个子不高的女人,生养有一女二子。世珍伯瘦高的个子,说话不紧不慢,笑的时候也是轻轻的。他是个头脑精明之人,为着这个家四处奔走,时不时地做点油料或面粉生意。说是生意,也就是到几个村子收购油菜籽然后兑换菜油,或是收购小麦兑换面粉。自然,和菜油厂、面粉厂有些账务往来。不想,有一次他收了五千元的面粉账,却谜一样地消失了。我的父亲和他算是关系不错的朋友,父亲说世珍伯是爱自己的孩子的,如果他活着,即便是冒着牢狱的风险也是会回家看看家中孩子的。几十年过去了,世珍伯一直没有回到我们的村子,这个谜也就成了我们大家的一个谜一样的念想。他家中的大儿子和我同龄,名光,考上了一所师范院校,听说是在大三时就没了钱交学费,最后没能拿到大学毕业证书,也没有顺利参加工作。后来,大儿子光外出打工,也没有什么收获,等到三十好几的年龄,才终于成了个家;没能生下子女,在四十三岁的年龄因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病,听说是肠癌,在大城市是可以动手术治愈的。他的母亲,世珍伯的妇人,一个个子不高却深信迷信的女人,坚信自己的儿子不用手术可以病愈,误送了儿子的生命。这个女人,仍在家做着自己的迷信,引得一些信众聚会在家里,好一番热闹的场景。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是陶渊明的诗意桃源,也是我们村子树木分布的样子。桃树李树大多在屋前,没等到成熟,嘴馋的孩子就拿了竹篙,对着青绿的果子猛搅上几下,自有耐不住打闹的果子扑通掉下。孩子们捡进了嘴里,不停地笑。极少有榆树,多的是柳树。柳树们依着村里屋子的形状,长龙一样地排开。最高大的几棵柳树,在村子的中央地段。有棵大柳树下,却是间小屋子。小屋子里住着一个人,我们都叫他“小耀伯”。我们见到小耀伯时就觉得他年龄很大了,却总是单身一人;他是没有结过婚的。他总是穿着深色的衣服,右眼眼角有颗大大的痣,头上戴着一顶总是耷拉着帽舌的小帽。他的眼是深度近视,几乎看不见人。上小学的我一直迷惑,他没有读过一天的书,却成了个近视的人。他是不配眼镜的,也没有条件让他去配眼镜。他很会喂牛,有时同时喂养两三头。那牛,从牛犊长成半大的牛时,他就出手将牛卖掉,赚些差价。平日里小耀伯手中会积攒或多或少的钱,他是舍不得吃喝或穿衣的,却等着过年的时节,可以坐在赌桌边赌博。那种押单或双的两颗骰子的赌博游戏,小耀伯可以押上几天几晚。赌博时,他仍是看不见骰子的,只是听人家说“单了”或是“双了”,他才知晓自己的输赢。我到县城读书的第一年,小耀伯离开了人世,是60多岁的年纪。他前三天还在赌博桌上押着单双,他昨天还去牵了他喂养的一头牛犊,一路摸着牛犊的头走回了家。
小耀伯有个哥哥,我们叫他“大耀伯”。四十多岁的年龄,才找了个丧偶的妇人成了家。妇人带了两个儿子来,他和妇人没有生育。那妇人,一脸慈祥,我们叫她“福奶奶”,活到了98岁的高龄无疾而终。大耀伯的家,在村子的最西边。他们的屋子,前后几乎没有一棵树,是他家的大儿在屋前屋后栽下了好几棵白杨。
大耀伯的家,隔着进到村里的小路,就是肖师傅的家。肖师傅家的屋子边,有棵柿子树。柿子树不高,我从没见过它挂柿子,于是疑心柿子树应该有雌雄之分。但我每每经过这不结果的柿子树时,就知道到了肖师傅家门前。肖师傅是个铁匠,他的手艺方圆十里闻名。他和他的姐姐,也是随着母亲改嫁到了我们这个村子。2022年的盛夏,肖师傅七十三岁时驾鹤西去,一个铁匠的时代也就戛然而止了。
我家门前曾有两棵特别的树。一棵是椿天树,幼小的我一直以为是“春天树”,因为当它长出青绿鲜嫩的叶子时,春天就真正到来了。我那长着长长胡须的爷爷,抽着长长烟杆的大叶烟,慢慢地对我说:“它也叫香椿树,长寿吉祥哩。那嫩叶儿,是可以食用的……”但我们从没有吃过椿天树的嫩叶儿,只是听着爷爷在一声又一声的咳嗽声里慢慢老去。另一棵树是柏枝树,它没有完全展开的叶,是细长细长的枝,偶尔会看到它粉蓝色的果。母亲说,柏树枝是结婚新郎宴席上专用之物。于是,村里有男子成婚之日,我就会看到有人从这棵上慢慢摘下些枝条,插在装满棉籽的大红花的碗里,摆在大红大红的喜宴之上。我读初中时,读到“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的句子,于是对这棵树肃然起敬。我同时会想起,父亲的名叫“松柏”,那是读过线装书的爷爷给他取的名字。
如今,我家门前的香椿树和柏树都已不在了,我村子路边的那些苦楝树也不见了。村子一长条的屋子后边,还长着些稀稀落落的垂着鸭嘴果的大柳树,那长着细软枝条的杨树也难以见到了。身在南方的我,每年会回到我江汉平原的老家几趟,会见到我日渐苍老的父母,会遇到我村子里看着我长大的老人们。他们都看着我,我会笑一笑,然后和他们说上几句话。
转过头,我觉得村子里的老人们,就成了村里站着的一棵又一棵的树。那些树,分明已经长在了我的脑海里。三十多岁的启珍姐,她家屋后有棵癞柑树,树上的柑子很苦;当年他忍心丢下了两个幼小的儿子,自服农药离开了这个世界。十斤爷爷,据说出生时有十斤重,却天生不会说话,见了我总是会竖着大拇指夸我会读书。满头银发的“老妑妑”(“妑妑”是江汉平原对德高望重女性的尊称),总是笑容满面,像是从《红楼梦》里的荣国府里走出来的。弓着腰行走的张妑妑,嘴里总是衔着一支烟,吞云吐雾像神仙。个头不高的诏珍爷爷,腿上冒出一根又一根的青筋,有着使不完的力气;身材修长的世祥伯伯,手中可以握一支画笔,画出鸟雀跳跃式的对联。均华伯伯,春节舞龙时总是会舞龙头,居然可以站在八仙桌上舞,可以睡在地上舞;均吕伯伯,可以口含柴油,喷出两三丈高的火焰。秉光爷爷、均富伯伯,一个打着鼓,一个敲着锣,以他们为主的“六合班”乐器声,随时出现在村里的红白喜事现场;那个吹着唢呐的是秉岩爷爷……
那些树们,只是自己生长着,一点阳光一点雨水足够了。这些树们,是没见过森林里的热闹与喧哗的。他们身旁,没有甘甜的泉水流过,没有轻快的小鹿跃过,也没有蓝天白云和他们对视,他们只是默默地站在那儿,一年,又一年,悄无声息地走到生命的尽头。
回到南方时,我的心中满怀着不舍与心酸。几回回梦里,我看到村里的那一棵棵树仍旧笔直地站着;在那树下,站着我村子里的一个又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