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拉纳·米特与埃尔斯贝特·约翰逊两位学者在杂志《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错误理解》(What the West Gets Wrong About China)的文章,旨在指出如何正确地认识中国。
尽管他们对于西方的误解进行了反省,但在文中仍有一些片面的解读,如以所谓“威权”来描述中国。对作者的个人观点和表述方式,观察者网不予认同,翻译本文谨供读者参考。
【文/拉纳·米特、埃尔斯贝特·约翰逊 翻译/ 观察者网 刘思雨】原摘要:
许多人错误地认为,在中国,经济自由的发展会带动政治自由的发展,并且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建立在与西方相同的基础上。本文作者认为,这些假设根植于对现代中国的三个根本错误的观点上。其一,经济和(西式)民主是一体两面;其二,“威权”政治制度不可能获取合法性;其三,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生活、工作和投资。
但是,自1949年以来,作为影响所有中国人的机构、社会和日常生活经验的中心,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强调中国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重要性。除非西方的公司和政治人物了解这一点,并修正他们的观点,否则他们将继续这样错误地解读中国。
当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到中国旅行时,它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非常不同。即使在北京,许多人也穿着毛泽东式的制服,以自行车作为交通方式;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官员能够使用汽车。在农村,人们的生活则保留了许多传统元素。但在接下来的30年里,归功于旨在发展经济和增加投资的政策,中国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一个渴望消费的新兴中产阶级。
但是,有一件事仍旧没有改变。许多西方政治人物和企业高管仍然不了解中国。例如,他们相信政治自由将伴随新的经济自由而发展起来,并且错误地认为,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模式将与西方类似,随心所欲,并且具有政治颠覆性。此外,由于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会建立在与西方相同的基础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认识到中国政府持续充当投资者、监管者和知识产权所有者的角色。
为什么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总是如此错误地理解中国?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会看到商界和政界人士经常坚持三种对现代中国的理解,它们流传甚广,但本质上是错误的。正如我们在下文中所论证的,这些假设反映了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和语言的了解上的空白,使得他们在将中国和其他国家类比时,得出了有说服力,但存在严重缺陷的观点。
误解1:
经济发展和民主是一体两面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的发展轨迹与日本、英国、德国和法国在二战结束后立即开始的发展轨迹相同。唯一不同的是,与其他亚洲经济体相比,如韩国和马来西亚,中国起步晚得多,因为它受到了持续40年的毛泽东时代的阻碍。根据这一观点,伴随着经济增长和逐渐富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将走向更自由的模式,就像其他国家一样。
这是一种合理的说法。正如作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所指出的,自冷战结束以来,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似乎已经衰亡,自由主义几乎没有对手。
并且,这种说法得到了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的支持。在2000年的一次演讲中,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宣称:“通过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不仅仅同意了进口更多我们的产品,还同意学习民主最宝贵的价值之一:经济自由。当个人有能力……实现他们的梦想时,他们会要求更大的发言权。”
但这个观点忽略了中国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以及法国之间的一些根本性差异。自1945年以来,这些国家一直是拥有独立司法机构的多元化民主国家。因此,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携手并进,比如通过立法保护个人选择和少数人的权利。
这就使得人们很容易认为民主和经济发展是一体两面。苏联的解体似乎验证了这一观点。苏维埃政权无法为人民带来足够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它的解体。在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glasnost,开放性,指20世纪80年代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俄罗斯最终融入了全球化的经济体制(perestroika,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政治及社会结构的改革)。
1985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右)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会面(图源:搜狐网)
然而,在中国,经济增长是在稳定的共产主义治理下实现的,这表明民主和增长并非必然地相互依赖。事实上,许多中国人认为,中国最近的经济成就,比如大规模的脱贫、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发展为全球性的科技创新者,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威权主义”政府。
此外,中国对新冠肺炎的积极应对与许多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国家的死亡率较高,后来的封锁也不那么严格。这一事实也加强了这种观点。
中国还打破了其“威权主义”将抑制创新能力的猜测。它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太空探索的全球领导者。它的一些技术成就是由市场力量推动的。人们想购买商品、或者更方便地沟通,而阿里巴巴、腾讯等公司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一需求。
但很多技术进步来自于军队,他们具有强大创新能力和充足的资金,对中国新兴产业进行了大量投资。当然,这与美国国防和情报上的支出在硅谷发展中的作用是一样的。
但在中国,面向消费者的应用实现得更快,政府投资与惠及个人的产品和服务之间的联系也由此表现得更加明显。这就是为什么普通中国人将中国公司,比如阿里巴巴、华为、抖音等,视为民族自豪感的来源和中国成功的国际先锋,而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将其简单地看作工作岗位或GDP的提供者。
因此,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艾什中心于2020年7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95%的中国人对北京政府持满意态度。我们自己在中国的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我们遇到的大多数普通人并不觉得“专制国家”完全是压迫性的;对他们来说,“威权国家”也提供了许多机会。因为中共改革了财产法,现在重庆的一名清洁工能够拥有几套公寓;一位上海记者从国家控股的杂志社那里获得报酬,飞往世界各地报道全球生活方式的变化趋势;归功于社会的流动性和党对科学研究的大量投资,南京的一名年轻学生能够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学习推进物理学(Propulsion Physics)。
过去十年,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中国领导人对一个观点更加坚定了,即没有所谓的政治自由化就可以进行经济改革。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中国人眼中,这场危机暴露了“华盛顿共识”的疏漏,即认为民主化和经济成就是绑定在一起的。
在此后的几年里,中国成为经济巨头、技术创新的全球领导者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同时,它强化了政府,并坚定了自由主义模式不适用于中国的看法。2017年,习近平宣布中国发展的“三大攻坚战”针对的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实际上,中国不是一个追求更加自由化的国家,而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寻求更加成功的国家。
在西方对中国的许多分析中,“停滞”一词最经常被用来形容中国的改革。但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停滞不前。相反,它仍然快速发展,只是不朝着所谓自由化的方向罢了。
许多人误解中国发展轨迹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倾向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变体,特别是在其用于海外宣传的英文材料中,认为这样更容易获得信赖。
它经常拿自己和西方人熟悉的品牌作比较。例如,在说明为什么要参与英国5G基础设施建设时,华为自称是“中国的约翰·刘易斯”。约翰·刘易斯是英国著名百货公司,该公司经常被评为英国最值得信赖的品牌之一。
中国也经常煞费苦心地向外国政府或投资者暗示,中国在许多方面与西方相似,比如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休闲旅游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这些相似之处确实存在,但它们是中国新兴的富裕中产阶级的财富和个人追求的表现,绝不意味着中国和西方在政治制度上不存在真实的巨大差异。
而这就引起了第二个误解。
误解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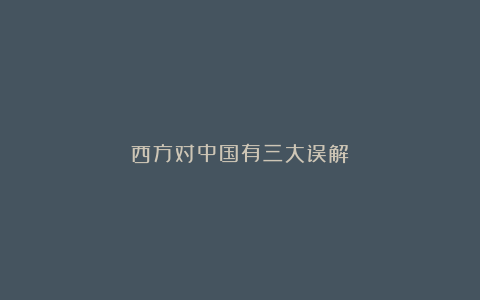
“威权政体”不具有合法性
许多中国人不仅不认为政治上的民主是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且认为他们的政府结构是合法和高效的。但是西方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许多人仍然期待中国政府减少投资、监管,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占有,而中国政府认为自己在这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在中国人眼中,其“威权”政治制度的部分合法性同样来源于历史:中国经常不得不击退外来侵略者,而且,正如西方很少承认的那样,从1937年到1941年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中国基本上是独自与日本作战。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其单独击溃了外敌,而打败了国内敌人(1949年的蒋介石)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胜利,从此确立了共产党及其体制的合法性。
七十年过去了,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现在的政治制度其实比西方的更合法、更有效。这种观念在许多西方企业高管看来很陌生,特别是如果他们有过与其他威权政体打交道的经历的话。中国和其他“威权国家”关键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制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根据我们的经验,许多西方人并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理解它为什么重要。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体系主要关注经济结果,这当然会产生政治影响——例如,为了确保财富的公平分配,公有制是必要的——但经济结果是重点。然而,列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学说,它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度不仅关注经济结果,而且还关注如何保持和稳固现有政权。
这对希望在中国做生意的人有着重要意义。如果中国只关心经济结果,它将欢迎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如果他们还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话,中国将把他们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不关心谁拥有知识产权或合资企业的多数股权。但是,由于这也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制度,这些问题对中国领导人至关重要,无论他们的外国伙伴在经济上是多么地有效或有帮助,他们都不会改变想法。
中共列宁主义式的领导选拔方法也是其保持合法性的一种方式,因为对许多普通中国人来说,这种方法可以产生相对称职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是由中国共产党挑选出来的,而且是从成功治理乡镇开始,一步步晋升到省级,然后才进入政治局。如果你不能证明你作为管理者的价值,你就不可能成为中国的高级领导者。中国领导人认为,与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政体上的列宁主义式规则使得中国政治远没有那么专制或有那么多的裙带关系。
要获得成功,掌握列宁主义的学说仍然很重要。不管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是进入大学,人们都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这门必修课。而这也成为了中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从2018年的电视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就可以看来。通过“学习强国”等便利的应用程序来教授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习近平在内的思想家们的基本知识,政治教育如今已成为21世纪的业务。
电视节目《马克思是对的》截图
中国政治的列宁主义性质也可以从其讨论政治时所使用的语言中得到印证。中国的政治话语仍然根植于马列主义的“斗争”和“矛盾”思想——两者都被看成是促成必要甚至有益的对抗局面的重要因素,有助于取得胜利结果。
中国利用其特别的“威权模式”——以及其认为的合法性——与民众建立信任,不过这种方式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会被认为具有高度的干涉性。例如,山东省某市利用大数据(政府可通过监控和其他采集数据的基础设施获得)为人们设定其 “社会信用评价”。这会根据公民平日政治或经济上的信用良好与否来奖励或惩罚他们。奖励既有经济利益上的(例如可以获得抵押贷款),也有社会公共服务上的(允许购买新高铁的车票)。那些社会信用分数较低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法购买机票或无法在某应用软件上约会。对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但对中国的许多普通人来说,它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签订的社会契约中一个完全合理的部分。
这样的想法可能与中国向国际上英语听众展示的、儒家对外宣称的“仁爱”与“和谐”的概念大相径庭。但即使是这些概念也导致了西方人相当大的误解,他们常常把儒家思想简化为令人厌烦的“和平”与“合作”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实现“和平”与“合作”的目的在于尊重一个恰当的等级制度,而等级制度本身就是一种控制手段。在后启蒙时代的西方看来,“等级”和“平等”似乎是对立的概念,但在中国,它们却具有内在的互补性。
如果西方人要对如何与中国打交道或在中国投资作出更现实的长期决策,那么认识到“威权”的马列主义制度在中国不仅是合法的,而且是有效的这一点至关重要。但第三个误解也会误导那些寻求与中国接触的人。
误解三:
中国人像西方人一样生活、工作和投资
中国近来的历史表明,中国人与他们的国家作决策的方式与西方人截然不同——无论是在时间观念方面,还是在最令人担心的风险方面。但由于人们倾向于相信其他人也会像他们一样作决策,这可能是西方人最难以克服的一个误解。
让我们想象一下一位如今已经65岁的中国女性的故事会是怎样的。出生于1955年,她小时候经历过“大跃进”,十几岁的时候成为了红卫兵。由于父母是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再教育,而她则高喊着崇拜毛主席。到了20世纪80年代,她是第一代重返大学的人。
接着,在20世纪90年代,她利用新环境下的经济自由,在其中一个经济特区成为了一个30多岁的企业家。她买了一套公寓——这是她家历史上第一次有人拥有房产。由于想积累更多经验,她在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外国资产管理公司担任投资分析师。尽管她的雇主为她制定了长期的职业规划,她还是离开了这家公司,因为一个竞争对手可以提供少量的短期内加薪。
到了2008年,她最大限度地利用可支配收入的增长购买了新的消费品,这是她的父母以前做梦也实现不了的。到了2020年,她希望看到自己7岁的孙子和刚出生的孙女(直到最近才开放二胎)过得好。
许多中国内地消费者更喜欢股市的短期收益,而不是把钱锁在长期储蓄工具中。市场研究一贯显示,大多数内地个人投资者的行为更像交易者。比如2015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频繁交易是在破坏而不是创造长期基金的价值,81%的个人投资者还是选择每月至少交易一次。这一数字高于所有西方国家(例如,只有53%的美国个人投资者如此频繁地交易);甚至高于邻近的香港——另一个也喜欢赌博,并且有着相似的资本收益免税制度的汉族社会。这表明,中国内地特有的某种东西影响了这种行为:现在购买股票的那些人或曾经经历过对长远未来的不确定性,或将其传承了下来。
这种专注于确保短期收益的做法就是这位上海的年轻资产经理放弃了一份未来可期的工作,而换了一份收益相对较小但能立竿见影获得加薪工作的原因——这种行为仍然困扰着许多试图留住人才和管理层的企业。人们通常是在满足了他们对短期安全的基本需求之后,才愿意承担长期职业风险的。
例如,我们曾采访过一对夫妻,妻子“下海”创业了,成为了中国众多的女企业家之。她之所以能下海,是因为她丈夫在国有企业工作,有着虽低但稳定的收入,能为家庭提供安全保障。房地产作为长期投资的资产类别之一,被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资——其25岁至69岁人群的所有权从1988年的14%增长到2008年的93%——这种变化也是出于对安全的需求:与所有其他资产不同的是,如果出现社会问题,房产起码能给人提供庇护之所。
(与个人)相比之下,政府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则偏低,并且非常关注长期回报。大部分投资的方式仍然是中国共产党苏联式的五年计划,其中包括发展以太阳能技术、“智慧城市”和高密度节能住宅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如果没有政府的参与,这样的雄心壮志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中国,这种理想是相对迅速而容易实现的。相比之下,西方经济体在这些问题上的进展往往极其缓慢。
个人和国家关于投资的决策都有同一个目的:在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中(为自身)提供安全性与稳定性。尽管西方许多人可能认为,中国在其21世纪的全球计划里只看到了机会,但其动机却截然相反。在中国动荡的现代史上,它一直受到外国势力的威胁,无论是在亚洲内部(尤其是日本)还是在亚洲之外(19世纪中叶的英国和法国)。
因此,中国的领导者认为,外国的介入与其说是机会的来源,不如说是威胁、不确定性,甚至是屈辱。他们仍然将许多不幸归咎于外国的干涉,即使这是发生在一个多世纪前的事情。例如,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中的角色开启的100年仍被中国人称为“屈辱的世纪”。中国的历史继续影响着它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目前对其主权不可侵犯的坚持。
和西方人不同,那些经历过他们无法控制的艰难时期的人更倾向于在短期内作出一些关键选择。相比之下,政策制定者们则在寻找在未来获得更多控制权和主权的方法,他们的计划比西方要长远得多。这种对可预测性(或者说稳定性)的共同追求解释了以控制为核心原则的“威权体制”何以能保持持续的吸引力。
……
许多西方人接受了中国呈现给世界的解释:1978年邓小平开始的“改革开放”时期强调要避免文化大革命时的那种激进且往往充满暴力的政治体制,这说明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不再重要。现实情况则大不相同。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塑造中国人民的制度、社会和日常生活的中心。党始终相信和强调中国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重要性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一切。除非西方企业和政治家接受这一现实,否则他们将继续误解中国。
点一下右下角“在看”,让我们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