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狼居胥、石勒燕然,这两者代表两汉对外武力之巅峰,但前者让汉军付出人员死伤数万马匹死亡十余万的代价,后者战损比极佳却因为打破草原上的均势致使北匈奴衰亡后,吃下匈奴残余势力的鲜卑又成了汉朝之大敌。本文要说的却是常被忽略,然而战果相当卓著的昭帝朝对匈奴的反击战。
昭帝朝不似喜欢主动出击的武帝朝,对匈奴的战斗基本上选择了防守反击。防守反击并不等于被动挨打,昭帝朝的防守反击打出了汉代对匈奴的最佳战损比
明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
没看错,这一战打出了9000:0的战损比,还生擒了瓯脱王!单纯只是九千骑损失对匈奴不算大伤元气,若是普通的王在匈奴可能也不算太值钱,毕竟卫青霍去病抓过的匈奴小王不知凡几,但从匈奴后续反应来看,这个瓯脱王在匈奴的地位很是不一般的。
瓯脱王的领地在匈奴应当处于极重要地位,甚至可能跟匈奴王庭是相连的,以至于瓯脱王被抓后匈奴怕他成了带路党,吓得不敢南逐水草。而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罕见的让人民屯居瓯脱以构建防御体系,在第二年更是增兵九千屯于受降城,并于北方的余吾水造桥方便跑路。
此战对匈奴的震慑,使匈奴远遁,整个武帝朝也只有使匈奴于漠南无王庭的漠北之战可以媲美,然而漠北之战劳师远征取胜之后人力物力消耗甚重,此战中汉军无所失便显得更胜一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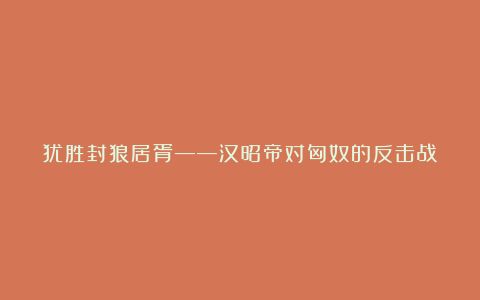
服软求和亲的匈奴
很多人以为汉武帝就打废了匈奴,其实不然,武帝末年由于数十年征伐不断导致’海内虚耗’,又出现人民不愿当兵’民多买复’,想漠北之战时有数万私负从者就可知当时汉朝风气尚武好战,如今出现人民乐意当兵打仗,就可见武帝末年确实征伐过重。在大汉的经济水平和兵源素质双重下滑下,匈奴已经再度嚣张起来,单于公然叫嚣’南有大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不为小礼以自烦。’
正是昭帝朝再度打击了匈奴的嚣张气焰,就在上文所提战役的前后,其实还有几次和匈奴的战役,可惜具体的战斗细节未被记录,但从战果仍可看出对匈奴打击效果卓著:
卫律在时,常言和亲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后,兵数困,国益贫。单于弟左谷蠡王思卫律言,欲和亲而恐汉不听,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风汉使者。然其侵盗益希,遇汉使愈厚,欲以渐致和亲,汉亦羁縻之。
从这段记载来看,匈奴的主流观点对与汉和亲一事是不赞同的,接受和亲后虽可收到汉庭所给予的大量物资,但和亲的同时双方也是签订了友好盟约,再去边境劫掠就显得太过理亏,匈奴本质上是一个部落联盟,动辄便背约匈奴作为这个盟主名声太臭,对内部统治未见得有好处。尤其是武帝末年后,自以为重新占据优势的匈奴,相比于和亲所得物资,认为劫掠可以带来更大利益是可以想象的。
然而昭帝朝的打击使得匈奴’兵数困,国益贫’让匈奴开始服软,主动对汉朝示好。左谷蠡王担心主动提出和亲汉朝可能不答应,这更表明一个事实,由于汉昭帝时期对匈奴的打击,匈奴在汉朝面前再度变成弱势的一方,汉朝完全不惧前来寇边的匈奴,通过和亲来避免匈奴抄掠边境的手段已经可有可无!
张掖太守破匈奴
汉代的大多数情况,边地的郡守之于入寇的匈奴都是被刷的副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早在汉初晁错就说的很清楚了:
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於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出胡又已去。
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居无定所,可以更方便的挑选防守薄弱的郡县入侵,汉制对太守其本郡的惩罚是很严厉的,没有特殊情况出界是往往会丢掉官位。虽说在受到五千人以上的敌人入侵时是被允许找周围的地区帮助,但匈奴凭借轻骑兵优秀的机动性,往往在汉朝大军聚集之前就已经劫掠完跑路了。然而昭帝朝的张掖太守却成功反杀了匈奴一次:
单于使犁汗王窥边,言酒泉、张掖兵益弱,出兵试击,冀可复得其地。时汉先得降者,闻其计,天子诏边警备。后无几,右贤王、犁汗王四千骑分三队,入日勒、屋兰、番和。张掖太守、属国都尉发兵击,大破之,得脱者数百人。属国千长义渠王骑士射杀犁汗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犁汗王。属国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后,匈奴不敢入张掖。
匈奴单于探得酒泉张掖的兵弱,以为像以前那样可以捡漏,哪知道这个计划被投降汉朝的匈奴人告密,张掖太守早早做好了战备工作,于是大战到来,匈奴惨败,入寇的四千人只有几百人亡命而去,犁汗王被当场射杀,一战打匈奴自此以后不敢入张掖。甚至之后的西汉历史都出现了
“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稀)复犯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