颖邨旧貌
(一开始的陕西南路误读成西藏南路了,算了,不改了,希谅。)
长远没来走走这段复兴中路了,从襄阳南路到陕西南路。
昨日地铁八号口出来,走过一个弄堂口,看到里面很多人在排队,走近仔细一看,右面一排动迁办公室,大家等着面觐。
后来找了个人少的空隙拍照
每个门上都贴着蓝纸条,上面写着1218弄、1232弄、1248弄、1252弄等,这不就是我熟悉的小桃园弄、颖邨、辣斐新邨、张家弄嘛!
怎么?这里也都要拆了么?
辣斐新邨
张家弄
我还有点不相信,一只一只弄堂都走进去张一张,果然都挂满了促迁的红色横幅。
这段复兴中路,承载了多少我的青春往事啊!
借书、还书、谈文学、谈电影、学桥牌、学照相,包括谈最初的那几段恋爱,以至于后来每次到这里来走走,都如梦如幻。
乃末完结,青春记忆要无处安放了。
讲起来,老早属于徐汇区的这段复兴中路人气最足。襄阳路朝西,肃肃斯静;陕西路朝东,也没啥店面,都算是当年半夜里小姑娘不敢独行的路。
唯独这一段,颖邨、辣斐新邨沿街面都是店家,什么留华兴(音)百货、明星理发社、红星酱油店、时代文具店,还有邮电局、烟纸店、馄饨店、大饼摊,西面一直到张家弄,东面到小桃园弄,上街沿永远有人来来去去。
颖邨对过,嘉善路是弹格路,也是小菜场,一直连到现在最时髦的永康路,也极具烟火气,永远的大呼小叫,永远的一脚深一脚浅。
小桃园弄也四通八达,啥个环龙邨、道生里,都可以通到南昌路、陕西路。里面永和坊、生生里、永顺邨和张家弄也都是相通的。一部分拆钱家塘时已经拆掉了,现在,要拆所有剩下来的。
顺便说一句,老早钱家塘分三块。
此地叫南钱家塘。南昌路与淮海路之间叫钱家塘,淮海路以北,陕西路以东,现在百盛那一块叫北钱家塘。
梅谷公寓
梅谷公寓陕西路门面
再朝东还有上海大戏院,转弯角子是四层楼的梅谷公寓(Mico Apartments),又叫过亚尔培公寓。
底楼转角是宝仑药房,后面可以对穿的是采芝邨食品店,是两家食品店连起来的。朝南一家老早叫中央,朝东一家老早叫中美,名字倒都起得大豁豁哩,狠的。
马路对过并排有两间学堂。靠路口一间,阿拉小辰光叫机校,一机部的机器制造学校,最早是同济德文医工学堂,现在叫上海理工大学。
靠嘉善路一间是赫赫有名的徐汇区第一中心小学,最早叫比德小学。1950年代的校长是秦鸿钧烈士的妻子韩慧如,当年徐汇区的小学生都去听过她作报告的吧。
嘉善路当年也有一所“名校”,人称“嘉大”,即“嘉善大学”,其实是一爿民办中学,最早缩在永乐邨隔壁弄堂的几间平房里。
此地弄堂里的爷娘看见自家小囡小学读书不用功,就要讲,哎,小鬼,再迭能神之巫之下去,人家侪去读“五十一”(即位育中学,就在附近)了,侬只配去读“嘉大”啦。
我最早到此地来,是因为我大哥当时初中毕业就沦落到生产组,组里最要好的同事住在颖邨,我就当他们的跑腿,夜里来借书还书。
说起这个生产组,也是宝庆路3号最后的徐公子徐元章先生生前唯一的工作单位,最早叫线圈组,后来叫玩具组,从新乐路52号搬到张家弄20号,后来变成新乐无线电厂,就在现在的“博多新记”隔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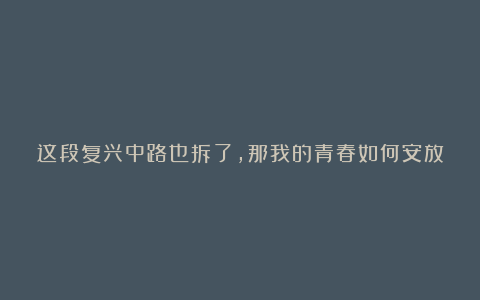
那个年代,私自传阅幸存下来的翻译小说还不能大鸣大放,所有的借书还书都要在夜幕之下进行。
何况,书的周转极快,每人过手只有一两天。而十二点前还书才叫“只脱时辰,不脱日脚”,所以,还书总会拖到很晚。
再晚,书还是不能明当明拿在手里,放在包里也不放心。
定坚要塞在后腰的皮带里,再用外套罩牢,走路还不好鲎背,以免显出书的形状。
我从上方花园过来,要么先穿新康花园,走到襄阳路,如果夜还不深,便不再东行,而是绕到南昌路;要么从淮海路过来,先穿钱家塘到南昌路。
然后再穿弄堂,张家弄585弄啥个弄都可以穿,有时从辣斐新邨出,有时从小桃园弄出,再到颖邨,所以里面的路我熟得不得了。回去如借到了书而非空手,也不走大路,先穿弄堂。
借书还书,当然不会只是交接,总要坐忒一歇,讲忒两句。
一讨论小说情节,人物命运,往往就刹不住车,一谈就到半夜。
谈着谈着,发现趣味如此相投,于是,不借书还书的日子也去坐坐,也去闲谈。
跟着那些大哥哥小姐姐,还一起游公园、看电影、听音乐,打桥牌,还一道将棉被封住窗门,在自制暗室里汏照片印照片,不亦乐乎。
也疯,也闹,也曾恣肆汪洋。
好像青春挥霍不尽,永远还有,就像那段复兴中路,会永远陪伴我们。
认得的人也越来越多。有蕾茜饭店楼上的,有小桃园弄里的,还有永顺坊的。
讲起来,那时弄堂里的美女还真不少,商店营业员中也有,个个漂亮,一点也不比杨超越推扳。有的气质极好,简直就是明星相。
可惜当年机会实在太少,部队文工团来招生,也无从得知啊。放到现在,早就选秀出道了。
不过,自从有了星探,有了选秀,基层再也看不到啥美女了,是不是也很没劲。
另外,当年能接触到的小姐姐都很年轻,已婚少妇是不大会轻易来搭讪的,她们的男人要吃醋的。
说起来现在年纪轻的人也许无法相信:60年前,上海弄堂里的风俗,22岁一过,就是老姑娘了,寻不着男朋友真会抬不起头来,日脚蛮难过的。
弄堂里热心做红娘的阿姨妈妈心里都有路数:22岁以下或刚到22岁的,才帮侬介绍同龄(上下两岁)的上海男子。
22岁到25岁,就要帮侬介绍比侬大七八靠十岁的上海男子了,要么明显有点不足的;25岁朝上,要么郊区的,要么二婚头,还有,就是分配到外地工作的上海大学生。
有一位住在颖邨的老兄,曾经谈了一个很好的女朋友,我也认得,就是因为没婚房,一直拖着。
拖到小姑娘25岁了,再也拖不下去了。女方爷娘叫伊相亲伊不去,干脆作主,帮伊寻好一个从上海去武汉支内的大学毕业生,这一次,她也犟不过了。
分手那晚,两人一边抱头痛哭,一边竟还在那里想办法。
那女子甚至讲,要么我先嫁过去,一年内就开吵,一直吵到离婚,爷娘那里总有交代了吧。我再回来寻侬,但肯定没工作没户口了,你还会要我吗?
当年的上海女子真的很痴情,这样的故事不是个别的,我就听见过好几回。
我也曾认识一位住在永顺坊的胖胖的女孩子,一来二去颇相熟。但我那时已经知道,按条件我毕业以后肯定是要去外地插队落户的。情热时,她依然不止一次对我讲,我等你,我真的等你。
青春的胡话好美丽,也最难忘。
后来,大家都好理智,说话都好正确,人生却好没意思。
青春记忆,当然可以放在文字里,放在照片里,存在手机里,存在硬盘里。
但它也一直安放在原地,在那楼那墙那门那窗那楼梯那过道那把手那栏杆。
你一走近,它就开始在你心里原声播放。
唉,都拆了,我就再也找不到播放的开关了呀。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