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从维柯、克罗齐到柯林武德,人类史和自然史是分离的,甚至自然史是不能被纳入到史学研究范畴的学问。但随着全球范围内气候异常现象的频发,气候以及相关的环境问题既成为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自然史也开始被提上研究日程。后殖民史学家查克拉帕蒂在近两年连出两本书讨论当前“人类世”气候问题,希望打破人类中心的“全球史”“人类史”等陈旧范式,把历史写作从“全球”(globe)的尺度拓深到一种“星球”(planetary)尺度,也即走向一种“星球历史”的写作。
✦
✧
一个星球,多重世界
✦
气候问题激发讨论
作为史学契机的气候问题
在讨论气候问题之前,查克拉帕蒂首先指出,史学领域长期以来都存在着“自然史”和“人类史”相分离的倾向,而这与史家对“自然”相对消极的观念密切相关。这一倾向可追溯到近代历史哲学之父维柯,后者就曾指出,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因而只有上帝才能真正理解它,而我们“这个民政世界既然是由人类创造的,人类就应该希望能认识它”,历史就只适合处理人类世界,人类只能拥有“关于自己的民事的和政治机构的种种知识”,因为是人类造就了这些机构,反之,自然的历史只能搁置一旁,因为人类无法理解它(《新科学》)。
深受维柯影响的意大利现代哲学家、史学家克罗齐同样也认为,就某种程度而言,“自然界没有历史”,因为自然界不像人类,不是一个“有思想的理性生物”,人类也没有办法将自身的精神和思想投射其中,与其共通,因而也就无法将其作为一种历史对象来理解,最多只能将其“加以分类并排列成系统”,就像是人类如果认为一片草叶有其“历史”,那么人类自己首先“应该设法使自己变成一片草叶”,进而才能将其作为历史对象理解,但是如果“变不成功”,就只能“满足于分析叶片的各部分”,或者为叶片主观建构一种想象的“假历史”(《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
作为克罗齐思想的重要阐释者,英国史学家柯林武德在其代表作《历史的观念》中最为直观地将这一脉影响呈现出来。首先,柯林武德认为,一个真正的历史事件往往有“内在”和“外在”这两个维度。所谓事件的“外部”,属于“可以用身体和它们的运动来加以描述的一切事物”,比如“恺撒的血在某个时刻流在了元老院的地面上”,而事件的“内部”是指“其中只能用思想来加以描述的东西”,而“恺撒流血”一事的“内部”就是恺撒和谋杀者之间有关宪法政策的冲突。再者,史家研究的不是“单纯的事件”本身(单纯的事件往往只有“外部”),他要研究的是“行动”,而“行动”是事件外部和内部的统一体,“恺撒流血”令史家感兴趣仅仅在于这件事与一场宪法冲突的关系。史家的任务是“从事件的外部钻入它的内部”,把自己放到这个行动中去思想,去辨识出其“行动者”的思想。
但是,对柯林武德来说,自然界中固然会发生一些变动(比如自然灾害等),但是这些只是前面所说的“单纯的事件”,这样的“事件”不存在“内”“外”两个维度,它只有“外部”,在其中也不存在具备思想的“行动者”,史学无法去“从事件的外部钻入它的内部”,发现“行动者”的思想,相较之下只有人类事务才可能同时具备两个维度,成为可待研究的“历史”,进而,柯林武德那句著名的宣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才顺理成章(《历史的观念》)。
从维柯、克罗齐到柯林武德,如查克拉帕蒂所言,这样一脉相承的史学观念,总体而言就是将自然或地理环境只是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个沉默的、被动的“背景板”,人类社会数千年来可能早已经过几种社会制度的更替,但自然作为“背景”的“消极”处境却几乎不变,自然环境的长期的缓慢变动——如果称之为“自然史”的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自然史”与“人类史”因而也就长期在史学领域中两相分离。
“自然史”和“人类史”长期的两相分离
随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环境史”(environmental history)研究不断扩大影响,以及随着近年来神经科学、地质科学等学科不断被史家吸收,前述史学眼光才发生了改变:首先,自然史和人类史之间不再分离,开始呈现出双向的互动,如史家克罗斯比就写道,哥伦布到达美洲及其带来的全球交流与生态交换(动植物的跨大陆流动、病菌的传播等)对地球动植物的生态系统造成巨大改变(《哥伦布大交换》);再者,人类自身的“生物性”及其发展变化也开始被史家关注,而不是只被关注社会性和思想性维度,比如美国学者丹尼尔·斯迈尔就尝试结合神经科学等前沿学科指出,人类大脑的进化历史和人类的文化发展史之间关联紧密(On Deep History and the Brain)。
不过,查克拉帕蒂认为,如前所述的变化恐怕仍是不足的,在今天,史学对人类活动的讨论需要进一步超出“环境史”范畴,因为当下的人类活动已成为重塑全球地质环境和生态圈层的主要驱动力。“人类世”概念也正是在此背景上被提出的,虽然概念的细节还存在争议(杰里米·戴维斯:《人类世的诞生》)。当代人固然不单单是社会性、思想性的“行动者”,也不仅是生物性的“行动者”,更加已然成为一种地质力量,一种地理层面的“行动者”(geological agent)了。史学领域中“自然史”与“人类史”的两分这才真正被打破,因为在“人类世”语境下,“人类史”本身就已经成了“自然史”的一部分,二者已然融为一体。表面上看,气候危机只是一个当下的现实难题,而历史学家只关心过往之事,似乎两者并不相干,但是对查克拉帕蒂来说,当代气候问题恰是史学发展的契机,将会促成学界进一步更新“史学的想象力”。
从“全球历史”到“星球历史”
再现“人类世”的插画(来源:foreign polic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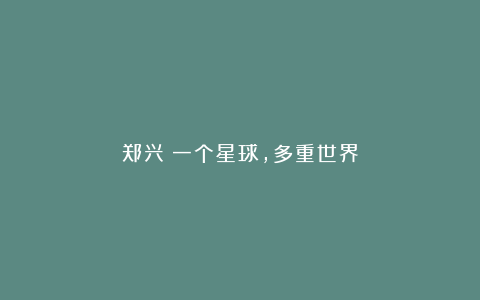
“一个星球”与“多重世界”的两难
但是,查克拉帕蒂并不只是单纯提倡一种更为总体性的“星球史观”,他更进一步的洞见在于,“星球史观”或者种种“人类世”话语其实仍然面临着内在悖论:一种普遍性的视野固然使我们能够跳出具体的、特定的人类历史的狭隘性,但是普遍性的视野本身会不会可能带来另一种总体暴力,一如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对黑格尔的批评——“普遍历史”是否意味着对于个体性、特殊性的漠视和伤害?作为一个来自印度这一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查克拉帕蒂本能地疑惑:虽然同处一个星球,但不同国家、地区和族群的发展千差万别,实际是处于完全不同的现实世界,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应该如何面对自身经济发展需要和承担全球环境治理责任之间的两难?
首先,印度、中国这些发展中国家对于发展经济的渴求是值得肯定的。查克拉帕蒂借助于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理论指出,摆脱贫困的标准不是绝对收入数字的提升,而是人的“实质自由”得到提高,此即有更大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去“做他们有理由珍视的事情……以及去享受他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如果经济发展能使人们摆脱原先的困境,带来“可行能力”的提高,这样的经济发展就可算是“作为自由的发展”,一种对人的“解放”(《以自由看待发展》)。对印度、中国这样曾经长期处于绝对贫困的国家而言,经济发展固然可能带来环境压力,但也意味着一种极大的可能性让更多人从贫苦的困局中走出,从弱势的处境中走出。以印度为例,其城市的拥挤并不全是人们贪恋“舒适”生活所致,人们涌进城市更多时候是因为一个底层人对正常生活的渴望、一个贫寒者对摆脱身体折磨的渴望、一个普通女性摆脱性别不平等的渴望,总之就是出于获得“解放”(emancipation)的愿望,而无论是个体还是国家,获得“解放”的愿望在道德上无可指摘。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印度和中国一方面摆脱了列强控制,为人的解放创造了政治基础,同时在近年来促成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即便只是普及洗衣机这一点,也意味着一种对妇女的解放。不能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这快速发展的几十年称为资本和城市化扩张的负面时代,也应该看到其中“实质自由”的提升值得肯定(《气候视差》)。因此,对发展中国家在“人类世”中的位置要持“同情之理解”,不能因为“人类世”危机的总体性就否定了人类不同族群的处境差别,其对环境危机所应担负的具体责任更值得仔细斟酌,不能简单强调“平等”而忽视“公正”。当然,更加要理解发展中国家走出和西方国家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因为“现代”本来就不必只有西方这一种版本:一方面,从反殖民角度来说,解放和自由意味着免于对殖民者的恐惧;另一方面,解放和自由还意味着摆脱对于贫困的恐惧。如果不能解除对于贫困的恐惧,那么,他们的自由就是不完整的、不彻底的(《气候视差》)。
再者,“星球历史”还要求我们要兼顾到人类以外的生命体,这无疑带来更加棘手的问题。举例而言,马绍尔群岛的居民主要以捕食金枪鱼为生,但是以“后人类”的眼光来看,金枪鱼也会索要自己的生存权,如何处理这两者的冲突?查克拉帕蒂建议,我们首先要敬畏自然,时刻谨记它的复杂性远超我们的理解和技术计算之外;此外,现代人不妨从人类学对一些原住民群体的描绘中借鉴跟自然对话的方式,比如当北美印第安人通过自己的“波塔瓦托米语”,以及种种当地的故事来理解茅香这种植物时,是将茅香视为一种神圣的生命,与之建立起某种神秘的亲缘,而这跟现代植物学的理解方式截然不同。这当然不是要走向反科学的泛灵论,而是要将“科学的语法”和“有生命的语法”结合起来(罗宾·基默尔:《编结茅香》)。当然,这种方案具体会有多大实效仍有待验证,不过,至少为我们尝试在“人类世”中容纳“非人”、理解“非人”提供了起点。
更进一步而言,查克拉帕蒂认为,在今天,政治仍然重要,因为政治发生的前提就是承认人类群体的差别,在政治中辩论、妥协和异议乃是常态,人类群体的内部分化是一定存在的,这种差别当然要通过更进一步的政治讨论来协商。但是,我们也只能“部分程度”地接受当前的政治,因为当前的政治机构和规则都是建立在人类自身有限的现象学经验的基础上,依然是以人为中心,“非人”还没有被纳入到政治规则之中,如何能在政治层面与其兼容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人们仍然有待找到一种更好的路径,建构拉图尔所说的“自然的政治”(《气候视差》)。
查克拉帕蒂提出“星球历史”并不是为了凑近当下的热点话题,而是因为史学的发展本身就存在与这一话题对话的内部逻辑:这颗星球并不仅是人类的星球,也不仅是和人类发生关系,更不为人类而存在,气候危机重新把这颗星球的“他者性”裸露在史家面前,敦促后者摆脱人类中心主义,重塑研究范式。当然,“星球历史”也促使我们直面危机中“人”和“非人”的在地性和具体性,在现实层面最大程度地理解差异,寻找最具包容性的解决方案。
(Dipesh Chakrabarty: The Climate of History in a Planetary 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Dipesh Chakrabarty: One Planet, Many Worlds: The Climate Parallax,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23)
* 文中图片未注明来源者均由作者提供
#artContent h1{font-size:16px;font-weight: 400;}#artContent p img{float:none !important;}#artContent table{width:100% !important;}
 皮不要扔!|可持续材料
皮不要扔!|可持续材料 可以被吃掉的瓶子|可持续材料
可以被吃掉的瓶子|可持续材料